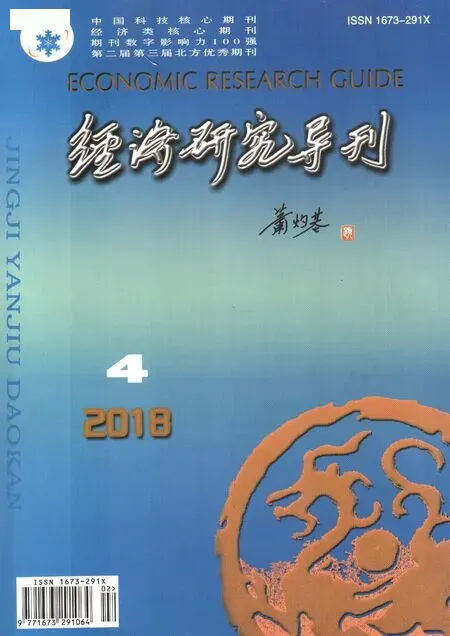古镇空间文化发掘中的法律困境与救治
崔彩贤,唐暨鑫
(1.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陕西杨凌712100;2.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杭州310000)
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及国家对文化产业的扶持,特别是现代休闲消费的兴起与快速发展,承载着现代人浓厚“乡愁与怀旧”情怀的古镇空间文化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以“文化的名义”对古镇空间进行发掘与保育的情况随处可见,但部分主体“趋利性”的行为导致古镇空间发掘过度或混乱,致使古镇空间文化保育和拓展出现问题。而现行大部分的学术研究主要是从社会学、建筑学、历史学、文化学、景观学等方面对古镇空间文化进行研究,鲜有从法律和制度规制层面对古镇空间文化进行阐释。本文主要从法律规制的视角,对古镇空间文化发掘与保育的利益相关者行为进行分析与梳理,并提出相应的救治措施。
一、法律诉求
中华文明五千年历史造就了660多个大中小城市和近2万个集镇[1],而古镇更是千年文化积淀的精华所在,具有无可估量也无法再生的人文价值。但随着消费经济的兴起和趋利性的开发,以开发的名义对古镇的破坏与不合理开发层出不穷。把古镇以商业化的模式打造成旅游景区,形成了以丽江、乌镇、凤凰等各具代表的古镇旅游目的地,但在市场经济趋利性的作用与影响下,古镇居民和当地政府忽视了古镇游客游览的总容量,超负荷的旅游性开发对古镇的生态、历史建筑、原始生活形态都产生了潜在的破坏。同时,在开发过程中不重视整体规划与监管,古镇建筑的改扩建行为泛滥,带来极大的安全隐患。2014年1月11日凌晨,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州府香格里拉县的独克宗古城发生大火,一千三百年历史的古城核心区变成废墟;1月25日晚,贵州省镇远县报京乡报京侗寨发生大火,三百年历史的侗族村寨被烧毁;4月6日凌晨,云南丽江束河古镇发生火灾,造成重大损失。火灾事故的发生,与古镇开发过程较随意、程序审批监管缺失有很大关系[2]。面对市场趋利性的古镇破坏性开发行为,法律的缺失、不完善以及各相关主体法律意识的淡薄是其中很重要的根源。古镇文化的开发、挖掘与拓展需要明确各利益主体间的权利义务,并且在运行过程中施以层层监管。同时,各相关主体要有对制度的敬畏和遵守,提高法律意识和法律素养,保护古镇文化生态的稳定性与挖掘和拓展的可持续性。
二、法律困境
古镇到访者一般包括游客、开发商、政府以及当地居民等,由于各主体的利益诉求不同,特别是在商业经济快速侵入与趋利性开发的共同作用下,造成了对古镇空间非保护性的开发,造成历史文化资源的流失与变异。当前相关的法律有《文物保护法》《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规划编制办法》《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规划备案办法》等一批行政法规的出台与实施,为古镇空间文化的发掘在法律层面搭建了一个粗略的保护框架。但这些法律法规都较为原则,可操作性和针对性有一定的局限性。
(一)现有规定缺乏协调性
各地政府在对古镇古村发掘过程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在这两部上位法律强调的“保护性开发”原则指导下,古镇所在区域的地方各级政府纷纷根据古镇自身的特点制定地方性法规,用以指导与规制古镇空间文化的发掘,但由于各方面的因素,上位法与下位法之间的衔接与协调问题较为突出。
1.上位法律较为原则,具体操作性不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在法律内容的制定方面表现出明显的框架性,缺少对古镇空间文化发掘过程中的详细规制,甚至针对一些突出问题没有详尽的解决或救济途径。如2015年“山西大片文物建筑坍塌严重、且盗贩成风”事件中,当地集体、村民拆旧建新的意愿非常强烈,大量古建筑被村民悄悄拆除,地方政府站在文物保护的角度上想制止此类行为,但无法在现行法律体系下找到明确、直接且合理的行政行为依据[3]。此外,在古镇管辖范围的划定上缺少明确规定,全国性法律法规都授权各地方政府管理和保护当地古镇古村,那么在全国和地方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名录之外的其余地方,存在着一些极具保护价值的历史文化遗迹,如何保护、由谁负责保护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同时,古镇古村一般存在于农村地区,农村地区则应当按照基层群众组织自治制度由集体组织自主管理,但位于城市和乡镇交叉地带的古镇古村地方行政主体能否有权管辖,全国性法律中缺少明确的规定。而随着城乡一体化的进程,某些地区行政区划调整后,一些极具开发与保护价值古镇的管辖权归属也极易产生矛盾与冲突,而这些矛盾都需要具体法律来调整与解决。
2.地方性法规违背保护性原则,相关主体权利义务失衡。在古镇古村空间文化的发掘中,对政府行政权介入的程度没有统一的标准,仅仅概括地表述为保护、管理与监督。由于上位法的模糊和原则化,加之各地发掘形式的多样性,地方法律文件中授予各基层政府的职权也形式各样。有些地方政府很容易受到利益驱动,在制定地方性法规时,一味追求短期的经济效益与“政绩”,过分追求商业化开发,完全违背了全国性法规强调的“保护性开发”原则。不仅在地方性立法中放大自己的行政权力边界,扩大自己的行政权管辖范围,减少自己的法定义务,甚至为自己的行政不作为提供“合法”依据,而对于发掘过程中其他主体权利义务也缺少明确的规定,一方面造成了外来投资者越权性开发,带来不可逆的破坏,另一方面造成了古镇内被侵权者无法找到有效的法律救济途径。
(二)利益分配不合理激化主体间矛盾
鉴于古镇古村完整的行政组织以及复杂的产权主体,同时,现有的法律呈现出分散性特征,地方政府在商业旅游短期内获取巨大经济收入的刺激下,主导利益的分配,一味追逐经济效益而忽视了社会效益、文化传承和生态环境的保护,进而导致参与主体间矛盾突出。在涉及到保护与旅游发掘活动中,居民、政府和旅游公司,甚至部分投资者、中小经营者都会参与其中,利益分配成了矛盾指向的焦点。此外,在经济条件良好的地区出现政府强占或联合私人主体强行介入管理古镇古村、抢夺当地居民利益的情况。在古镇政府、古镇居民、古镇外来投资者这三者的利益分配问题上,本可以通过市场为主导的交易方式解决,但行政强制权的介入以及公共利益的诉求,使古镇古村空间文化旅游的利益分配问题进入了公法调整领域。而现行的法律中,没有对这三者的利益分配做出规定,也没有划清其边界,由政府来主导利益的分配这一做法是否有行政权越界之嫌,有待商榷[4]。一旦地方政府在发掘过程中被商业利益冲击,损害地方居民或其他利害关系人的利益,则很容易引起社会矛盾和冲突。
(三)开发审批程序不规范
从《云南省丽江古城保护条例》《平遥县加强对平遥古城内房屋建筑和历史街区保护的若干规定》以及《苏州市古村落保护条例》等相关规定中分析政府的职能应包括如下几方面:第一,对古镇内进行古建筑文物的拆除、改建、添附等实体处置行为的管理权;第二,对古镇内整体建筑与文化氛围、建筑风貌的限制管理权;第三,对古镇内非物质文化遗产部分及生活设施安装或处置的管辖权[5]。然而在古镇的保护性发掘过程中,部分政府并没有行使其管理权,导致第三方外来投资者以及当地居民对古镇进行随意性开发,不仅缺少统一的规划实施方案,同时在利益的驱使下监管呈现出失控状态。很多古镇在商业化开发后,改变了原始风貌,沦为“小吃一条街”“酒吧一条街”,文化氛围完全灭失。无论是对古镇“拆旧建新”的行政许可,还是政府应该行使的行政监督程序,都因为上位法在程序方面制定的不严密与框架化给了当地政府在利益驱使下钻法律漏洞的机会,导致行政乱作为和不作为现象严重。
(四)保护性法律意识淡薄
古镇一般位于相对封闭、偏远的地区,经济发展程度相对较低,古镇的文化教育资源匮乏和古镇居民受教育程度较低,因此很多古镇居民法律意识淡薄,甚至无法清楚地分辨自己行为是否违法以及该行为会造成的法律后果。在市场经济趋利性的影响下,古镇居民很容易为了追求短期利益而做出破坏古镇文物、未经报批私自大拆大建的破坏行为,对古镇空间文化的发掘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同时也不利于保护性发掘长效机制的建立。同时,游客法律意识的高低也直接影响着古镇空间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游客不自觉的破坏行为可能对古镇的建筑或遗迹带来不可逆的毁坏。而现行的相关法律法规对这种破坏性行为处罚力度较小,游客的违法行为成本较低,难以引起重视,因而出现了破坏行为的反复性。这样的情况同样也出现在参与古镇空间文化挖掘的外来投资者中,他们与政府合作,以资金的投入与政府一同发掘古镇旅游资源,但在趋利性的作用下,往往会为实现短期利益而盲目开发,破坏古镇建筑、古镇空间格局的情形。而政府迫于缺少对古镇保护与开发资金的窘境,在很多时候只是象征性的采取惩罚措施。因此,法律意识的淡漠,造成了违法行为的反复性,违背保护性开发原则的现象层出不穷。
三、法律救治
(一)完善法律法规,强化法律法规间的协调性
1.制定具体管理政策法规,奖惩并行。制定文化景观遗产保护责任制度,制定各级文物保护、维护以及利用的相关管理制度。同时,制定协调管理责任制度以及利益分配制度,以明晰行政权在管理过程中的边界,明晰奖励和惩处措施,并以此规范古镇空间文化发掘各方主体的行为,鼓励民众互相监督,充分调动群众参与古镇空间文化发掘与保护的积极性,重点打击只着眼于短期利益的商业开发行为。古镇所在区域的城镇体系规划、城镇总体规划、镇总体规划的组织编制机关,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和专家定期对规划实施情况进行评估,并采取论证会、听证会或者其他方式征求公众意见,保障古镇居民的知情权和参与权[6]。
2.加强规范外来投资行为。外来投资者的投资行为是目前多数古镇空间文化发掘的主力军,但投资者一般注重成本回收和效益优先的原则,过度与盲目的趋利性发掘较多。各级政府应注重以法律及制度的形式规制外来投资者的趋利性发掘行为。制定生态环境保护和人文环境保护优先的原则,从古镇空间遗迹保护、整体文化传承等方面做出具体的规定,鼓励外来投资企业立足于当地的民族、历史文化特色,开展文化传承性、非物质遗产体验性、历史展示性文化旅游开发。同时,严厉打击与处罚外来投资者对传统文化、古镇遗迹、古镇建筑格局破坏性开发,使外来投资者的开发行为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
3.成立专门管理机构,健全责任追究机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细则》第一章第3条规定,主管全国文物工作的国家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是国家文物局。国家文物局对全国的文物保护工作依法实施管理、监督和指导,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保护本行政区域内的文物。目前,多数古镇空间文化发掘基本是突击性、间断性的,缺少长效机制。为实现古镇空间文化的可持续性发展,可成立专门的管理机构,责任内容主要涉及古镇建筑、遗迹的保护、安全评估与检测、文化流失防治等具体事务,同时要明确各机构职能。安排机构或人员定期走访检查,对古镇空间文化的发掘与保护情况登记造册,制订年度工作计划并上报上级主管部门,同时向当地群众进行公示广泛征求意见。在责任追究方面,现行《文物保护法》中对古镇文物破坏的责任追究力度较低,需要进一步健全责任追究机制,对于严重破坏古镇文物、破坏古镇文化生态的行为以《刑法》的相关法规予以处罚。同时,针对于行政主管部门的失职、不作为或越权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此外,管理机构人员进行定期培训,提高工作人员技能水平与自身素质,吸引高校等研究单位或人员入驻古镇成立研究观测点,为古镇空间文化发掘提供科学指导。
(二)健全利益分配机制以化解主体间矛盾
在古镇空间文化发掘中面临的突出问题之一是利益分配机制不健全,过分重视短期利益,导致过度商业化开发。当前由政府主导利益分配的机制,容易产生公权力进入私法领域,与民争利现象。因此,应当在相关立法中明确规定利益分配机制,明确“追求并实现社会效益最大化,兼顾经济效益”的总体原则,禁止行政主体主导的利益分配,通过引入第三方机构或组织,量化且科学地评估各相关主体的投入与贡献,并以此作为利益分配的主要依据,对进行破坏性开发的主体,不仅要减小其利益分配的份额,还要要求其进行补救或缴纳补偿金并由第三方机构或组织使用该笔补偿金用于古镇文化的发掘与保护,并定期向社会各界公布,由社会各界监督[7]。
(三)严格开发审批程序
对古镇空间文化进行保护性发掘是首要选择。政府规划部门必须根据古镇当地的具体特点以保护为原则制定古镇开发的详细规划实施方案,并上报上级行政规划部门审批备案。同时,还需以行政规章的形式把古镇空间文化发掘的审批程序规定下来,并且各级行政审批部门必须严格依此执行,杜绝未经开发审批许可私自乱搭乱建,大拆大建等破坏甚至违法开发行为。在开发审批程序的审核过程中,必须重点评估开发行为与古镇空间文化环境的适应性与融合性。上级行政审批机关要形成长效监督检查机制,层层监管,严厉打击与惩处下级行政审批机关的不作为行为或违法性审批行为,并以此作为古镇当地政府政绩考核的重要指标,同时及时向社会公众反馈违法审批行为的处罚情况,以保障公众的知情权。
(四)强化保护性法律意识
由于多因素的影响,古镇空间文化传承出现代际失衡的现象,需要着重提高古镇居民中青少年群体的古镇文化传承意识。当地的教育部门,可以根据地方历史文化实际,编制相关法律教材,并培养一批专业的培训教师,同时把文化保护的内容纳入当地中小学生的课程培养计划之中,以提升青少年群体的文化传承意识与法律保护意识。成立宣讲团,定期开展宣讲活动,鼓励各年龄层次居民参与,并建立反馈机制。同时,创新政策法规宣传方式,提高法律意识普及效果。大多情况下,居民、游客、外来投资者对于《文物保护法》《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以及地方性法规的了解程度并不高,因此破坏性行为时有发生。各方主体对于自己行为的后果、侵犯的法益都缺乏比较系统而正确的认识。政府应当针对当地法律意识较为薄弱的偏远自然村、集镇重点开展普法宣传工作,向村民重点介绍《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相关重点法条,更正村民错误的法律意识,分析违法行为的严重性,全方面地提高村民参与文物保护工作的法律意识[8]。对于破坏以及违法行为,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在对这些违法行为处以行政处罚之后,可以通过媒体进行曝光,以警醒当地居民、游客以及外来投资者的法律行为。同时,可以在各个入口设置宣传广告牌,在重点文物保护区域设置警示牌,以提醒相关人员注意自己参观游览时的行为,也可在安排讲解内容以及文化体验游的项目中融入传承与保护的法律思想,如“保护历史文物遗迹、参与文物保护是公民应当履行的法定义务,破坏历史文物、遗迹,违反《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的开发建设行为都是违法行为,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的法律意识。只有不断地在法律意识形态方面加强引导与灌输,才能从根源上保障历史文化古镇的文化传承实现可持续性。
有人说过:“制度是最好的老板。”古镇空间文化的发掘与保育,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既要激发各主体的积极性,提高他们的制度意识和规范常识,更要有规划、法律法规、制度规定的合理性与及时性。
[1] 章玉钧.保护古镇传承民俗促进旅游发展[J].中华文化论坛,2006,(1).
[2] “1·25”贵州省镇远县报京大寨火灾事故[EB/OL].百度百科.
[3] 李玲.浅析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及其对策[J].大众文艺,2012,(10).
[4] 孙安军.《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实施》的研究[J].中国名城,2010,(5).
[5] 张炜.我国历史文化名城的可持续发展[J].财经科学,2007,(6).
[6] 张哲,韩凝玉.面向竞争的规则——转型期我国风景资源保护与利用实效管理模式研究[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2.
[7] 邢鸿飞.政府特许经营协议的行政性[J].中国法学,2004,(6).
[8] 许抄军,刘沛林,周晓军.古村落民居保护与开发的产权分析[J].衡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