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物册页
路来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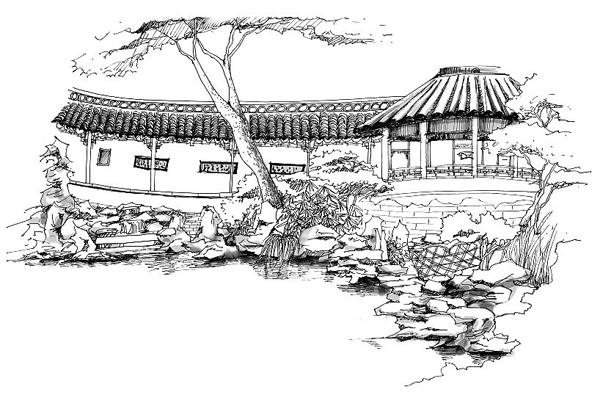
田水清音
田水声,水在田地里流淌的声音。
这很容易让人想到江南,江南的稻田。浅水漫漫,田水清清,清清的田水中,水稻摇曳;稻花上,粉蝶逸飞;稻丛中,一群群稻花鱼,浮游、嬉戏。
田水声,有什特别?
清人李慈铭,有一段写“田水声”的文字,文曰:“予尝谓天地间田水声乃声之至清也。泉声太幽,溪声太急,松涛声太散,蕉雨声太脆,檐溜声太滞,茶铛声太嫩,钟磬声太迥,秋虫声太寒,落花声太萧飒,雪竹声太碎细,惟田水声最得中和之音。”
在这段文字中,李慈铭抓住一个“清”,从下文系列的比较中,可以看出,李慈铭的“清”,主要是指“音之清”——清越、清亮、清畅,怎么理解都好,关键是要扣住“最得中和之音”。
“中和之音”,中正、平和,不急不躁,舒缓从容,田水潺湲地流淌着,让人觉得日子长长,岁月静好。
不過,我倒觉得:这个“清”字,是应当包括“色之清”的——水色之清。
田水长流,泥滓沉淀,稻田里的水,大多的时间,也确实是“清”的。
清且浅,静而柔,若然不是田埂水口水的流动,你几乎,不会意识到稻田里的水是在流的。清亮的田水,那么平稳、那么平静地存在着,能让人看到稻花鱼在水中浮游的身影;稻花纷然落下,飘在田水中,明亮的田水,成为飘逸的稻花的背景,点点如星,浮光闪烁,给人一份碎碎的悦目的柔软感。鱼儿在游动中,唼喋觅食,吞咽着漂浮在水面的稻花,于是,水面冒出一串串气泡;于是,水面荡起浅浅的涟漪,那景象,婉约之极,柔美之极。
若然你站立在稻田边,垂首间,也许就会看到几枚田螺,正附着在稻叶上,或者,正在田水的水底,蠕蠕而动——那水,真是太清了,清澈到万物无处隐藏。
某一个早晨,晴光朗照,一位老农,也许正从稻田边经过,头上戴着一顶斗笠,手中牵着一头水牛。徐徐而行,散漫而从容,影子就倒映在田水中,人移影动,姗姗可爱,是实景,也是画景——风景如画。
所以说,尽管李慈铭的文字,侧重点在表现田水之“清”,带给人的“耳之悦”;但我们,却能从中体悟到田水之“清”,展示给人们的“目之美”。
同样是倾听“田水声”,躬耕陇亩的陶渊明,则是另一番感受。
据唐·冯贽《云仙杂记》记载:“渊明尝闻田水声,倚杖久听,叹曰:‘秫稻已秀,翠色梁(应该是“染”)人,时剖胸襟,一洗荆棘,此水过吾师丈人矣。”
毕竟生活不易,毕竟躬耕艰难,所以,倚杖久听,陶渊明首先想到的是庄稼的长势:秫稻已然抽穗,弥目翠色莹莹。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庄稼有可能的丰收。于是,满怀喜悦,“倚杖久听”的情态,栩栩然,有一份高蹈的生动。
不过,到底是陶渊明,格调,自是高人一等。
他“倚杖久听”,在享受庄稼长势大好,带来的形而下的喜悦的同时,又一步迈上了形而上的高度——“时剖胸襟,一洗荆棘,此水过吾师丈人矣”。
在陶渊明看来,秫稻之翠色,不仅可以“养目”,更可以“洗心”、“养心”——阔人之胸襟,涤人之不快。
在北方,是难闻田水声的。
偶因干旱,灌溉田地,也大多是急水汤汤,浑浊而沉厚。不过,却也别有一番情景,别有一番滋味:老农蹲坐田头,抽着旱烟,静静地凝望着流进田地的流水——是那样的凝重,是那样的期待,你仿佛能从他的眼睛中,看到了厚重缤纷的秋色。
但,欲闻“田水声”之清亮,之纯粹,到底,还是让人思念着江南了。
瓦上烟
瓦上烟,总让人想到江南,白墙黑瓦的江南——石板小巷,一片片的鱼鳞瓦,还有那阴雨连绵,朦胧如翳的梅雨天气。
雨,一直在下,不大,细细的、密密的、软软的、柔柔的,如烟如雾,轻轻地落着,缠绵地绕着,风一起,便游丝一般飘起,却总也飘不远,飘不开;风一小,那雨,便又缠绕起来,绕着一座座白墙黑瓦的江南老宅,慰抚着一片片的鱼鳞小瓦。
时间,在烟雨中苍老着一切;趴在屋顶上的一片片鱼鳞瓦,在江南烟雨中,氤氲出青黑色的苔藓。
青黑色的苔藓,是对时间的记忆。
瓦缝间,或许还生长出一些小草,一些亭亭的莠草。莠草青青,雨雾中,那份青略略有些暗淡,很是有一份幽微的情趣。一只鸟儿飞来,落在黑瓦上,静静地凝视一会儿,然后又霍然飞走了。翅膀扇起的风,拂动了身边的一株莠草,于是,莠草摇曳,莠草摇曳……
静,一切都很静。
巷子很静、很深,极少有人走过。偶或走过的人,我想,应该是一位女子,一位江南女子。手中撑着一把油纸伞,或者花布伞;身上,穿着一条筒裙,一条碎花筒裙。人,行走在小巷中,娉娉婷婷,娉娉婷婷,袅娜美丽得不得了,不得了。
小巷,在女子的行走中,生辉,生香。
老宅,也很静。人,大多在室内,梅雨的天气,适合于待在室内,安安静静的,十分的闲适,异常地温馨。似乎,干什么都好:弈棋?打牌?聊天?女人们,则在绣花,江南女子是应该绣花的,江南女子绣出的花,有水气,有灵气——是水灵灵的江南花。老宅,有天井,天井是用来“望天”的,望天的,应该是一位老人,老人走出老宅,站在庭院中,望向天空,然后,望向屋顶,望向屋顶上氤氲的雾气、水汽,还有烟气。
一片一片的鱼鳞瓦,瓦上,缠绕着水的烟,汽的烟——瓦上烟。
瓦上烟,江南的瓦上烟,总让我想到静、柔、绵、幽等等的字眼,我觉得,江南的瓦上烟,就是宋词中的一首婉约的小令,是元曲中的一首略带伤感的小调,是戏曲中游逸缠绵之极的昆曲。
烟雨天气,江南老宅,似乎最是适合拍曲了。拍曲就请江南女子单雯来唱,唱一曲《牡丹亭·寻梦》:
最撩人春色是今天
少甚么低就高来粉画垣
原来春心无处不飞悬
是睡荼縻抓住裙钗线
恰便是花似人心向好处奔。
缠绵、柔软,百转千回,低回不已。太美,太美,美得让人心碎。听着,听着,就禁不住让人热泪盈眶,热泪盈眶。
江南晚烟,也好。雨停了,天晴了。黄昏时分,家家户户都做起了晚饭。灶烟升起,瓦缝中,丝丝缕缕地冒出,弥漫着,弥漫着……
天边,晚霞如火,辉映着大片翠绿的竹林;竹林青青,青青,遥望着屋瓦上的炊烟。这种遥望,遥望了多少年?多少年?这是一种人与自然的对望,这是人与自然对望中,形成的一种默契,天人合一,大约就是如此罢。
水田边,灰黑色的水牛,仰起头,哞哞哞叫了起来;牧牛的少年,顺着水牛的叫声望去,望到了屋瓦上升起的炊烟,升起的炊烟。
于是,少年手中的柳条一挥,水牛蹒跚、迤逦;他们一起,走上回家的路,去寻找自家的“瓦上烟”。
夕阳满扉
柴扉,柴门也。
从前,庄户人家,穷家敝户,难得有青砖红瓦之家。大多是草房陋室,篱笆院墙;大门,则多为柴木捆扎而成,文人雅称之为“柴扉”。
柴扉,大多与田野相望;闭扉,严严一户人家;敞扉,则与田野浑然一也。
故尔,柴扉,别有一番情味。
史震林《西青散記》:“秋末阴凉,黍稷黄茂,早禾既获,晚菜始生,循田四望,远峰一青,碎云千白,蜻蜓交飞,野虫振响,平畴良阜,独树破巢,农者锄镰异业,进退俯仰,望之皆从容自得。稚儿渴,寻得余瓜于虫叶断蔓之中,大如拳,食之生涩。土飞掷,翅有声激激然,儿捕其一,旋令放去。晚归,稚儿在前,自负棉徐步随之,任意回答,遥见桑枣下夕阳满扉,老母倚门而望矣。”
此段文字,写秋日拾棉晚归,乡野情景,历历然;田园风情,茂茂然。可谓文笔舒徐,从容自得,一派风雅,尽得于“无意”间,真乃自得之文,自在之文也。而最得人心之处,则莫过于最后几句:“晚归,稚儿在前,自负棉徐步随之,任意回答,遥见桑枣下夕阳满扉,老母倚门而望矣。”
“夕阳满扉”,洋洋溢溢的,是一派秋日的暖煦;“老母倚门而望”,则亲情融融,依依,让人生无限怀想。
读此文,就每每让我想到自己小的时候。
旧家,位于村庄的最西头,除东邻之外,三面为田野环绕。一圈篱笆扎成的院墙,除却冬日,总有藤蔓类植物璎珞其上。风来摇摇,篱垣堆碧,唯柴门豁然一缺口,眼睛一般遥望着门外的田野景象。
每至饭时,母亲便推门而立,站立柴扉之前,大声吆喝:“哎,吃饭了,吃饭了……”一声声,一声声,声播四野。
我们兄弟姐妹,听到母亲的吆喝声,便从四面八方,纷然归来。如燕子归巢一般,回到家中,回到饭桌前,回到母亲身边。母亲,见孩子们都回家了,便也回转身体,进入柴门,随手又把柴门一扣,啪啦一声,身后余音簌簌,簌簌……
冬日上学,晚学归来,远远的,就能透过篱笆柴扉,看到房中的一豆灯光,忽明忽暗地闪烁着;等到走近家门,即发现柴门前影影绰绰的黑影——母亲,正依柴门而立,依柴门而立。
刘长卿《逢雪宿芙蓉山主人》:“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诗情画意里,别有一份悲戚和苍凉,但更有一份期待的温暖。想来是写实,但却更写出了一种共性,一种山村人家特定时代的特有共性。对我来说,就是儿时的许许多多的切身经历和感受。
“夜归人”,是朋友归来,抑或是赤子归来?但不管是谁人归来,都有一份对家的向往,都有一份家人的期待。虽是蓬门荜户的柴扉人家,但是,只要“归来”了,你就拥有了一个温暖的家。
多少年后,我回忆、联想至此,就觉得,那柴扉,是风景,是田园,更是母亲的一种遥望和期待。倚柴扉,则是众多的乡村母亲的共性行为,那是母爱的一扇门,是母亲用爱铸成的一个“特写镜头”。
夕阳满扉,亲情依依,乡情依依。
黄蜂·野篱
黄蜂,旧时的乡村,可谓随处可见。
树枝间、篱笆下、屋檐处,举目,即能看见它们垒下的蜂巢。太阳一出,温度升高,黄蜂们就离开蜂巢,四处游走飞舞。
而黄蜂,最喜欢栖落的地方,就是篱园。
篱园,对,篱园。从前的乡村,是几乎家家都有一处篱园的,在村口,或者,在房前屋后。篱园的构建,很简单,用一些枯败的树枝,或者一些高粱、玉米的秸秆,扎下,环绕圈起,就可以了。
春天里,乡人于篱笆边,种下扁豆、豆角、丝瓜等藤蔓类植物;篱笆外,则种植一些向日葵,如此高低搭配,完美矣。
春芽夏长。
进入夏天,藤蔓类植物,爬满了篱笆,璎珞其上,绿意婆娑,姗姗可爱。篱笆外的向日葵,则亭亭玉立,与篱笆上的藤蔓植物,俯仰相就,欢喜如一家人。
扁豆开花了,红的、白的、紫的,很是有些姹紫嫣红,乱人眼目;丝瓜也开花了,丝瓜花则纯然一黄,嫩嫩的黄,婷婷然,大有出篱之欲;向日葵,开的是大大的花盘,粉黄的嫩蕊,一圈整齐的肉黄色花片,像一只欲望的风情的眼睛,瞭望着太阳下这个乾坤朗朗的世界;风来则花摇,尤为灼人眼目。
花开的时候,虫鸟儿们就飞来了。窈窕的黄蜂、肥硕的大黑蜂,娉婷的蜻蜓、蹀躞的飞蛾,有时,还会飞来几只知了,飞来一些鸟儿……
于是,一圈篱笆,就热闹了;于是,就忙坏了那些顽皮的乡村儿童。
捕飞虫,弹鸟儿……游戏,在烂漫的夏日绽放。
“闲扑黄蜂绕野篱,尽横小扇觅蛛丝”,这样的一些诗句,就是描写乡村儿童那些的游戏活动的。
那个时候,还没有“护鸟儿”的观念,弹鸟儿,就成为了儿童的一种很重要的游戏。不是冬天,难以像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所写的,用竹筛扣捕,于是,就只好用弹弓弹射。远远地站立着,拉紧弹弓,瞅准鸟儿,弹子射出,鸟儿击中,扑扑棱棱地飞几下,便啪嗒一声掉落到地面上,儿童们呼啦啦一拥而上,那份欢喜,真是难以言说。当然,很多时候,是击不中的,鸟儿受惊,霍然飞走,鸣叫着飞向远处,或者飞向高空,儿童们便只好眼巴巴地望着,望着……
正午,天热的时候,知了叫得最欢。“知了,知了……”一声声地叫着,把个夏日的中午叫出阵阵热浪。可知了太过机警,人一靠近,它就不叫了,人再靠近,知了便蓦然飞走。
最有意思的是捉蜻蜓,也只能用一个“捉”字。蜻蜓辍在花枝上,稳稳的,像一架架等待起飞的小飞机。儿童们蹑手蹑脚,慢慢地靠近蜻蜓,然后迅速伸出两个手指,一下子就把蜻蜓的尾巴“捉”住了。知堂老人在《苍蝇》一文中,写他们小时候玩捉苍蝇:“我们又把它的背竖穿在细竹丝上,取灯芯草一小段放在脚的中间,它便上下颠倒地舞弄,名曰‘戏棍;又或用白纸条缠在肠上纵使飞去,但见空中一片片的白纸乱飞,很是好看。”感觉,天下儿童的游戏,真是“异曲同工”。我们捉住蜻蜓,也大多是在蜻蜓的长肚上缠上花色纸条,让它在空中飞舞,亦是感觉“好看”。
黄蜂蜇人,捉黄蜂只能用网捕,长长的竹竿上,拴上一只丝网,远远地瞅准,一下子就把黄蜂扣住了。
捉黄蜂干什么?也只是觉得好玩,也只是彼时儿童的一种游戏罢了。
知堂老人,曾经多次在文章中感叹彼时缺少体现儿童游戏的书籍;如今,我感叹的是:现在的儿童,还有这样的贴近自然的游戏吗?
俱往矣,似乎,一切只能存在于回忆中——我想念从前的篱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