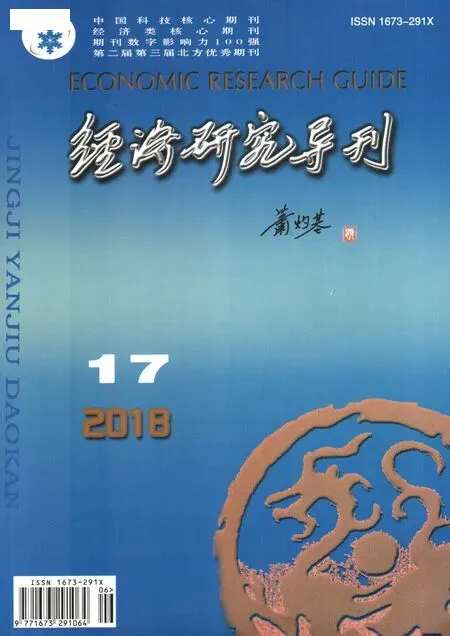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战略机遇加快高端装备制造业战略转型
王向军,杨 漾,吴艳强
(上海市教育发展有限公司,上海200011)
引言
我国“十三五”时期,正值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又适逢新一轮科技革命的“窗口期”,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战略机遇,不仅关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成败,而且关系第二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最终实现。随着新工业革命闸门的慢慢打开,作为我国“工业4.0”技术依托的“互联网+”正在继续与各产业进行互融互通,发挥自身价值。在“互联网+”政务服务中,将实现政务部门数据共享、信息透明;在“互联网+”中国制造中,将实现制造业智能化、数字化、网络化,继而整合区域资源,提高产品质量,发挥工匠精神;在“互联网+”绿色生态中,将实现对全国排污企业进行实施监控,倒逼环境技术,促进可再生资源的利用;同样,在“互联网+”医疗卫生、教育中,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1]。当智慧城市(互联网+物联网成为传统产业后)作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业态出现后,下一个风口必定是资本+实业的再次兴起,实业兴企、实业报国成为国企主流。先进智能制造业将有更大的市场和舞台。一是国家医疗设备创新体系建设,力争在自主创新的基础上,实现医疗设备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即医疗仪器设备的工业4.0时代到来了。二是国家教育装备创新体系建设,力争在智慧管理的基础上,实现青少年素养全方位塑造的环境模拟、实操平台、技能培训、评估测试,即教育装备的工业4.0时代到来了。
一、我国医疗、教育装备制造业的发展现状
坚持市场为导向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原则,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目前,我国装备制造业优势主要在低端装备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实力与发达国家差距仍然巨大,医疗、教育行业还存在一些主要矛盾。
(一)医疗设备行业市场发展
我国医疗器械企业普遍实力较弱,企业规模较小,外资、合资企业占到半数以上;多散布在全国各地,缺乏有机整合;自主研发能力不强,产业的竞争力较弱,缺乏高附加值的产品,拥有的核心技术和品牌不多。制约我国医疗器械产业发展的主要因素是缺乏核心技术和关键材料。出于国际制造转移和靠近市场等目的,发达国家和地区将一部分医疗器械制造产业转移到我国,但重要设备的核心技术和关键材料并未向我国开放。发达国家和地区通过对新技术、原材料和新产品的控制限制了我国医疗器械产业的发展。此外,缺乏整体规划,我国中低端医疗器械产品产能过剩,市场的过度竞争浪费了大量资源;产学研用互动不足[2]。
大型医疗设备关键技术长期被国外公司垄断[3]。目前,国内高端医疗器械设备市场的70%已被跨国公司占领。甲类设备包括PET/CT、伽马刀、质子治疗系统以及其他在区域内首次配置的单价在500万元以上的医用设备等;乙类设备包括CT、核磁共振、血管造影X线机等。其中,PET/CT和头部伽马刀被作为需要监管的主要甲类医疗设备,如放射诊疗方面有GE、西门子和飞利浦,微创诊疗方面有强生、西门子等,生化检验方面有奥林巴斯等。当前,国家在战略上高度重视医疗设备产业发展,大力支持并引导国产医疗设备夺回国内市场,杀入国际市场,并对高性能医疗器械的具体规划定了基调,国产医疗器械,尤其是高性能医疗器械破局在即。
(二)教育装备行业市场发展
目前中国教育装备行业处于市场全面竞争态势,从产品集中度来看,众多教育装备品牌企业之间激烈竞争倒逼企业不断研发新产品,行业集中度较低。国内教育装备龙头企业及品牌企业有实力自主研发高附加值教育装备产品并占据高端市场,但在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教育装备产品市场,众多中小教育装备企业之间产品同质化程度严重。随着教育装备产业升级的不断加剧,行业内竞争将越来越注重产品科技含量、档次、更新换代等方面的问题。中国教育装备行业发展潜力巨大,拥有千亿规模的产业巨量,市场吸引力强,随着国内教育事业的高速发展,学校、教育机构及销售商对教育装备的需求越来越大,智能化、数字化教育装备趋势已经逐渐的被人们所接受和认可。在中国教育装备行业面临发展机遇的同时,国外教育装备企业及产品逐步进入中国市场,随之而来的外部冲击也加大。
二、新科技革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工业革命均是通信技术与能源技术的结合,进而引发重大的经济转型。19世纪蒸汽机的使用,导致了报刊、杂志、书籍等通信手段及相关产业的大量出现,使人类能够对以煤炭为能源的蒸汽机以及工厂进行系统管理和操作,产生了第一次工业革命。20世纪出现的电话、无线电通讯和电视等通信技术,催生了全新的信息网络,与燃油内燃机的结合引发了第二次工业革命,使人类进入到石油经济和汽车时代。互联网技术与可再生能源的结合,将使全球出现第三次工业革命。当前,全球经济危机的本质是以化石燃料及相关技术为基础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已日薄西山,无法再支撑世界经济的发展,而以新能源与互联网技术为特征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是摆脱经济危机的必由之路。新产业革命将是以新生物学革命与信息转换、再生技术为核心引领的变革[4]。与以往历次科技产业革命不同,新一轮科技产业革命的显著特征是信息技术、互联网技术的深度发展及其与生物、能源和材料等多学科、多技术领域的相互渗透、交叉融合及群体突破,并促使产业领域颠覆性技术不断涌现、新的产业组织形式和商业模式层出不穷。
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推动生产方式变革和新兴业态产生,将助推高端装备制造业转型升级。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发展和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对高端装备制造业的绿色化、智能化、服务化将提出新的市场需求。我国在推进信息技术与制造技术深度融合方面,积累了大量实践经验和技术基础。全面深化改革,必将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破解产业转型升级体制机制和技术资源瓶颈,为推动高端装备制造业由大变强提供动力支持和体制保障。“一带一路”对于高端装备制造业在新兴市场国家实施“走出去”战略提供了机遇。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业面临着高端回流和中低端分流的双重挤压。发达国家纷纷实施以重振制造业为核心的再工业化和制造业回归战略,抢占国际产业竞争制高点。新常态下,国内经济转型对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出了紧迫要求,高端装备制造业亟需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国际市场需求下滑甚至萎缩的风险加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对我国高端装备出口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
三、我国医疗、教育高端装备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实现路径
(一)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完善创新体系建设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一是让企业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激活“企业实验室”的创新功能,弘扬以创新为核心的企业家精神;促进传统企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以数字经济、智慧经济引领企业转型发展;推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互补创新。二是提升科技创新的效率,完善产学研用相结合的高端装备制造业产业创新体系[5]。提高创新设计能力,加强核心技术、关键技术转化成先进制造基础工艺技术的能力。深化体制改革,强化创新激励。三是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减少政府部门对创新资源的直接分配;大力发展市场化、专业化、社会化创新服务机构和组织;加强统筹协调和顶层设计,建立统一的信息化服务平台。
(二)培育具备系统集成能力的装备龙头企业
未来企业的竞争既不是产品的竞争,也不是产品服务的竞争,而是商业模式的竞争。随着装备产品竞争日趋激烈,装备行业领导企业开始重点构建系统设计和系统集成方面的核心竞争能力,逐步外包或者剥离产品的生产部门。国外大型装备制造企业往往通过这种模式占据“微笑曲线”的两端,也即集中于研发、市场渠道、总包服务,通过构建完善的产品线和先进的项目解决方案能力,不断增强自身的技术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能力。为了增强我国重大装备的成套能力,政府应积极引导和推进装备行业的市场化兼并重组,致力于培养一批能带动装备产业发展、具有国际先进水的大型成套装备龙头企业集团,对全行业的发展起到巨大的带动作用。此外,龙头企业通过供应链的整合和管理,带动缄默知识在集群内上下游的扩散,提升整个产业集群的技术创新能力,有助于解决我国中低端制造业普遍存在的低端化、模仿化、同质化、个体化、偶然化的低质低价竞争模式,带动区域产业结构的升级。
(三)发挥国有企业在高端装备制造业中引领作用
国有企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顶梁柱,将义不容辞地承担起自己的历史使命,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技术标准的制定,更好融入全球创新和产业分工体系,加快培育世界一流企业。坚持主业为本,一张蓝图画到底。国企布局、产业分布、错位发展、协同有序。面对欧美国家重新回归制造业和“再工业化”战略,《中国制造2025》战略[6]是培育我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优势的必由之路。在实施高端装备创新工程中国有企业将承担主力作用。
(四)优化高端装备制造业的人才培育机制
人力资源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是技术创新的关键,装备制造业向高端发展从根本上依赖于国际一流的工程技术专业人才。针对我国装备制造业人才短缺和人才流失的严峻局面,必须加强装备制造业的人力资源发展和优化配置工作,培养企业所需要的专业技术人员。从前沿科技突飞猛进、制造学科交叉综合、企业对于技术人才需求的实际出发,重视培养具有综合知识基础、职业训练和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和工程管理能力的创新型人才。人才激励机制方面,消除专业人才的市场化流动的障碍,创造条件鼓励专业人才进行创业。
(五)营造有利于中国高端装备制造业发展的政策环境
建立健全相关政策和法律体系。完善资本市场结构鼓励企业继续加大研发投入。鉴于高端装备制造业的行业特点,企业需要巨大的资金进行研发,中国高端装备制造业企业需要努力提高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努力拓宽融资渠道。积极搭建创新平台。积极申报和搭建创新平台,并完善创新平台的评价体系,提高整体研发能力和服务水平。可以采取政府和企业出资的方式,保证创新平台的整体质量,将其打造为提供研发创新、成果转化再到市场化产业化一条龙服务的高端制造业创新平台。
(六)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企业群体,推进中国装备“走出去”
培育发展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企业群体,是我国成为装备制造业强国的重要支撑。要努力造就一批在国际产业分工中处于关键环节,具有产品、资本和技术输出能力的大企业,同时还要着力培养一大批“专精特”高成长性的中小企业群体。要充分利用全球创新资源,以构建国际竞争新优势为目标,加快装备制造业“走出去”的步伐。
(七)重拾我国装备制造全球价值链阵地
我国装备制造转型中,要着重填补国内工业基础技术的缺口,改变核心零部件和先进材料过度依赖进口的现状;努力提高生产效率,从粗放式的生产模式向精益模式转变;重视工艺和制造过程的研究和生产过程的管理,不断提升产品质量;努力研发核心生产设备和智能设备,并对设备的使用进行精细化和信息化管理。同时,要注重原始想法的创新,提升产品的服务能力和可持续赢利能力,以顾客端的价值缺口为导向创造新的市场机会,利用增值服务提升我国工业产品的核心竞争力。
(八)构建智能化、网络化、绿色化和服务化新型制造体系,推动制造强国建设
围绕“中国制造2025”战略和“互联网+”战略,以智能化、网络化、服务化和绿色化为方向,全面推进制造业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和服务创新,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培育若干世界先进制造业集群[7]。
四、展望
在新一轮科技产业革命背景下,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及其与新能源技术、生物技术及新材料技术的交叉融合,将对全球创新驱动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产生颠覆性影响。
(一)信息技术的主导地位将继续提升,生物技术有望突破
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广泛应用和新兴产业的蓬勃发展,将推动人类社会由信息时代迈入后信息时代、智能时代。基因测序、干细胞与再生医学、分子靶向治疗及远程医疗等技术大规模应用,合成生物学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二)未来可实现智慧工厂的无忧虑制造
在工业4.0的工厂中[8],自我意识和自我预测的功能成为监测和控制系统的新功能。机器的健康可以通过零部件健康状况的融合和同类机器的对比来预测。零部件及装备层面智能化,实现自省性、自预测性和自比较性。实现全生产系统层面的智能化、无忧虑的生产环境。
(三)个性化、定制化生产方式成为主流
人机共融的智能制造模式、智能材料与3D打印结合形成的4D打印技术,将推动制造业由大批量标准化的生产方式转变为以互联网为支撑的智能化大规模定制生产方式,提高生产制造过程的自动化、智能化、柔性化和绿色化水平,促进制造业向产业价值链高端迈进。
(四)形成全球一体化产业价值链体系
全球研发设计、生产制造以及服务交易等资源配置体系加速重组,异地设计、就地生产的协同化生产模式将被广泛接受和采用,制造业分享经济、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及精准供应链管理等将加速重构产业价值链体系。
我们必须清醒的意识到,过去30多年经济的成功,是建立在工业化和装备制造业在国际上竞争力的提升上的,国际竞争力和装备制造业休戚相关。未来在国际上的地位,仍然取决于制造业能否从大到强。面对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挑战,装备制造业仍然是大国之重器。我国科技创新已步入以跟踪为主转向跟踪和并跑、领跑并存的新阶段。目前,发达国家纷纷以“深度技术”抢占全球价值链的高端,领跑新一轮科技革命。我们目前在人工智能、生命科学、新能源、新材料等“深度技术”的核心领域超前部署,有望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相信经过不懈努力,我国一定可以在世界中、高端装备制造的市场中形成较强的国际竞争力,逐步迈向制造强国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