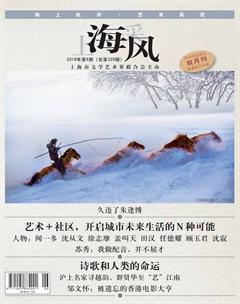对话黄磊:走出乌镇,哪怕灰头土脸的生活迎面扑来
刘莉娜
我还记得第一次去乌镇戏剧节采访,是2014年10月中旬,第二届。那一年家里孩子刚上一年级,放学丢了文具盒,从上海不知所措地打电话来求助妈妈。我一边接电话一边在乌镇陌生而错综的小桥流水间发足奔赴黄磊的采访之约,每一座桥都很像,每一条石板路都不知通向何方,一通电话打得心不在焉,最终孩子委屈地问:“妈妈你在哪里,干什么啊?”五年之后,乌镇戏剧节办到第六届,孩子也即将从小学毕业,由于每年都要来戏剧节,在电话里已经可以熟门熟路地告知:“妈妈你忙你的,我到了先一路看表演,我们可以约在望津里的桥下见。”
顿生感慨。
短短五年,乌镇戏剧节又何尝不像一个飞速成长的少年,转眼就从懵懵懂懂变得明眸善睐。还记得当年采访黄磊,他在乌镇有个宅子,小小的院子里种了树,砌了个方方的泳池,那天他搬了两把竹椅与我对坐,说到筹办戏剧节最初的那些艰难和对不可见的未来的执著时,他转眼望向泳池安静了好一会儿。秋天的泳池落满枯叶,又寂寞又平静,我也移开目光,假装他眼里的水光是倒映的池水。
那一年乌镇戏剧节办到第二届,资金上全靠发起人之一、文化乌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向宏一力承担,压力不小;而作为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国际戏剧节”,在剧目统筹上又陷入了某种悖论——想要做出知名度必须把控质量,就要邀请国内外的名剧名团,而名剧名团特别是国外的那些,又怎会轻易应邀去一个“都没有听过名字的小镇的新兴戏剧节”?可以说,在最初两届,三位同为“发起人”的戏剧人黄磊、赖声川和孟京辉几乎绞尽脑汁、用尽人脉,搭上了所有的私人关系。比如赖导在国际戏剧圈比较有影响,就拿自己的作品做品质保证,用《如梦之梦》做开幕大戏,说服外国人相信乌镇戏剧节的水平。“而我呢,那几年我见人就说有这么个事情,您能听我说说么?您愿意一起做这个事儿么?您可以来参加参加么?说得多了,就像洗脑一样,人家面上不说心里估计都烦了。”说到这里黄磊笑得一脸了然,“我知道很多人当面答应着,附和着,‘到时候一定去或者‘太棒了,其实是给我面子,心里并不相信我能做成那么大一个梦。但我告诉自己,我就当成他们的答应是真的了,当戏剧节渐渐有轮廓的时候,我真的会去再次邀请他们。”有些人就这么依约而来,而另一些人也许还不那么确信,所以踌躇着婉拒:“正好撞上事儿了,明年吧,一定去。”黄磊也就依然“当他是真的”,到了第二年依旧去约,于是更多的人就这么被“洗脑”而来,却在乌镇真正被惊艳到了,转头成了帮他“洗脑”别人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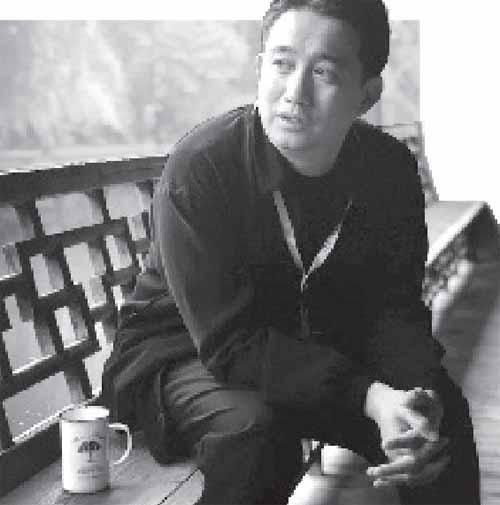
“我的梦想有点大,”我还记得那年的黄老师在自家暮色四合的庭院里说起这个,眼神明亮:“我希望所有爱戏剧的人都想来乌镇戏剧节,所有来过乌镇戏剧节的人都会爱上戏剧,我知道这可能需要很多年,没关系,但梦总要有的。”结果大概他自己也没有想到吧,没有“很多年”,只有短短五年,他那半自嘲半自勉的“春秋大梦”就落地了。如今,从第一年的10天6部戏,到今年的11天24部戏,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剧团带着自己的作品来到这个水边的小镇,因为他们知道这里有中国最好的戏剧观众;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从全国各地来到这里,把自己封闭在小小的西栅,不是在看戏,就是走在去看戏的石板路上。
“一直以来我都会被无数次问到,为什么是乌镇?”今年黄磊并没有把采访约到自家小院,而是选择了秀水廊旁边一段安静的河边木廊,时而有游客走过,认出了他,隔着河张望一下,然后走开。黄磊笑说,“这在北上广我得被围观投喂。为什么这里不一样?因为这里纯粹。乌镇有它的天时地利人和,它把那么多人那么多戏关在一起,你去看戏,看完戏,出剧场,也不用担心地铁末班车,也不用急着抢taxi,你只能石板小路走一走。身边都是和你一起散场的人,你听他们说戏;饿了去路边吃碗馄饨,也没包间也没雅座,大家坐在很近的距离,还是聊戏。这种纯粹的生活,这种单一的快乐,一年有一次,就足够幸福了。”
“可是只有11天。”我听得心动又惆怅。
“即使只有11天。”黄老师说得温柔又坚定,“你在这里得到的美好,足够让你包容外面世界的不美好。走出乌镇,哪怕灰头土脸的生活迎面扑来。”
记者:五年前你在游泳池边述说的“梦想”几近实现,今天我过来的一路上都是美好的年轻人,各种肤色,快乐,热情,仿佛全世界爱戏剧的人都在这里了。那么之后呢,你对乌镇戏剧节还有下一个五年的梦想么?
黄磊:还有两个(黄老师real实诚)。一来我希望在现有的相对高端的“特邀剧目”和相对群艺化的“小镇嘉年华”之间,增加一个“OFF”的部分。就像阿维尼翁或者国际上几大知名戏剧节那样,OFF的参与形式与IN不同,它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选拔机制,而是向所有戏剧人和戏剧爱好者完全开放的平台。在有作品的前提下,只要能找到剧场的空档期,租下一个时间段,在OFF组委会上报名注册一下自己的演出信息,自己搞定签证食宿,就可参与进这场戏剧的盛事中。如果这个梦想实现了,乌镇戏剧节的剧目数量和丰富度都会得到一个大大的飙升,整个戏剧节的体量会成倍扩大。
另一个梦想,也是我做了很久的一个梦,就是我想开办一个艺术大学。民间的,关于戏剧的,最好的大学。我一定会请国内外最好的戏剧大师来上课,但他们不止是老师,他们会和来报名的那些真正有戏剧梦想的人一起学习、探索。而我招的学生也不用是专业的,有戏剧背景的,只要你对戏剧有爱好,有理想,就可以来报名,不管你是大学生,还是卡车司机,你都能来。
记者:听起来第二个梦比较飘渺……那这所大学能毕业么?

黄磊:能啊。当然会有专门的课程设置和考核,毕业了我们也发毕业证书——就是这个毕业证可能对你找工作没什么用处,但对你的内心一定是有意义的。其实这件事我一直在推进,也有了一定的进程,它是我乌镇戏剧节之梦的一个延续,但也可能落地后会成为戏剧节乃至整个中国戏剧教育的源头活水,谁知道呢。还是那句话,梦想总要有的,也许实现它需要很多年,也许只要五年,也许就在明天。
记者:说到戏剧教育,我看到一个现象,就是随着乌镇戏剧节的名气越来越大,以及你的明星朋友们带来的粉丝效应,戏剧节这两天乌镇也成为“网红打卡地”了。但这些“网红”少男少女们来到这里却并不是看戏的,甚至有的跟风看了,却在网上大力吐槽看不懂,这些难免与你的初衷背道而驰。
黄磊:我这几天也看到很多小网红在拿着自拍杆拍直播啊,很好很好,欢迎欢迎。我一直觉得,我们做的这些,起点是戏剧,但终点一定不是戏剧。那些小网红跑来不是为了看戏的,但是他到处走走到处拍拍也很好啊,秋天这里多美;这里铺天盖地的海报,万一有个小网红觉得,这张海报超好看,我去看看这个戏吧,这多好,哪怕只是想想,他就与戏剧有联系了;如果他看完之后觉得,这都什么啊,看不懂,我要上网骂骂它,也很好啊,至少他对戏剧有了体会、有了感知,甚至有了思考。我欢迎各种年轻人来到这里,也许他看不懂戏,但一定有他看得懂的东西,比如擦肩而过的文艺小哥哥,比如美,比如愛。
记者:我记得第一届第二届戏剧节的时候,都有邀请乌镇西栅的原住民看戏,嘉年华也总有大量本地人围观,现在办到第六年,你感觉戏剧节对乌镇这个地方和这个地方的人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黄磊:这很难说得清,在我看来,回报不是直线的,联系也不是直接的,这里的蝴蝶扇动翅膀,会给地球另一端带来一场风浪,这世界还有这样的联系。并不是让所有乌镇人都走进剧场看一场戏就是联系,事实上,通过这六年的戏剧节,乌镇本土的戏剧有了国际舞台,乌镇的年轻人有了世界格局,乌镇的孩子们从很小就知道“看戏”,这些都是戏剧节和乌镇之间彼此产生的联系和影响。甚至不止是乌镇人,我的梦想是,有一天你去国外旅游,你说自己来自中国,外国人的第一反应千万不要还是“哦~熊猫!或者,哦~功夫!”而是,哦,中国,那里有乌镇戏剧节!就像阿维尼翁,就像戛纳,一个小镇因为丰盛的文化而走向世界,那种文化自豪感,和他们乌镇人有关系,和你们上海人有关系,和我们北京人有关系,和每一个中国人都有关系。我有三个孩子,我希望他们长大了都能体验到这种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