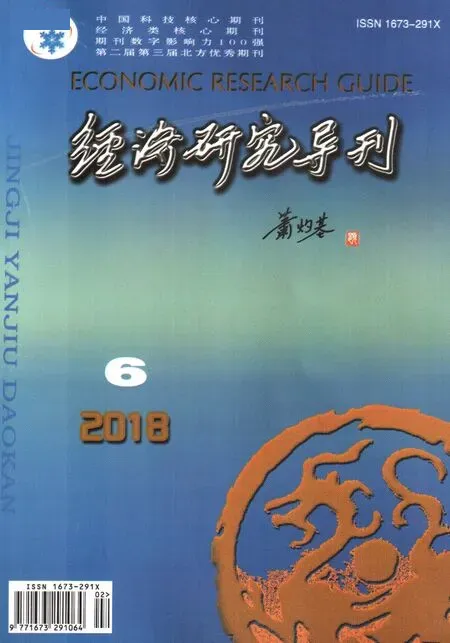微观视角下成都创业城市建设研究
黄 超,史振华
(1.四川水利职业技术学院,成都 611139;2.香港商报四川办事处,成都 610031)
2015年5月,清科集团首次提出区域股权投资已形成北京、上海、深圳加成都、武汉的“3+2”格局;7月,阿里研究院等机构提出“中国硅谷”将集中在成都等六大城市;8月,《财富》杂志将成都列为“2015年中国十大创业城市”;9月,清华大学启迪创新研究院公布2014年《中国城市创新创业环境排行榜》,非直辖市中成都仅次于深圳、广州,排名第三。这些知名、权威的报告说明,成都“创业之城、圆梦之都”的新名片已实至名归。成都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成都“创业天府”行动计划(2015—2025)的通知》,明确提出发展目标:到2020年,形成全域覆盖、功能完善、特色突出、全国领先、示范带动的创业支撑体系。
当前国内创业城市的研究,鲜见成熟、系统的本土化理论,主要是引用美、英等国的理论,其中以GEM——全球创业观察最为普遍。但是,不同地区创业环境有所区别,不必囿于GEM而削足适履,需要因地制宜、量体裁衣[1]。不同的区域形成的差异化创业环境,既能突出各自的优势,又能形成协作互补关系。
一、具有代表性的创业城市环境研究
创业环境是对创业要素和创业活动能够产生影响和发生作用的各种因素及其相互关系的总和,是创业的基本条件,具有客观性、复杂性、变化性的特点。现有研究,对创业环境的研究主要有以下理论:
1.量化评价论。全球创业观察(GlobeEntrepreneurshipMonitor)由英国伦敦商学院和美国百森学院共同发起成立,采用模块化和量化的方法对创业环境和创业活力进行评价。该模型从生态系统学角度将促进经济增长的条件分成一般环境条件和创业环境条件,创业环境分为金融支持、政府政策、政府项目、教育与培训、研究开发转移、商业和专业基础设施、市场开放程度、实体基础设施、文化和社会规范九个方面。
2.制度环境论。Spencer和 Gomez(2003)认为,创业环境本质上是一种制度环境,制度环境由规范的制度(NormativeInstitution)、认知的制度(CognitiveInstitution)和规制的制度(RegulatoryInstitution)三个维度构成[2]。
3.环境分类论。罗山(2010)从创业主体之外的角度观察,认为创业环境包括主观要素(创业能力)、客观要素(外部的支撑条件),客观要素又分为有形要素(基础设施、配套服务设施、硬件手段及其他有形要素)和无形要素(政策环境、政府服务能力、创业氛围及其他软环境),还从先天要素和后天要素角度进行了解析[1]。
二、创业环境研究评析
上述富有代表性的理论,从不同角度对创业环境进行解析,开启了科学认识创业环境的大门,使得创业政策的设计更具系统性、科学性和针对性。但与此同时,这些理论都站在创业环境的宏观角度,在整体上对与创业有关的因素进行属性分类,相比于直接针对创业活动真实需要的微观角度,具有一定的不合理性。
1.缺乏针对性。上述理论都将着眼点放在环境本身,就环境本身中与创立和经营新企业中的因素按重要性、关联性进行分类提取,忽视创立和经营新企业的真实所需。2006年,《中国城市创业观察报告》利用回归模型计量分析了环境因素对机会的贡献,发现专家与企业家对创业机会的影响因素差异非常明显,专家认为政府项目、创业文化、市场开放程度是创业机会的主要影响因素,而企业家认为创业文化和市场开放程度是创业机会的主要影响因素[3]。所以,创业活动真实所需与我们观念中的创业所要具有一定的差异性。从创业活动真实所需,从企业家、创业者的角度来分析各因素的关联程度和重要程度,更具针对性。
2.忽视差异性。由于忽视创业活动真实所需,上述理论过多地根据不同的属性将创业环境进行分类,不同区域的创业环境从整体性而言似乎具有同一性。其实不然,不同的政治法律环境、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不同的产业结构、不同的经济水平、不同的资源禀赋条件,创业活动本身就存着鲜明的差异。所以,立足于区域创业活动真实需求的创业环境各要素的重要性程度不同。
3.忽略微观创业对环境的反作用。创业环境中政府和社会的力量,可以营造鼓励创业、帮助创业、服务企业的氛围,对创业活动非常有必要。但这些毕竟是外部因素,创业环境是外部因素与内部因素相互作用、共同促成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创业主体因素和创业活动的内部因素,比外部因素所给予的鼓励、帮助更为重要。良性的运转机制应该是外部环境因素立足于创业内部因素的需求进行改革、提供帮扶。创业活动是创业环境改革的内动力,部分环境因素甚至无须人为,随着创业活动持续、深入、有效的开展,这些因素也会随之变化。
4.忽视环境的不可控性。先天资源禀赋、自然与地理条件、地缘条件等具有不可控性,是营造创业环境的背景条件。即使可以施以影响的后天因素,同样具备不可控性。因为,创业环境具有复杂性、开放性、动态性,人类的认知水平还不能够清晰、明确地辨清规律。所以,对创业环境建设既要坚持有所为,又要放手有所不为,既要规划性、计划性地建设,又要给足创业活动空间,调动和释放创业活力,加强对创业环境建设的动态过程进行引导和修正。
从微观角度,舍弃创业环境的整体观和严谨的属性分类,围绕着区域创业活动真实所需,缺什么补什么,差什么添什么,充分调动创业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区域创业环境建设,形成更富有针对性,更具实效性,更能实现区域创业的差异互补和宏观微观环境良性互动的局面。
三、微观视角下创业环境的框架
微观视角,即站在微观创业的角度,从创立和经营新企业的真实需求的角度来考察外部环境的改革。创立和经营新企业,从时序的纵向来看,可以分为创业者、创业机会、创业准备、实施创业、创业管理;从事务的横向来看,实施创业包括资源筹措、创办经营组织、建立合作关系、场地与设备建设、人才招聘、规章制度建立等,创业管理包括产品开发、生产管理、营销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管理、文化管理等。其中,创业者包含创业动机、创业意愿、创业心智、创业能力与技能等内在素质。
创业者是识别创业机会,进行创业准备,实施创业的主体,创业者内在的素质和能力是创业能否成功的基础性因素。另一方面,机会识别、创业准备与实施本身也是一种实践教育,可以培养创业者内在素质和能力。所以,微观的创业活动内部也是互为促进、互有影响的有机体。
将GEM的环境因素在该微观创业系统上进行分解,可以发现有些环境因素与创业是直接相关的,有些是间接相关的,还有一些因素仅具有一定关联性。也有些环境因素,如创业文化,是创业活动构造的,而不是政府凭空任意打造所能凑效的。
四、微观视角下成都创业城市建设的路径
基于微观视角的环境解析,本土创业城市环境建设应尊重本土创业活动的主动性和反作用,要立足于本土创业活动的实际需求,有针对性地实施。
1.政府适度干预。对城市或区域而言,创业环境既是创业活动的基础,又是创业活动的结果。创业环境的营造需要政府和市场的共同努力,政府既不能缺位也不该错位和越位。创业城市建设是政府的宏观管理和公共服务,但“引力”在政府,“发力”在市场,必须正确界定政府和市场行为边界,避免政府对创业活动的不适当干预和介入。创业环境营造中,政府主要在市场失灵、市场环境、文化导向、教育投入等方面参与。具体而言,主要是基础设施、科研平台建设、基础研究、产业政策、市场环境、创业文化、创业教育等方面。当前,科技竞争越发激烈,创新创业越发活跃,成都正以融入全球产业链高端和价值链核心为导向,加快推进要素供给侧改革,创建企业集聚、产业集群、要素集约、技术集成、服务集中的产业生态体系,完善集成整合、协同配套、精准高效的产业政策体系。
2.完善内生性的治理制度。内生性的创业制度是由创业的内部条件或内部力量产生的,外界条件或影响力量与内部因素产生关联、甚至融为一体而形成的。内生性治理是政府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促使各市场主体基于自身利益目标和市场需求,在发展过程中自发形成良性秩序,实现自我规范、自我完善的治理理念和治理方法。内生性治理代表着包容与开放,任何能够有效满足市场需求的方式和手段都能及时、准确地进行吸收和采纳。内生性治理要求政府“把该管的管好,把该服务的服务好,其他都交给市场”,强调科学、高效、民主的治理,充分考虑新生事物的正当性和合理性,保持适度和适当监管。
3.加速创业服务的组织建设。创业服务是创业系统有效运行的基本保障。创业服务组织是创业活动中调配创业资源,整合创业要素,促进创业资源和要素向创业行动和创业成果转化的重要机构。创业服务组织主要作用表现在:(1)咨询和管理支持,主要为创业提供经营策划、管理培训、资金融通、形象设计等专业性服务;(2)孵化服务,主要为技术研究、科技转化、创业管理、产品推广等提供孵化服务,以帮助新创企业生存和发展;(3)市场性服务,主要是建立专业性或综合性的创业要素市场,如人才市场、资本市场、产权交易市场等;(4)评估、认定类服务,主要为创业要素进行评估和认定,如资格认定、水平评估、资质服务等;(5)半公益性质的团体服务,如行业协会、商会等,既为成员利益服务,又可以承担行业自律或政府对市场的监督与调节功能。成都可以建立官方的创业服务组织,也可以建立半官方性的协会、商会、联盟等组织,还应该引导和资助社会资本加速聚集,形成创业服务合力,提高创业服务的质量和水平。
4.创业教育人格化转型。目前,创业教育被理解为老板速成,以商业创业的知识内容和技能要求为目标。创业所需的知识与技能比较容易显性传授,而创业更需要精神品质、创新能力、决断智慧,这需要高水平的教化和实践的不断磨炼。成功创业的关键因素是创业人格[4]。人格性的创业教育,相比于技能型创业教育,更强调依靠专业教育、人文教育培育起创新精神、创新能力和决断智慧。四川大学创业教育要求所有教师必须引导学生提问,鼓励质疑,教学活动源于“问题”又高于“问题”,虽然表面上与创业无关,但在问题中学习所培养的探索乐趣、形成的思考习惯、塑造的理性思维,都与创业人格密切相关。
5.制定精准帮扶制度。为营造创业氛围,鼓励大众创新、万众创业,成都各级政府及部门均给予一定的政策扶持和财政资助。扶持政策按一定的条件或门槛进行设计,体现了政府的政策意图,也帮助了企业发展。但政策的起点不是企业的真实需求,而是政府的政策意图,其结果是企业所受到的扶持并非真实需要,甚至为获得扶持政策而改变经营思路和管理决策。精准的帮扶制度是以创业需求为政策起点和施政逻辑,可以动态调查和适时监控创业活动的真实需求,形成“一篮子”的扶持政策,供企业进行选择,必要时一企一策进行帮扶。
[1]罗山.城市创新型创业环境结构分析与设计[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0,(9).
[2]Spencer J.W.,Gomez C.The relationship among national institutional strueturse,economic factors and domestic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a multicountry study[J].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2003,(5):1-5.
[3]高建,等.中国城市创业观察报告[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48-49.
[4]于建华,黄超,王永莲.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有机融合模式研究[J].教育与职业,2016,(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