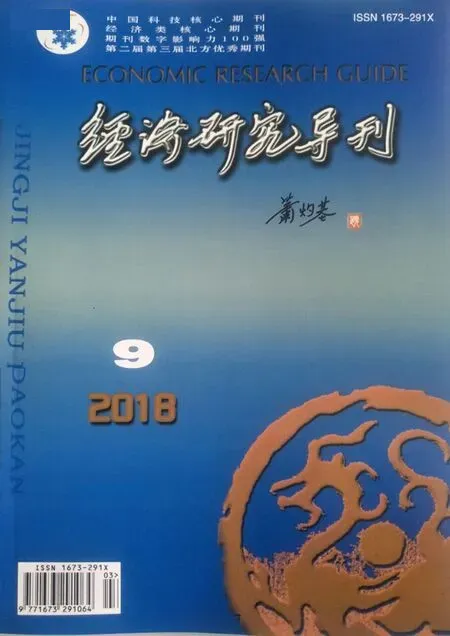城镇化背景下中国新市民身份认同研究反思
李 博
(山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太原 030006)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逐步推进,农村人口的就业选择范围相对有限,因而他们开始由少至多地进入城市,此后成为人口大规模的流动和迁徙运动——中国城镇化。为了更好地适应与调整社会的变迁和发展,我国各界对于城镇化都给予了强烈的关注,让城镇化不再仅仅着眼于农民经济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应是更为全面、更为人性化地城镇化。因而基于身份再生产的新市民对于自身身份的界定,对于城镇化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可以说,“只有农民形成了市民的身份认同,‘人的城镇化’才基本完成。”
一、城镇化背景下的中国新市民
我国的新市民群体是城镇化的衍生物,然而我国学界对于新市民群体的研究却是始于城镇化基础上的城市移民。不同于西方学者将注意力集中在移民动机、移民过程与移民结果的研究思路与框架上,随着后续研究的深入发展,我国学者逐渐将流动人口和农民工群体的研究纳入了城市移民的研究范畴,但仅仅是移民群体的研究,还不足以包含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没有发生地域转移、就地城镇化的部分群体。基于这一缺漏,我国学者提出了“新市民”这一概念,认为新市民应该是在城镇化的进程中,从最初的传统农民逐步向市民转化这一发展脉络上的所有群体。但是,通过文献检索不难发现,我国学者使用新市民概念的较少,多数仍然沿用城市移民、农民工、失地农民等概念。
二、城镇化背景下中国新市民的身份认同
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许多农民的生活地域已经从传统农村逐步搬到了城市或城市边缘。此外更进一步的是,国家通过对城郊村、城中村的改造使其在户籍制度层面成为了市民。但是,在户籍制度上或是生活环境上的市民化就是“人的城镇化”了吗?答案显然是不够的。身份的转变不仅仅是户籍制度和生活环境的转变,更重要的是在社会转型期人们心理层面和行为层面的转变。要想从心理层面上实现全方位的市民化,就必须先解决其身份认同的问题,即“我是谁?”“我要到哪里去?”的问题。
我国学界关于身份认同的概念界定尚未形成较为一致的观点,部分学者从词源构成的视角,认为身份认同是“身份+认同”的集合,是社会生活中的个体对于自身地位、所能获取的资源以及相应的责任、义务的感知和同意,是个体对于自身身份的确认以及属于哪个群体的划分[1]。此外,还有学者从社会学的视角,给出身份认同的定义:身份认同是个体为自身寻求群体归属的基础,是个体社会关系及社会行动的指南。若从心理学的视角来看,身份认同则是个体强调自身属于某种人、哪个群体的意识和认知。
对于身份认同概念的界定不同学科关注点不同,且互相独立互不包含,各有侧重。但值得一提的是,当今学科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化,很多社会现象及概念并不是一个学科便能阐释清楚和全面的,因此我们应该采用多学科交叉的视角来全面、客观地看待问题。基于此,在身份认同概念界定方面,本文认为单一学科领域的概念界定不甚完善,更偏向于学科交叉的概念界定方式。因此本文认为,钱龙等人从政治心理学视角对身份认同进行的界定更为准确、完善。他们认为:“身份认同是个体对于自身所处的社会地位、所扮演的社会角色以及所获取的社会资源的一种心理判断。与此同时,个体通过对自我身份的定位,很好地解决了我是谁、我和谁一样(属于哪一群体)以及我应该如何做等根本性问题。”[2]
三、城镇化背景下中国新市民身份认同的研究现状
(一)新市民身份认同与城镇化理论的内在契合性
上文已论述过新市民是伴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应运而生的群体,那么新市民群体理应或多或少地具有现代性的一些特征。梳理学界已有的现代化理论,不难发现对于现代化学者们主要持有三种态度:第一,乐观主义态度。坚持乐观主义态度的学者主要延续了启蒙思想家的观点,认为现代化的问题会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而得到解决,同时强调现代人积极的心理特征和性格特点。第二,悲观主义态度。这种态度暗含着对于社会变迁的实用主义的接受现实,也就是既然个体不能改变周遭的环境,就只能被动地接受。但是,这种被动的接受并不是问题的最终,而是会出现:不能够改变的社会现实—被动接受—麻木逃避—心里焦虑的现实路径。例如,以弗洛姆为代表的学者就对现代化过程中个体所遭遇的心理冲击感到忧虑和担心,他们认为现代性能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人心理层面的焦虑、不安和归属感的丧失,更甚者会造成个体对于自身身份的模糊感应,使人产生强烈的心理失序感。第三,激进的卷入。这种态度更多是一种中立性质的态度,既包含积极的乐观主义,又在一定程度上含有消极的悲观主义情绪。它是指当人们发现社会中存在一些我们人为力量无法改变的社会现实,既不悲观也不逃避,而是在看清事实后采用较为积极的手段去解决问题,降低风险。
综合各家观点不难发现,现代化的浪潮不仅冲击着宏观层面的社会制度建构,更是无声无息地渗透进了个体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对个体意识较为强烈的现代人而言,时空的抽离和重组打破了传统的习惯和秩序,使得个体原本无比熟悉的生活环境、生活方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转变,人们开始对周边的人、事、物感到陌生,之前建立的社会网络、社会信任全部需要重新适应和调整等等。由此,现代化的生活给人们带来的不仅仅是外在环境的变化,更是侵入到人们的心理层面,使得人们对于自身的身份产生怀疑。由此,新市民身份认同的危机产生。
(二)我国新市民身份认同研究的主要维度
西方对于新市民身份认同的研究,始于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对于欧美的波兰移民的文化身份认同考察。而我国的现实国情和文化氛围与西方都存在较大差异,在研究新市民群体的身份认同时,并没有跟随西方学界只关注移民的文化性身份认同的研究思路,而是以更广阔的视角从群体身份认同和地域身份认同两个维度来考察城镇化进程中所有的新市民群体。
1.群体身份认同研究。群体身份认同的研究主要根据群际关系理论,划分我群和他群,从而帮助自我寻找特定的群体归属[3]。我国学界在群体身份认同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有:张璐等学者运用实地调研的方法发现,多数农民工仍未将自己划分到市民群体,也就是并不认同自己具有了市民身份。与此类似的还有学者王春光,他比张璐的研究更进了一步,指出农民工不仅不认同市民身份还不认同农民身份,因此就产生了两边摇摆、不甚清晰的局面,这种现象也被部分学者称之为内卷化的群体身份认同。
2.地域身份认同研究。地域身份认同主要是个体对于自身属于哪一个地域,是不是某个地域的人群的内心判断。我国学者在研究新市民的身份认同时也关注了这个维度,例如关注流动儿童身份认同的石长慧就在其研究中指出,在地域认同方面,流动儿童的身份认同未出现整体一致性,即部分流动儿童认同自己的“城市人”身份,也有相当一部分流动儿童认同自己的“农村人”身份。不同于流动儿童相对分化的地域身份认同,流动人员则对于自己的地域身份认同有相对明确的认知,即认为自己是“城市的陌生人”,与城市人身份没有太大的关联性。
(三)我国新市民身份认同的影响因素
身份认同作为一种心理变量,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而我国学界也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对影响身份认同的因素给予了关注。综合各方观点,本文挑选了两类关键因素进行了归纳和整理。
1.个体因素。个体因素主要包含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等公民自身层面的要素,个体因素对于新市民身份认同的影响受到诸多学者的关注。例如,学界经常探讨的农民工与新生代农民工或是一代农民工与二代农民工。可见,年龄的区隔会对个体的身份认同产生一定的影响。在性别对于身份认同的影响方面,许传新在研究了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后发现男性相对于女性而言更认同自己的市民身份;出乎意料的是,个体的受教育程度与身份认同并非相互促进的关系,而个体的受教育程度越高,个体越不认同自己的“城市人”身份。
2.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我国长期存在的二元户籍制度在实际层面逐渐拉大了城市和乡村之间的距离,农村逐步落后于城市,这样农村的剩余劳动力逐步步入城市,寻求新的生活,但是城市的一系列限制政策又使得他们无法真正地融入到城市生活之中,这样进入城市的农业户籍人口虽然拜托了农业户籍的生活环境,但却无法从心理层面真正认同自己的市民身份。因此,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新市民市民化的身份认同。
这些已有的文献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身份认同及新市民的理论,但就国内现有的文献而言,也仅仅是通过群体身份认同和地域身份认同的研究,指出了新市民身份认同的制度困境和对城市认同感不高的现实。但是结合已有理论,不难看出,对于新市民身份认同而言,已有文献大多是关于其现状及影响因素的探讨,并不能脱离时空的限制,同时缺乏将新市民身份认同作为自变量的相关研究。因此,目前的已有的相关文献并不能切实而全面地满足我国城镇化进程中日益丰满的中国身份问题。但也正是因为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才为今后这方面的发展提供了思路和可以开拓的领域。
参考文献:
[1]张淑华,李海莹.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测量分析[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5).
[2]钱龙,卢海洋,钱文荣.身份认同影响个体消费吗?———以农民工在城文娱消费为例[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1).
[3]赵立.农民工群体身份认同与群体偏好研究——自我认同的中介作用[J].浙江社会科学,20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