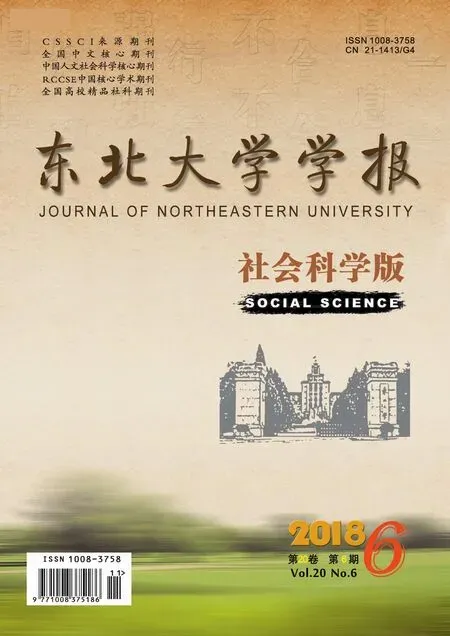译者选择的场景框架认知模式分析
闫怡恂, 成晓光
(1. 东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24; 2. 沈阳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辽宁 沈阳 110034)
认知语言学研究可以分为三大研究角度,也有人归纳为三个研究方法[1]。这三个研究角度是指经验观(the experimental view)、突显观(the prominence view)和注意观(the attentional view)[2]。经验观建立在心理学对认知范畴的研究之上,这类心理学研究遵循一条更实际和实证的路径。突显观主要涉及语言中所表达的信息位置和分离关系。注意观中的两个主要概念是框架(frame)和视角(perspective)。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是经验现实主义,即体验哲学观,因此这三个研究角度不是也不可能割裂开来,而是辩证统一的。它们是一个基础不同角度,一个概念系统不同术语区分。突显观与注意观都是以经验观为基础的,突显观与注意观之间又互相依存。本文重点从认知语言学的注意观视角出发,依据Fillmore框架语义学理论探讨译者选择的过程与模式。
本文的分析语料主要是根据葛浩文近半个世纪中涉及的59部翻译作品的书名及相关内容的翻译。葛浩文翻译可以说达到了中国文学作品英译的又一个高峰,至少在杨宪益、戴乃迭之后,是无人能及的。对每一部作品,译者都倾注了心血,虽说也有少数与他人合译的作品,但也是句句斟酌,字字推敲。在书名翻译方面,葛浩文更是兼顾中西,与原文文化对话,与原文作者对话,通过文化协商,把最贴切的主题传递给译入语读者。本文试图对相关翻译现象进行归类、对比,并对译者选择进行认知模式分析与阐释。
一、 框架语义学与翻译研究
Fillmore的框架语义学对翻译研究的启示意义主要来自对语言意义的理解范式。众所周知,翻译是具有跨文化、跨语言特征的交际活动。Fillmore[3]提出的针对语言意义研究的场景—框架范式(scenes-and-frames paradigm),对从源语到译语的转换过程的解释或阐释是十分有意义的。Fillmore这一范式中提到的场景包括我们在现实中看到的视觉场景,也包括来自人类认知体验的典型场景。也就是说,这一范式既是关于现实世界的直接反映,也是对人类普遍认知的间接反映。因此根据Fillmore的观点,框架就是由语言选择组成,并且和典型场景相关的任何系统。这一系统既“是词语的组合,还包括语法规则或语言范畴的各类选择”,显然这里的框架是和语言体系直接相关的,称为语言框架(linguistic frame)。此外这一系统还与认知密切相关。Fillmore在阐述场景-框架范式时谈及了框架概念,认为框架是“由概念组成的构架或图式”。因为,概念是认知的最基本组成。可以看出,这种表述实际是关于认知性质的。Fillmore[4]明确提出,阐明语言系统需要描写认知和互动框架,以帮助解释语言交流和理解的过程,并以商业交易事件为例建立了一个基于人类商业活动体验的典型认知框架[5]。Fillmore关于“买卖”的表述是最为公认的典型场景,它不仅涉及语言框架,也涉及认知框架。比如,如果我们不理解商品交换流程的话,我们就无法理解“卖”这个字,这个流程包括了买家、卖家、商品、金钱、金钱与货品的关系,卖家跟商品、跟金钱的关系,买家跟商品、金钱的关系,如此,一个字才会激活跟这个字本身概念相关联的语义知识框架。词汇本身不仅仅凸显其概念,也会特指一个框架所特有的视角,再如,“卖”这个字,从卖家的视角去观察,“买”这个字则是从买家的视角去定义。可以说,一个人如果不把跟一个词语相关联的百科知识理解透,他就根本无法理解这个词汇本身。
Fillmore也用这个概念去解释很多词汇关系的不对称特征[6]。框架语义学是一门跨学科理论,是一门综合考虑了语境、原型、感知、个体经历的意义理论,框架语义学对翻译现象,尤其在涉及译者决策方面,具有相当的应用价值[7]。Fillmore的格语法到格框架再到认知框架全面阐释了语言意义生成的过程及生成机制,奠定了框架语义学的基本核心领域。框架语义学对译者选择的运作机制的解读与阐释的指导意义如图1所示。

图1 Fillmore的框架语义学的核心概念对译者选择的阐释作用
二、 场景框架认知模式
在认知模式中,Fillmore 的场景框架说是一种比较全面和相对为人所知的认知模式。Fillmore认为,我们听到或读到的词汇实际上就是唤起我们记忆中的思维画面或思维场景的框架,也就是说,我们理解一个词语的时候,我们回忆起相应的画面,然后会把注意力集中指向该词语所指的那一部分。Kussmaul[8]解释说,尽管有些人会认为这就是语言符号与语言意义的关系,但他强调,这个场景,其实就是指向我们的思维、我们的记忆的。意义并不是从语言系统中衍生的,而是会涉及人们的体验、经历。更何况,“场景”这个术语会跟“某一形象”有关系。场景框架说可以应用到翻译实践、翻译教学,以及翻译标准、译者角色等问题的研究。
Kussmaul在此基础上更加细化了场景框架的关系,他认为场景框架存在较为活跃的四种互动关系。Kussmaul 并没有给出更多的细致解释,但根据他的撰文(AcognitiveFrameworkforLookingatCreativeMentalprocess)及例证可以推断出这四种关系对翻译认知过程运作机制的解释,以及这四种关系之间的明显差别。在文中,他清楚地说明了翻译过程中的场景框架互动关系,每一种互动关系其实也是认知模式的类型关系,也是译者的翻译策略形成的依据[8]。
第一种是框架进入场景(frame-into-scene)。 在这可以看出从框架进入场景的过程,就是将原文的语言及其规则关系进入具体的现实世界的过程, 是一个具象化的过程。 第二种是框架变成另外一种框架(frame A- frame B)。简而言之, 就是框架有所改变。 我们认为,改变了的框架说明了源语到译语的语言选择无法直接完成, 这个时候按照框架语义学的理论,起作用的是认知框架,单就格框架而言是无法完成的。 因此,源语和译语中关于百科知识的调动与呈现应该是最大化的, 我们要考察这个认知框架的最大化是如何实现的,译者如何选择策略等。 第三种是场景进入框架(scene-into-frame)。 此时,在原文本中所表现的场景因素进入到目标语文本的框架中。 源语中的场景如何在译文中体现出来, 不仅要保留源语的细致与精细,还有代表规则或背景的框架介入,使得框架在原有基础上更加丰满和活跃,特别是在文学翻译中很大程度上是增加想象力、创造力的部分。 这里边毋庸置疑是离不开语言的丰富性的, 或者可以说,这也是文学翻译的语言魅力所在。 第四种是某一种框架被近乎相同的框架充分再现(frame A- frame A+)。 其实这个关系类型看上去是比较模糊的, Kussmaul本人更多强调的是这种类型的框架转换不是问题,他认为在具体操作时, 要重点关注翻译过程中如何体现“创造性”的问题。 因此这里更多强调的是认知框架的范畴,属于依靠百科知识调动语言意义的创造性的问题。 以上四种类型本文会依次举例说明。
三、 译者选择的场景框架认知模式
本文以葛浩文的59部翻译作品为研究对象,按照书名的翻译方法进行简要分类为完全直译与非完全直译,其中非完全直译包括意译和补偿翻译(见表1),分类标准描述如下。
① 完全直译:是指完全符合原文的语言意思,基本没有作任何修改的翻译。
② 意译:翻译的书名与原来不同,有的是部分不同,有的是完全不同。
③ 补偿翻译:是指译者对书名进行部分直译之后,又添补了一些内容以求书名与作品的一致性,以达到更加符合目标读者的接受度和作品的可读性之目的。
从表1中可以看出,葛浩文翻译的59部作品中书名翻译完全直译的共29个,占总体比例的49.2%,意译及补偿翻译等非完全直译共30个,占总比例的50.8%。我们可以作出假设,当书名翻译可以完全直译时,证明不同的两种语言文化之间的语言认知体验是相通的,这时候译者与作者的认知模式也是相似的。还有超过一半的意译及补偿翻译的数据表明:两种语言、文化及认知体验或语言表达方面的差异还是比较明显的。本文试图研究这一过程中译者是如何选择的,根据场景框架说分析推断译者认知模式是怎样的。具体研究问题如下:
其一,完全直译的原因是什么?这是否说明源语和译语的语言框架和认知框架都是一致的?
其二,在意译和补偿翻译等非完全直译中,译者选择的认知模式有哪些具体不同类型?它们都具有哪些特征?
其三,译者处理这些非完全直译的词语时,受到了哪些其他因素的影响?

表1 葛浩文翻译作品书名翻译方法信息表
注: 更新至2017年12月18日
1. 完全直译的认知模式
对于完全直译的原因,我们可以按照框架语义学的视角来审视与解读。框架语义学认为,一个词语的意义实际是这个词语本身和它所涉及的百科知识的意义的总和。书名的选择通常也是作者对整本小说大意的综合把握。如果译者不需要作任何修改就能传递信息,同时,也能够预测让目标语读者充分读取作者意图,那么译者就没有必要在翻译的时候进行改变,这里的框架没有发生任何改变,源语和译语的语言框架是完全一致的。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从源语到目的语过程中,虽然语言框架是完全一致的,但在认知框架下也不能保证两种语言的框架和场景因素都是一样的。比如刘震云《手机》,葛浩文直译为CellPhone。但即使是完全直译,框架完全没有变化,不同时期其内在的场景因素也会不同,比如在国内90年代和刚刚过去的一段时间,“手机”一词可能会分别代表一件时髦奢侈物品和与崔永元、冯小刚等相关的具体事件的代名词。这也如同Fillmore关于早餐的例证一样,其内涵根据不同文化群体等会发生变化。根据Fillmore的阐述,早餐需要满足三个标准[9]:
“To understand this word is to understand the practice in our culture of having three meals a day, at more or less conventionally established times of the day, and for one of these meals to be the one which is eaten early in the day, after a period of sleep, and for it to consist of a somewhat unique menu (the details of which can vary from community to community).”
根据原文,我们可以看出这三个标准分别是:我们一日三餐的一个文化行为;早餐是在睡醒一觉之后的一天的早些时候进行的;早餐菜单是有其独特性的,不同文化早餐菜单会有所不同。但在实际语境中,我们说“吃早餐”时,未必是一天吃了三餐,但我们仍然会使用早餐这一表达,或早午餐合在一起时我们也泛泛称之为早餐;此文化里的早餐是豆浆油条,彼文化就是牛奶面包或培根烤西红柿等。如Fillmore所说,即使这三个条件任何一个缺席,说话人仍然可以使用这个词。这里涉及的不仅仅是一个词语的核心意义的问题,还是一个词语的范畴问题,特别是这些范畴可以用在不同语境中,并将由典型用法的多个方面来决定。综上,我们可以看出,当两种语言完全可以直译的时候,即使他们的语言框架一致,认知框架也未必相同。
2. 非完全直译的认知模式分析
意译与补偿翻译都属于不完全直译范畴,因此我们放到一起来讨论,来回答上面提出的另外两个研究问题。意译与补偿翻译在葛浩文翻译作品书名翻译中占了50.8%,超过一半。为了便于分析,我们将使用Kussmaul关于场景框架的四种关系类型作为分析工具。这四种关系类型分别为:①框架进入场景;②框架有所改变;③场景进入框架;④某一框架几乎被近乎相同的框架充分再现。每一种关系类型都再现了译者的认知模式,从而反映了译者选择的态度和策略的产生与变化。
(1) 框架进入场景(frame-into-scene)
框架进入场景是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把原文的框架放入了译文的场景。这是一个使得框架具体化、物化的过程,原文中看似概念化的、不清晰的表述,在译文中采取了场景具体化的方式。它的特征是:译文中词语选择更加实际、更加具体,它是把原文中具有概念化的特征的词语或句子在译文中进行物化的过程。
例1 白先勇的《孽子》(CrystalBoys)
译者翻译时,选词策略原则往往会无意识或下意识地在框架与场景之间变换。葛浩文对这类情形的解释是下意识的翻译再创作本能。葛浩文在白先勇《孽子》(CrystalBoys)的“Translator’s Note”里写道[10]:“台湾把男同性恋社群称为‘玻璃圈’,男同性恋者会称为‘玻璃孩子’。译文中使用的是‘Crystal Boy’”。应凤凰对小说名的译法大加赞赏:“‘孽子’ 二字,既能呈现那群孩子在阴暗角落的具体形象,又能暗喻小说‘冤孽’的命题,只用极少的字,却有多重寓意,实在是相当难译的书名。葛浩文高明地也只用两个英文字Crystal Boys翻译出来, 不但涵盖中文惯用的‘玻璃圈’比喻——Crystal即‘水晶’,而且把‘孽子’的‘子’——那青涩少年的形象,也对应地用Boys准确翻译出来,当真是玲珑剔透的译笔。”[11]这也充分说明译者也在下意识地使得框架进一步清晰,使得原文中的场景因素更多在译文中展示出来,具体物化了原文的框架,说Crystal 是玲珑剔透的一笔,真是极大丰富了译文的场景,把同性恋群体对于家人对于社会的内心反应用最简洁最贴切的文笔得以具体再现。此时,译者追求的恰是让文学作品尽量忠实地展示给目的语读者的翻译准则。
(2) 框架有所改变(frame A- frame B)
这里边的框架改变具体而言,是指一种框架变成另外一种框架,简单而言,就是框架有所改变,我们可以用框架A变成了框架B来表示。原文中的框架在译文中变成了另外一种框架。
例2 刘震云的《我不是潘金莲》(IDidNotKillMyHusband)
我们看看2014年出版的英译本《我不是潘金莲》的翻译。《我不是潘金莲》是刘震云2012年出版的小说,由冯小刚导演改编成同名电影,电影英文译名为IAmNotMadameBovary。我们知道,福楼拜塑造的包法利夫人的形象主要是向往幸福,向往浪漫,是一个失去理智全心投入爱情,最后在绝望中选择了死亡的悲剧人物形象。潘金莲在传统的中国话语中,是一个毒死丈夫、不甘生活现状的淫妇形象,尽管有些评论试图挖掘人物性格的合理性等,但总体而言,杀夫的标签肯定与潘金莲有关。刘震云小说借助这个基本传统认识,把《我不是潘金莲》描写得淋漓尽致。显然,葛浩文和林丽君夫妇是谙熟这一情形的人。他们的英译本译为IDidNotKillMyHusband。这里边的原文框架几乎被译文的框架代替,实现原文世界与读者世界的交际融合。他们的译本尽量寻找与目的语受众话语的共同点,根据目的语受众的表达习惯来再现原作的表达方式,并努力扩大这个共同点,以海外受众乐于接受的方式进行传播,达到了让目的语受众理解和接受刘震云原作中所要表达的内容[12]。
例3 毕飞宇的《青衣》(TheMoonOpera)
下面再以《青衣》翻译为例。毕飞宇的作品人物刻画入木三分,连葛浩文本人也感叹毕飞宇“将来肯定是个大作家”[13]。毕飞宇作品涵盖诸多中国文化因素,翻译不好处理。青衣是京剧文化的特有词汇,是京剧中的女主角。青衣,又称“青衣旦”和“正旦”,因其扮演庄重、贫苦的中年妇女常穿青色裙子而得名。青衣之所以称做“正旦”,说明这是京剧中的女主角[14]。一般此类表达的翻译处理方法是采用汉语拼音Qingyi, 采取的是零翻译策略,比如译文中多次出现的Qingyi都是指青衣这个角色或概念。
译文中译者在处理的时候,对于青衣、花旦、花衫直接用拼音Qingyi, Huadan, Huashan直译作了处理,如“QingyiandHuadanare very different female roles…almost no one cared if people could tell aQingyifrom aHuadan…In short aQingyispeaks a language unknown to man…”[15]。而且凡是在文中出现的代表这个概念的“青衣”的表达都是译成Qingyi这一拼音形式。可见,在国外读者看来,这种音译更多指的是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或某一中国特色的事件、文化元素等表达方式。然而,作为文学作品的书名翻译,直接把《青衣》译成Qingyi, 显然是有损翻译过程中文化元素的传递与保留的。该作品翻译最终选择的是TheMoonOpera,意指作品中以小说主线展开的《奔月》这出京剧。作者毕飞宇在《青衣》这部作品的开头,就提及了《奔月》这出京剧,并通过对话提及了女主角——青衣筱燕秋的身份。葛浩文作为译者也相应地作了翻译选择,并且借此对译作的TheMoonOpera这一译法进行了交代与点题。“ The one who played the lead role in the 1979 performance ofChang’eFliestotheMoon—TheMoonOpera.” 原文的框架到了译文中发生了变化,由原来的京剧中的女主角,变成了一出京剧段子的名字。这一框架上的改变,显然是语言框架、认知框架交互作用的结果。TheMoonOpera带给读者的阅读反应和吸引是远远大于Qingyi这个不为大多数人所熟知的京剧术语的。当然,以上这些译者选择也可以由认知语言学的突显观来解释,即Langacker[16]提出的焦点—背景分离关系(figure-ground-alignment),Kussmaul更是曾经形象地把它描述为两个如图2所示的视觉图片。

图2 “焦点—背景”分离关系与视觉对比图
在图2(a)中,我们能看到一个小白点置于黑色的背景布中心,我们的视角会聚焦到这个白点上。在图2(b)中,我们会明显地把注意力放在黑色的框架内,或圆之外的“背景”上。Langacker认为面积越大的地方,可以称之为背景(ground),面积越小的地方可以称之为焦点(figure)。这里可以看出,面积大小的变化正好是我们关注的焦点的变化。Qingyi是这个故事中出现的京剧文化的主要焦点,我们称它为figure。可是在目的语读者的心目中,显然这样的音译表述是不能成为焦点来吸引读者的,而题目对于一部文学作品又至关重要。青衣作为译入语的焦点转化为The Moon Opera,是把整个焦点突出,直到这出京剧段子有了完整的背景空间,这时也就成为读者关注的焦点,这就是一个焦点—背景的角逐与抗衡。这里边的冒险成分固然有,可是翻译作为再创作过程,势必在译者的认知关注下寻找最佳效果。
(3) 场景进入框架(scene-into-frame)
场景进入框架是指在原文本中所表现的场景因素进入到目标语文本的框架中。它把原文中的细致场景通过解释、同位语说明等在译文中体现出来,与第一种情形不同的是,这种模式使得原来的场景因素更加丰满、更加丰富,增加翻译文学作品的阅读想象力与理解力。
例4 苏童的碧奴(BinuandtheGreatWall)
我们看看译者将《碧奴》原文中的框架如何在翻译中进入场景的。碧奴(BinuandtheGreatWall)是以一个名为碧奴的女主人公为主要角色,根据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作者以丰富的想象力重构一幕幕精彩场景,展现了在权势压迫下的底层女子以自己的善良与淳朴于乱世中创造的传奇故事。因此翻译后的书名为BinuandtheGreatWall,这样的处理方法显然增加了外国读者对中国和中国元素的向往,与此同时也把场景—框架介绍得清清楚楚。这类翻译的认知模式属于场景进入框架(scene-into-frame),也就是说,在原文本中的各种故事元素在译文本中是被场景化了的。具体而言,对于海外读者来说,对长城Great Wall是知道的,在书名里添上“长城”二字,能引发读者进入场景,引发联想,是有利于传播原作的。
例5 陈若曦的《尹县长》(TheExecutionofMayorYin)
陈若曦的《尹县长》是葛浩文早期的翻译作品。《尹县长》的英译名是TheExecutionofMayorYin,意为“尹县长的死刑”。《尹县长》的翻译其补偿策略的使用是基于出版商、读者世界等相关因素而作出改变的。葛浩文曾经回应Mark Elvin的评论中提到过:“有些是增加故事的可读性或为迎合西方读者口味,有些是删节过时、不清晰或无关紧要的按语引文。”同时他还提及,“把县长译成Mayor (市长)大多数关系人终于都同意,因为现在美国没有县长(Magistrate )这个官位,而在英国乃是地方法官名字。译作篇名上加上Execution (枪决)一字完全是由于销路的考虑。大家都认为这样才能引起英文读者的注意力”[17]。显然,译者采摘到了一个框架(frame)中(这里指尹县长这个人)的若干场景因素(scene elements,这里指的是一个人经历的各种故事),然后将某一因素(死刑)放大。对于一个人的故事而言,死刑也许是最具个案的,最具血腥色彩的吧!而且,既然写到了死刑,这一定是关于一个人一生的故事,一定具有很强的色彩与感染力。译作篇名中这样的添加本身就会在读者世界中产生极强的吸引力。
例6 萧红的《商市街》(MarketStreet:AChineseWomaninHarbin)
这一点从萧红《商市街》的翻译也看得出。英文译名为MarketStreet:AChineseWomaninHarbin,这部小说叙述了一个哈尔滨女人的故事。哈尔滨这个地名对域外读者来说本身就有吸引力,再加上一个中国女人的渲染,增加了故事的看点。这就如同,一个以商业街为背景的场景展现在译文读者面前,里面讲述的是以此为背景的一个中国女人的传奇故事。
(4) 框架充分再现
这是一种不太容易区分的模式,它是指原文中的某一种框架被近乎相同的译文框架充分再现。表面看这种表述似乎是一个直译问题,其实不然。它强调的不是框架转换的问题,而是框架的立体化再现的问题。因此,在具体操作层面如何实现“近乎相同的框架的充分再现”这一模式,主要是指向译者创造性这一问题的,因此,翻译的创造性魅力也因此得到最大化最优化的彰显。
例7 莫言的《檀香刑》(SandalwoodDeath)
葛浩文在《檀香刑》英译本的译者序[18]里提到,翻译这部莫言的历史作品从翻译书名就遇到了挑战,“原文书名直译是‘檀香刑罚’(sandalwood punishment)或‘檀香折磨’(sandalwood torture),然而作为文学作品书名翻译要考虑声、律、调等因素,所以这两个译法我都不满意。我注意到了一点,就是刑部(executioner)在宣判的时候是通过拉音的方式,一字一字读出了这三个字,Tan-xiang-xing!, 所以考虑到檀香已经占了两个音节,因此最后选择了Sandal-wood-death这个译法”。译者充分考虑了原文框架的音、声、律等因素,使其在译文中以具体实例的形式,直接把原文中没有提到的死刑“death”展示在译文中,用“death”一语点破了“刑”的真实含义,这样使得译文中的框架展示得更加充分、更加立体。
例8 莫言的《师傅越来越幽默》(Shifu,You’llDoAnythingforaLaugh)
在《师傅越来越幽默》的英译本前言[19]中,莫言指出,这篇短篇是其近期作品,并由张艺谋导演拍成电影《幸福时光》,作品开篇呈现的是中国工人面临的裁人下岗的局面。俗话说,醉翁之意不在酒,要说的还在小说里头。小说里的框架通过徒弟回应师傅的一句对白显示出来了。此外,原作的书名是一个陈述句,译者巧妙地把小说中最后一句徒弟说给师傅的话——“师傅,您越来越幽默了”(Shifu,You’llDoAnythingforaLaugh!),直接拿来作为译作的书名,使得原作的框架在译作中充分再现。这种变化,可以说,使译文读者径直进入一个幽默、讽刺而具有戏剧性的文学作品中,读者仿佛可以在一个师徒对白中领略小说幽默风趣又直指当时现实社会问题的诙谐语气与场景。这里还要指出,呼语“Shifu”翻译时没有作任何处理,选择了直译,西方读者是不是读过《西游记》,会不会谙熟这个词汇的含义已经不重要,大家也能猜出Shifu至少是个呼语。更何况,葛浩文在《师傅越来越幽默》的“译者的话”中,对“师傅”这一称谓作了如是解释:“‘师傅’是尊称,特指有技术在手的人,并且这一称呼在中国已普遍使用,可以说,已取代‘同志’等其他称谓”[19]。这一选择,十足给了西方读者一个暗号,中国变化着的元素也许正在吸引着越来越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外国读者们的眼球,因此这样把称谓当做呼语直接放在小说题目里,会更促使读者想去领略当代中国百姓的生活,从而进一步提升了原作的传播价值。
例9 莫言的《生死疲劳》(LifeandDeathAreWearingMeOut)
《生死疲劳》的译法更是经历了作者、译者、出版社等多方协商。“据说,为翻译这个书名,各国的翻译家都很头疼。”葛浩文自己也表示确实如此,“虽然出版社和我对小说译名的几个方面都很满意,但说到底还是那句佛经短语的意译,而不是直译,佛说:生死疲劳,从贪欲起,少欲无为,身心自在”[20]。由此可见,《生死疲劳》的书名翻译是基于这句经典佛经翻译这一框架的,这种佛家的轮回、转世、投胎等概念通过“life and death”这一生死轮回的表述,意义更加清晰,“wearing me out”也是非常直观地把主人公的疲于转世、疲劳奔命的苦楚在译文中表达出来。正如葛浩文自己所说,在翻译的过程中考虑的都是“很多与翻译相关的实际问题”,比如“译文读上去,要不要像译文?改变原文行不行?‘修改’原文行不行?删减没用的文字行不行?等等”,这充分说明由译者认知模式决定的潜意识选词择句的翻译现象。
四、 结 语
翻译过程无疑是一个再创作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译者的认知模式、认知观决定了其翻译观,也决定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选择与决定,遣词造句,文笔风格等特点。虽然葛浩文曾经表示,翻译无理论,也无直译意译之分,甚至无技巧可言[21]。这看似没有理论的一句话,恰好解释了翻译认知观对译者的重要性。近来,葛浩文又提及“从理论入手,成为一名合格的译者,这有点像一边下楼,一边研究膝盖的运动”, 认为“文学翻译可以传授,但是理论不能挡道”。这都说明了一个译者对原文作品的认知态度,应更多停留在翻译的实际问题上,而不是考虑所采取的翻译方法符合哪种理论。换言之,译者的认知观决定了翻译观。葛浩文的翻译观,简而言之,就是“在翻译过程中,通过一个字一个词的语言转换来求得对整个作品的深入了解”,可见译者选择贯穿他整个翻译观,一直认为必须要在信达雅之间求得平衡,甚至信奉“雅”字是他最大的追求[22]。翻译过程也是再创造过程中译者的认知模式的再现,选词造句、文风文体的确定是译者有意识或无意识作出选择的创作手段。不论是Fillmore的语言框架和认知框架,还是Kussmaul的四种互动类型的阐述,都能够帮助我们解读这样一个翻译过程,探讨翻译过程的诸多影响因素,以及并不好捕捉的译者认知与内心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