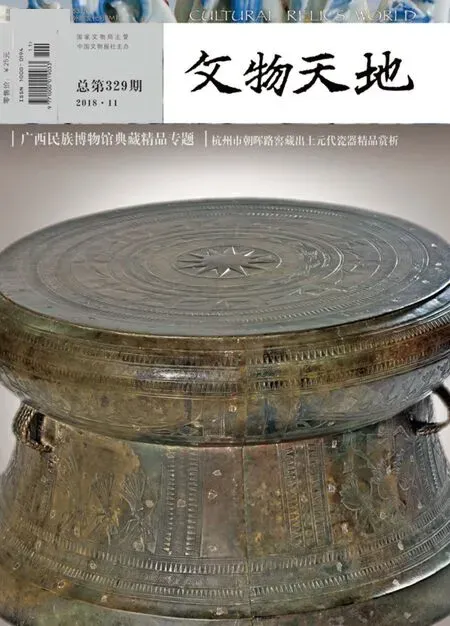堆华剔彩
——清代乾隆“百子婴戏图”剔红捧盒的图像考略

图一 新疆吐鲁番寺院幡画“诃利帝母”
一、寺观壁画中“鬼子母图”到“婴戏图”的嬗变
近代关于“婴戏图”造型来源的首发声者为胡适,1935年胡适发表《磨合罗》,探讨大黑天与“磨合罗”的关系,同时也提出了“鬼子母”信仰与“磨合罗”的渊源。这二者都是唐密显教最为常见的神祇,国内的学者认为“鬼子母”是菩萨样,与童子相去甚远,不可能与此有关。殊不知“鬼子母”的信仰主体神虽为女性菩萨,但伴其左、右皆为童子。“鬼子母”又名“诃利帝母”,随佛教传入,吐鲁番出土的幡画(图一)中,是“诃利帝母”在中国最早的呈现,并且与童子共组。故事讲述了药叉诃利帝母由于喜吃他人孩童,佛陀为了惩罚她,将其孩子扣押在饭钵之下,“鬼子母”率众欲揭开佛陀饭钵,终纹丝未动。饱尝失子之痛的“诃利帝母”,在佛陀感召下皈依佛门,成为“圣母菩萨”样。这一题材在宋、元时期极为兴盛,而现存山西繁峙岩山寺的金代壁画中就有《鬼子母变相图》(图二),作者王逵为金代宫廷画家,图中绘制了九个孩童与鬼子母戏耍的场景,其端庄的容貌与孩童在其身边的嬉闹,构成了诃利帝母“圣母”样的表达。这一故事文本的高超在于“揭钵”,在岩山寺壁画中,并没有对“揭钵”进行展开式描绘,而是将重点放在诃利帝母皈依之后乐享天伦的场景。
唐代应是“婴戏图”成熟期,在宋代院体《仿周昉婴戏图》(图三)中,童子与仕女的组合已成定式。虽然与壁画中的“揭钵”体稍有区别,但显然已经成型。北宋时期的院体绘画成熟,人物画中的“婴戏”成为专门题材,在故宫博物院藏佚名《百子嬉春图》中,就有与岩山寺《鬼子母变相图》相同的“影戏”图。宋、金时期的绘画相互影响,促进着这一样式的完善。
南宋迁都临安之后,宫廷画院建制保留,培养了一批技法高超,图写天趣的大家,苏汉臣与李嵩是其中的佼佼者。苏汉臣《秋庭婴戏图》(图四)中,两名孩童在庭院中玩耍游戏,庭院之中芙蓉盛开,野菊朵朵,地上佛塔、铙钹等玩具散落,笔调轻松自由,一派天真[1]。故宫博物院藏苏汉臣的另一幅作品《冬日婴戏图》在题材内容上几乎与前作相仿,男女孩童与猫嬉戏,大面积的假山花卉陪衬,营造田园景致。因工匠身份的影响,李嵩在创作过程中融合了民俗意味。《货郎图》(图五)和《骷髅幻戏图》(图六)就是带有强烈魔幻色彩的作品,但对人物的写实将仕女与孩童真实地进行了再现。此后,苏汉臣弟子陈宗训沿袭苏氏画法,在《秋庭婴戏图》中可窥师法一脉。有些佚名画家更是钟情于此,如《百子戏春》和《闹学图》,画中人物也增加为几十或上百[2]。无论是北宋或南宋及金朝,“婴戏图”作为独立的人物画科广为流传,但画中对于“鬼子母”的笔墨不见踪影,相反,孩童的形象更加趋向于写实的风俗画表现。虽然失去了半壁江山,退守江南的赵宋朝廷却把持了中国最为富庶的地域,因此,丰富的物产与发达的经济催生了人们对于市井生活的细致刻画,而选择抛弃“揭钵”故事文本,是因为宗教的渗透非常容易破坏这种世俗化的写实表现,因此,南宋的“婴戏图”是社会形态主导了人们的审美取向的自我演变。
元代之后,北方的寺观壁画接续了佛教图像的正统表达。在我国遗存的最早水陆壁画山西稷山青龙寺腰殿西壁下方,有一幅精美异常的“鬼子母”组图(图七)。图画中的鬼子母左右前后皆有孩童玩耍嬉闹,显然仍是对“揭钵”体的续接。明代的水陆壁画在“诃利帝母”的表现中也是无一遗漏,如阳高云林寺、繁峙公主寺等山西寺观壁画。

图二 山西繁峙岩山寺“鬼子母变相图”壁画(局部)

图三 宋 佚名仿周昉 戏婴图卷 30.5×48.6厘米 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

图四 宋 苏汉臣 秋庭戏婴图 轴 316×111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五 南宋 李嵩 货郎图卷 绢本设色 25.5×70.4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宋、元时期,“鬼母揭钵”还作为一类专门的剧本进行创作。元末明初《西游记》剧本中,出现的“爱奴儿”与岩山寺《鬼子母变相图》相仿,是对鬼子母儿子的称谓[3]。而西游记中的“红孩儿”也就成为了鬼子母的儿子,“红孩儿”在观音收服之后,成为“善财童子”,因此“五十三参”表现的童子模样,也是此类题材之一。“鬼子母”的信仰成为萌发“婴戏图”的诱因是有据可考的。这也意味着,胡适先生的推断有据可考,绝非单纯的猜测。

图六 南宋 李嵩 骷髅幻戏图 设色团扇 27×26.3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图八 山西河曲娘娘庙壁画(局部)

图七 山西稷山青龙寺青龙寺“鬼子母”壁画(局部)
入清后,中国北方出现了“娘娘”信仰。这种神祇的命名毫无宗教背景,强烈的民俗嫁接,使得“揭钵”题材消融在“祈子”的语境中,山西河曲县娘娘庙(图八)遗存了一殿清代壁画,图中有52个人物,在孩童的表现中“五子登科”、“习武图”和“礼仪图”等,是典型的“百子婴戏图”样式,而端坐其中的娘娘,自然也与“鬼子母”贴近。清代对于“揭钵”体的回归,再次以壁画的样式向大众传播,遗憾的是,原教的语体已经几乎消失,为了迎合民众需求,趋向“观音”信仰成为不二选择。纵观佛教发展,观音大士与诃利帝母并非脱胎一处,在发展过程中,“鬼子母”骇人的身份很难被世俗接受,“娘娘”作为一种笼统的称谓,成为中国民间底层求子信仰的基础。而据此产生的具有教化功能的图画大量传播,植根民间。
作为中国宗教图像的重要表现载体,壁画在发展过程中不断突破宗教语体的羁绊,宋代之后,更是将世俗化与三教合一作为搭建通向大众的普世价值。早期的主尊佛像表现与“曼陀罗”的中心式表达被庞杂的“千官列雁”取代,追求多元的宗教思想将三教紧紧地捆绑在一起。因此,佛教的神祇不断脱离浓重的“救赎”与“拔苦”意味,追求一种自然与世人的贴合,成为人们对“母系”神祇的精神寄托。鬼子母的形象在壁画的蜕变过程中,与创生时的形象完全不同,民间强大的“造神”功能由此启动,而“婴戏图”虽然在创立之初毫无宗教寓意,“揭钵”的语境能够迅速将其带入,形成理想的空间场域。“圣母”题材是“揭钵”在中国宗教蜕变的最后栖息之地。
二、“婴戏图”民俗化之滥觞

图九 南宋 庭园婴戏图银盘 直径15.9厘米 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

图十 山西代县当代面塑大师张海平塑爬娃娃
从民俗学角度看,南宋是“婴戏图”与社会高度契合的王朝,“摩睺罗”在江浙一带逐渐定性,发展成为一类泥塑,成为千家万户之玩偶。《东京梦华录》载:“七夕前三五日,车马盈市,……又小儿须买新荷叶执之,盖效颦磨喝乐。”宋代出现的执莲童子与“摩睺罗”的造型在此重叠。而《东京梦华录》记载这一玩具主要在七夕前后出现,南宋时期的著作《梦梁录》、《岁时广记》和《武林旧事》也记载了这一风俗[4]。七夕又名“乞巧节”,祭祀的对象为牛郎织女,将此物进行供奉,除了“玩具”功能,更是“祈子”供祭。
唐、宋时期,还有一类童子造像与“摩睺罗”相仿,就是佛教“四生”之一的“化生”,早期为菩萨样造型,后演化为“童子”形象。化生为中元节所供养的祭品,唐代为蜡制[5],并且出于西域,与摩睺罗为同一物。化生是“七月十五”女子用来祈嗣的物品,中元节女子在盆中盛水,将腊样的“化生”放入水中拍打,意寓生子。化生的材料为蜡,非常轻便,放入河中不仅可以拍打,还可点火作为河灯漂流祈愿(图九)。
而这类蜡样化生并没有遗存下来,在随后的发展中,中国北方出现了不同的材料进行加工的“化生样”。在山西晋北与晋中七月十五供奉制作一种面塑人偶,俗称“爬娃娃”(图十),造型为蛙状,有着蜡样“化生”的特征。这两类材料不同的“中元节”献祭的物品,似乎有着很重的渊源[6]。从陶瓷到面塑直至泥塑玩偶,“摩睺罗”与“化生”在宗教语体的式微中逐渐走向世俗化。尤其是借由面塑文化的形成,至今山西各地仍在活态传承着这种样式。虽然造型上趋于更加复杂的装饰,但最为经典的“爬娃娃”造型,是“化生”孩儿的延续。面塑的发生,在早期被认为是祭祀的替代品,这种与陶俑具有相同衍生形态的食品,在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中尚不明确,但“中元节”作为中国传统的“鬼节”,并不具祈嗣作用,“化生”与“摩睺罗”在功能上的交叠,也说明了早期汉族祭祀仪式的趋同性,对于子嗣的祈求,是人类繁衍生息的首要目标。因此,即使民俗在各类历史原因的阻隔下和演化中逐步脱离本体初始,但样式在地域的流迁中,依旧能够保留一部分价值。这两种“孩童”的样式虽然不能证明是“婴戏图”的初源,但绝对与此息息相关。

图十一 北宋 定窑白瓷童子荷叶枕 高8.3厘米 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藏
在宋代的民俗物品中,还有一类与孩童形象有关系物品,是瓷“孩儿枕”(图十一),此类夏季睡枕俨然“居家必备”。有学者梳理了宋代出土的瓷枕,最早为元祐元年(1086)的定窑“童子荷叶枕”,和一件大观年间(1107-1110)瓷枕共同之处是都有莲花装饰,这种样式显然具有浓重的“摩睺罗”痕迹。由于“孩儿枕”会有莲瓣的装饰,这一样式正是佛教文化的介入。而宗教语意渗透使得这一物品更容易被人接受。“孩儿枕”作为一种“寝具”具有了更加美好的寓意和佛教意味,宋金时期通行海内,成为繁衍子嗣的象征[7]。
明、清时期,“婴戏图”在陶瓷等工艺制品上的应用更加普及(图十二、十三、十四),而木版年画作为更加迅速和广泛的媒介推动了图像的传播。传统地域的几大年画刻版都有“婴儿戏春”的图样印刷。因此,“婴戏图”的推广在世俗化与佛教交融的宋代开始,逐步融合成型。样式逐渐形成一种定式,而“杨柳青木版年画”“桃花坞木版年画”“绵竹木版年画”与“潍坊木版年画”正是推动这种图像走向大众最为直接的工具。“婴戏图”完成了从墙壁到纸张印刷的身份转化,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普世价值作用。广泛的群体认知,开始导致人们对“婴戏图”样式本源问题提出讨论,因此,才有了民国时期胡适先生对其本源的追溯。
三、“乾隆造”“百子婴戏剔红”的工艺特征
乾隆雕漆在海内外收藏甚众,检索香港苏富比历年剔红雕漆拍卖,约203件剔红雕漆作品中,约80件乾隆年间制作,但“百子婴戏图”作品仅见于两件标注“18世纪”的“剔红婴戏图臂搁”和“剔红婴戏图桃形盖盒”[8]。这两件作品未明确断代为乾隆年间,且皆为把玩小件。这并非此类作品匮乏,而是精品太少。由于“百子婴戏图”人物众多,夹杂了山水亭台,制作周期极其漫长,如此庞杂的人物与山水穿插构图必须有极强的刀工与画面控制能力,传世之作较少是可想而知。
大量的清乾隆年间的剔红作品存世,足以说明这一时期对“剔红”工艺的推崇。而“婴戏图”作品鲜有问世,是否是乾隆年“婴戏图”遇冷的例证?从故宫博物院传世的乾隆剔红“百子宝盒”(图十五)看并非如此。这件剔红盖盒不仅极尽繁复,金属胎盒盖更是富于皇家气息。盒盖描绘有整整100位童子在其中穿插玩耍,工艺极其精湛,是一件剔红极品[9]。同时,作品向我们展示了乾隆“剔红”工艺革新特征。究其原因,即为其他门类的交融促进了“剔红”工艺发展。

图十二 明成化 斗彩婴戏杯 高4.7口径6足径2.7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十三 明宣德 青花婴戏图碗 高6.6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十四 明嘉靖 青花婴戏图盖罐 高26.5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由于康熙、雍正两朝对明代“剔红”的复原只是泛泛,挑剔的乾隆帝自然难入法眼。而江浙地区的牙雕、竹刻工艺精密纤细,乾隆帝对其倍加青睐。受此影响,乾隆三年始,钦命造办处“牙作”名匠参与雕漆工艺研发,其中多为粤、苏工匠领衔,最为著名的有陈祖章、施天章、叶鼎新、封岐、封镐。这些工匠都是牙雕竹刻执牛耳者。有如此“名匠”的参与,一时间工艺突飞猛进,宫内“云龙宝座”皆由此出[10]。然而,诸多的牙雕艺人参与到雕漆技艺之中,依据何在?《养心殿造办处各做成活计清档》载,雕漆并非在造办处加工,而是成于南方。其中,除了苏州聚集了大量的匠人外,主要是宫廷造办处对明代永乐雕漆的仿制久久不能成功,由于受到苏作刻竹、牙雕工艺的影响,明代嘉靖、万历年“剔红”入刀不藏锋风格亦然。这一时期的“剔红”起形高峻,但打磨程度远远没有明代圆润光洁。至乾隆朝通过多种工艺雕刻技法融合创新,方突破技术壁垒(厚料漆与雕刻技术),乾隆“剔红”研制成功。而在诸多匠人中,到底谁是真正复原雕漆之人?在清宫档案中,发现封氏兄弟在乾隆朝备受赏赐,较之雍正数目剧增,封岐回乡受赏纹银三十两,往返盘费皆数官家报销,不立奇功,焉有如此待遇?可以推断,乾隆三年研制成功的雕漆“剔红”应当是封岐所做,文献中亦记载详细[11]。自此,清代开始将雕漆作坊放在苏州织造进行,愈加精进。

图十五 清乾隆 剔红百子图宝盒 高8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图十六 清乾隆 剔红“百子婴戏图”捧盒盖 崔文煜先生收藏
乾隆时期盛产“剔红”,然剔红“百子戏婴图捧盒”极少面世。2016年,收藏市场现出一件口沿部稍有残损的剔红“百子婴戏图捧盒”(图十六),从题材到造型以及雕刻手法来看,属于乾隆朝重器。此盒直径38厘米,高度18厘米。盒身浑圆饱满,包浆高古,采用朱色大漆反复髹涂,漆膜厚度可达6毫米。盒采用了中国传统的雕刻斜切技法,使得作品平面高点能够保持一致,又不失层次变化。色彩所用为朱砂,历经二百余年而不衰退,显然是功毕“开漆”之后日渐蜕变,大漆色调逐步减淡,呈现出矿物色的本真,才使得红色能够累年彰显。
从制胎到雕刻,这件剔红“百子戏婴图捧盒”显然与元、明时期有着较大的变化。清室漆器中有“八宝”制胎的工艺,但乾隆漆器的胎体、形制、工艺不断趋向简略实用,去除繁琐的环节,提高了加工效率绝非是对古法的不敬,而是技术提高之后熟稔的一种自信。从工艺可断为典型乾隆“南工”剔红漆器。
四、从个案“百子婴戏捧盒”谈剔红的空间意趣营造
图像之于工艺,不仅是载体与寓意。图像本身在历史的演化中,能够形成相对独立而且丰富的审美域场,这种功能在视觉传达过程中尤为突出。这件乾隆剔红“百子戏婴图捧盒”,圆形的雕漆盒,整体设计为柱状扁盒。上、下两个外边,均有向内弧度的圆形倒角,整体造型浑圆。在结构风格上,利用“回纹”与“仰莲纹”的设计将漆盒分割为三个区域。顶面是图像的核心“百子婴戏图”(图十七);中间则是八组花卉草石;最下面的圈足部较小,但是有此设计增加了整体盒身精巧的意味。中间部分花卉的内容为牡丹、栀子、芙蓉和秋菊一类的题材,每组基本都有太湖石的陪衬,间或有兰草进行调节。八组花卉被“宝相花”、“缠枝纹”曲隔,这一题材在北宋开始出现,并逐渐在陶瓷装饰中应用。乾隆时期“宝相花”作为辅衬具有标志性特点,与宋代“宝相花”不同之处,乾隆时期更加注重装饰的一致性,因此,利用缠枝纹取代一般的云纹能够看到清代纹样在装饰取舍中的变化。此处的“锦地回纹”较圈足部要大一些,单位边长逾1厘米。采用深镂减地技法突出了花草,剪影效果也加重了“折枝花”的造型。
顶面为主体画面(图十八),53个人物雕刻其间,建筑与山石将每组人物分割,画面繁而不杂,动静皆宜,四周亭台楼阁,人物穿行不息,精心的布局完全没有造成观读的混乱,整体呈现出“左虚右实”的节奏变化。左侧有最大的建筑厅阁,采用了开放式厅堂设计,实则与后面映衬的菱窗隔扇形成一个序列建筑单位,这种亭台楼阁单体属于祭祀所用“献殿”。而其中端坐的人物正是“圣母”,在其周围有奉茶侍女及捧卷童子,意味着敬母孝亲。童子图像呈放射状布局,题材描绘了“上元节”场景。作为年俗的尾声,农历正月十五与春节构成了一个整体“年”的单元。这一习俗形成于汉代,当时的道教在这一天祭祀“太一神”,这是道教至高无上的天神。由于道教习俗的民间普及化极高,司马迁更将“上元”编入“太初历”中,成为历法节气中的重要节点。魏晋时期农桑文化植入其中,增加了祭门神、蚕神的习俗,此外,“迎紫姑”作为一种补充也有对蚕业织造祈愿之意。隋、唐时期的“上元节”演化为民间祭祀盛大的礼节,尤其隋炀帝在正月十五,不仅有百戏杂耍,灯光火烛所费甚巨,逐渐将汉代形成礼佛敬神的宗教膜拜改为开宵狂欢的全民庆贺。唐初,高祖与太宗沿袭了隋末传统,放灯成为正月十五标志性的欢庆方式。五代两宋“中元赏灯”方兴未艾,《东京梦华录》描绘了“灯山上彩,金碧相射,锦绣交辉”。《武林旧事》则有“闲设雅戏烟火,花边水际,灯烛灿然”。可见,宋代在元宵赏灯的风俗继承上不遗余力。在南宋宫廷画师李嵩《观灯图》(图十九)中描绘了孩童手持彩灯玩耍,女子兴弹琵琶的场景。明、清时期,由于“蚕神”一直作为主体信仰传承,将唐、宋时形成的扁形“面蚕”升级为圆形的糯米团子,俗称“元宵”,这种食物香甜味美,寄予美好,因此,“上元节”逐渐更名为“元宵节”,意味着团团圆圆。
盒盖部分雕刻内容为“闹元宵”,即“上元节”开宵,内容大致可分“奉茶图”“耄耋图”“有余图”“舞狮图”“礼乐图”五组。“奉茶图”作为整图起首部分布局舒朗简洁,人物的主次关系非常明确,持扇而坐的“圣母”与两名侍女疏密有致,不等边三角构图在稳定中寻找着变化。画面的中心部分为“耄耋图”,描绘了童子戏蝶与抚猫,猫与蝶在中文谐音“耄耋”,寓意长寿。正月里,本并无蝴蝶,手持为玩具,该图主要人物有七人,抚猫一人,其余五人追逐嬉闹,一名童子将蝴蝶高高举起,旁边二人拽扯争抢,竟有一孩仰面摔倒,远处有一儿童竟然看呆一般,怔怔地站在那里,好不热闹。构图采用了动静结合的方式,对童子天真烂漫的玩耍倾力表现。抚猫的静与争蝶的动,构成了强烈的对比效果。尤其是对于人物动态的刻画捕捉十分生动,同时将这一幅充满动感的图像布局“奉茶图”一侧,动静之间,怡然天趣。

图十七 (传)南宋 李嵩 观灯图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衔接右侧的“有余图”共有三组场景,分别是“钓鱼”、“游灯”和“观蟹”三联组图。钓鱼者起于图像中央池塘,四名儿童持竿垂钓,三人神情专注,背影沉稳,只有一名儿童受到锣鼓的影响而侧目观看,形成侧背变化。本组图像采用了“S”形构图,在狭长的空间中经营位置,“观蟹图”作为图像的承接转折,巧妙地掩藏在假山之后,并与下方的“游灯图”形成强烈的构图指向。螃蟹八爪在民间有“招财”之意,同时意喻和谐,与金鱼构成了“招财进宝”的商贾文化。利用鱼蟹图像含蓄地对此类吉祥寓意进行暗合,煞费苦心。画面的高潮是“游灯”。这也是“上元节”的代表,图中锣鼓喧天唢呐翻飞,下方的金鱼灯随杆游走,势作合围状,童子步履如飞,灯影晃动。鱼灯的设计与钓鱼图构成了“连年有余”的美好寄托,这种首尾呼应的图像表达,强化了民间社火深层次的植根性。
“舞狮”在画面的中心部分,这种习俗作为“上元节”游戏活动出现在明代,两只狮子摇头摆尾相互顾盼,一名童子手持长杆,并系彩球相逗,狮子为两人首尾装扮而成,与今天状貌完全相同。狮身毛发采用分段式刻画,背部毛发粗率而腹部柔软,刻刀对质感的刻画十分得心应手。“舞狮图”叙事场景宏大,除了舞狮充满动感的表达外,锣鼓钹挠的表现一样精彩,画面中一名童子正在敲击锣鼓,这种水平系在腰间的小鼓极为轻便,童子的双手上下打击,一起一落,鼓点随密锣合拍。铙钹为铜制大镲,两镲拍合,错落间体现出乐器的演奏方式。而铙钹锣鼓又构成了“战舞”伴奏的核心单位,下方一组“演武图”诠释了这种表征,两名弱冠少年英姿飒爽,威风凛凛。手中大刀红缨风驰电掣,与舞动的狮子闪转腾挪,场上似乎尘土飞扬,杀声震天。对于猛兽与武士的信仰,唐、宋就已十分流行,这种威猛的表达,不仅有着强壮体魄的祝福,也是对国泰民安的祈愿,对于饱受战争的中华文明,保家守土成为一种主体意识自然的流露。
“礼乐图”设置在右侧上、下阁楼中,楼上为童子读书,三五成群,坐而论道。楼下童子抚琴,一派祥和。亭台楼阁内部的表现力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物的动态,增加了儒雅的气质,朗朗书声与鼓乐悠扬营造出浓重的儒家气氛,同时强化了中华文明谦谦君子的文明气息。
纵观此图,利用谐音暗喻的手法对中国传统文武、礼乐、福寿、富贵、祈福进行了多向表达,这是传统手工艺极其核心的民俗承载,浓烈的节日气氛能够将这些美好的寓意集中凝练,加强表达意境。
这五类图像在空间上并非单独曲隔,人物安排疏密错落有致,俨然一体。亭台、山石、树木相互呼应,整体形成半合围的构图,将热闹的“中元胜景”锁在其中。在前后景深的表现当中,为了体现深远的效果,利用近大远小的关系将前景人物、房屋与后景进行了由大到小的渐变,表演者作为主要人物体量最大,远处阁楼的看景人物不见眼目。此类透视不仅是传统山水点景人物中“远人无目”的表现,且极有可能是受到郎世宁一派西方焦点透视的影响,使得图像写实性得到了进一步的细节刻画。
对于配景的刻画,本图显然有着极高的水准。与故宫所藏雕漆漆盒相似,树木进行边衬,形成了不规则的内框,这就打破了原有的圆形外框的呆板,树木枝丫在穿插中折枝出入,体现出域外造境的美学观,同时延伸了画面的表现力,这种巧妙的内框造景,显然也是乾隆造“剔红”的特征。图中树木以“松柏槐柳”最多,此类乔木有“四君子”的美誉。树木的雕刻技法大量借鉴了竹刻的样式,对于质感把握极其充分。同时,折枝的处理巧妙而不失意蕴,树木的虬曲盘桓时入时出,符合中国画悠远的气质。山石的描绘主要以远景而为,远山藏岱,树木掩映,云气氤氲绕于峰峦。近景中的太湖石将画面进行了虚空隔断,增加了画面下部的重量感,同时能够与童子形成掩藏的巧趣,使得画面玲珑剔透极具灵动。上、下两段使用了流云与栏杆作为休止,既提高了装饰性,同时丰富了空间层次。画面在人文意境的营造下令人流连其间,反复读赏不觉乏味。
从“摩睺罗”到“鬼子母”信仰,“百子”题材的演进不断地丰富着寓意的表达,对于民俗语意的贴合,无论是“中元节”或是“上元节”的适应,都在以广泛的“普世价值”为目的进行着流传。而在艺术的表现当中,正是陶瓷、金工、壁画对它的广泛采用,才能够让我们拨开迷雾,寻迹发端。尤其是在寺观壁画中的图像表达,使其成为面向大众、媒介传播的重要手段,这也正是“婴戏图”能够在人物题材创作中独树一帜之所在。中国是“剔红”的发源地,并且在本土逐步蜕变革新,复杂的工艺在每个朝代都因能工陨落,而淡出世俗,绝尘海内。而自元以后的兴邦之日,历任开国帝王无不对其青睐有加,这也注定此工艺需要不断地进行还原。清代乾隆造“剔红”技艺虽然不若前朝,但在工艺继承上善学各家,尝试突破,由于加入了新的雕刻技术,使其在表现力当中更具观赏意趣。而乾隆年间大量制作“剔红”,不仅是对国力的宣扬,更是将这一耗时费力的“奢靡之器”推向了大众人群。从胎形的材料变化,也能够看出乾隆“剔红”在“南工”的推波助澜中复兴精进,开创了新的“剔红”工艺时代。
在存世的乾隆“剔红”中,这件剔红“百子婴戏捧盒”不仅造型生动,工艺精湛,其精彩绝伦的美学表达折射出浓郁的高古意境,这种人文情怀是对元、明漆器的追赏,也是对宋风意境的倾慕。
[1]程沁:《苏汉臣〈秋庭婴戏图〉研究》,《绘画美学》,第64页。
[2]曹淦源:《“婴戏图”试论》,《景德镇陶瓷》1987年第4期。
式中*表示卷积运算符,在实际光学测量中,常用二维高斯函数表示光学成像系统的点扩散函数h(x,y,di),即
[3]李翎:《政治的隐喻:岩山寺金代鬼子母经变(上)》,《吐鲁番学研究》2015年第2期。
[4]赵伟:《神圣与世俗——宋代执莲童子图像研究》,《艺术设计研究》2015年第4期。
[5](元)杨士弘:《唐音引唐岁时纪事》。
[6]杨琳:《化生与摩侯罗的源流》,《中国历史文物》2009年第2期。
[7]孙发成:《宋代的“磨喝乐”信仰及其形象——兼论宋孩儿枕与“磨喝乐”的渊源》,《民俗研究》2014年第1期。
[9]王冬:《剔刻尽现繁华世,巧夺天工满乾坤——清乾隆朝雕漆的艺术成就》,《古玩》2007年第4期。
[10]陈丽华:《清代乾隆朝雕漆》,《收藏家》2002年第1期。
[11]杨伯达:《清代苏州雕漆始末——从清宫造办处档案看苏州雕漆》,《故宫博物院院刊》201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