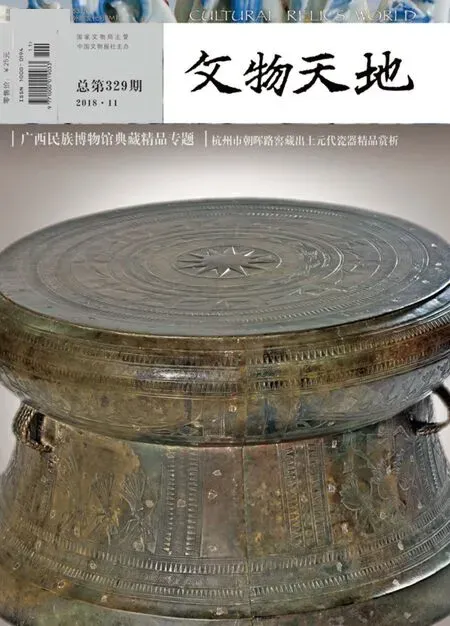21世纪以来北方青瓷窑址考古新进展
一、北方早期青瓷窑址考古
北方地区早期青瓷窑址并不多,目前知道的主要有河南安阳的相州窑址、巩县白河窑址,河北临城陈刘庄窑址、临漳曹村窑址、磁县贾壁窑址、峰峰临水窑址、内丘早期邢窑址,山东淄博寨里窑址等。
贾壁窑址位于磁县贾壁村[1],产品主要为青釉器物,主要器形有碗、高足盘、钵等,特征与曹村窑基本相近,碗均为深腹饼形底。胎质普遍较粗,色较深,黑色斑点明显。外腹施釉不及底,流釉明显,釉色青黄,玻璃质感强。部分器物胎釉略细,质量较好。贾壁窑址在胎料的处理上已区分出了精与粗并进行比较严格的控制。多为素面。窑具是筒形的支烧具与三叉钉形间隔具。明火裸烧。
峰峰的临水窑址、邢台的西坚固窑址可以确认是北朝时期的瓷窑址,在邢窑内丘西关窑区与临城陈刘庄窑区也发现了具有北朝风格的青瓷残片[2]。这些窑址产品基本器形以深腹的饼形底碗、杯为主,外腹施釉不及底,内底因流釉而积釉严重。临水窑址主要以粗胎为主,最突出的特点是在部分产品的口部施用化妆土。这类碗可能占到了产品的一半左右。西坚固窑址位于邢台县龙华乡西坚固村,产品也以碗为主,胎、釉、造型与贾壁、临水同类器物相似。内丘西关和临城东刘庄北朝风格的青瓷标本,厚胎、流釉、开片以及基本胎质、胎色等与临水窑址、西坚固窑址产品相似,但胎质相对比较精细。这可能与本地区是邢窑的中心产区有关[3]。
荥阳翟沟可以到早隋至初唐,生产一批以碗为主的粗青瓷[4]。
寨里窑址[5]位于山东淄博市淄川区寨里,共有四个地点,时代从北朝晚期一直延续到唐代中晚期。其中北朝晚期器物主要是碗,少量的盆类器物。碗浅弧腹略浅,饼形底。胎厚重而疏松,胎色较深,有大量的气孔的黑色斑点。釉多呈青褐色、黄褐色和深褐色,后者釉层厚处接近于黑釉,外腹施釉不及底。流釉严重,内底一般施厚釉。北朝末至隋代器物品类明显增加,除碗以外,还有盆、罐、高足盘、盒、瓶、贴花罐等。碗腹明显加深,仍旧为饼形底。胎釉质量有所上升。胎体变薄,胎质变细,胎色变白,黑色斑点明显减少。釉色变淡,多呈浅的青褐色、浅青色,玻璃质感强,施釉更加均匀,釉面明显干净而更莹润,外腹仍旧施釉不及底。有一定数量的装饰,尤其是贴花罐制作工艺复杂,题材丰富,有莲花、宝相花、宝塔、连珠纹及人面等,代表这一时期较高的制作水平。到了唐代中晚期,器类又非常单一,主要是碗,基本为黑釉,釉色不够纯正,产品质量一般。窑具主要是两种,一种是筒形的高大支烧具,另一种是三叉钉形间隔具。明火裸烧。
此外,在山东地区还发现一批隋代前后的青瓷窑址,包括曲阜的宋家村、徐家村、息陬、泗水大泉、尹家城[6]、泰安中淳于[7]、枣庄中东郝[8]、临沂朱陈[9]以及邻近的徐州户部山等窑址[10]。这批早期青瓷窑址最早可到北朝晚期,最晚可到初唐,以隋代为主,产品面貌比较接近。以宋家村窑址为例,它位于曲阜原防山公社的宋家村,瓷器以碗为主,占半数以上,另外还有罐、盘口壶、盘、高足盘、盆、瓶、砚、枕等。碗均为深腹饼形底。胎质较细,呈青灰胎、灰白胎和近白胎;均为青釉,外施半釉,呈青绿色、淡青色和青黄色等,玻璃质感强。素面为主,装饰有刻划、贴花等,题材主要是花卉。使用支烧具与三叉钉形间隔具[11]。
这几个窑址均是在20世纪发现,时代原来大多笼统地定在北朝或北朝晚期,许多材料从整理、研究到发表已经到了本世纪初。这些窑址的发现,对于探索北方地区瓷器的起源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将北方地区瓷器的烧造历史由唐宋时期提前到了北朝时期至隋代。
新世纪以来的相关工作主要在河北南部、河南北部这一相邻地区的安阳、邯郸、邢台一带展开,通过多年持续的调查与发掘研究工作,确认这一地区是北方地区早期青瓷的中心分布区,包括漳河流域安阳的相州窑址、临漳的曹村窑址以及邢台的早期邢窑遗址。河南除了豫北以外,在豫中地区也获得了突破。
相州窑位于安阳市,是北方地区早期青瓷的代表性窑场。北魏天兴四年(401)始置相州于邺城。580年相州南迁至今安阳城,安阳改称相州,因此有学者将隋代安阳发现的窑址称为相州窑。窑址位于洹水南岸安阳城区,1974年发现并进行过清理,但大规模的发掘要迟至2006年以后。2006-2010年先后进行了三次发掘,发现了瓷器坑、灰沟、沉淀池、窑炉以及废品堆积区等丰富的遗迹和包括窑具、青瓷产品、窑渣等在内的大量遗物。瓷器主要器形有碗、罐、瓶、钵、盂、高足盘、高足杯、器盖及瓷塑等(图一),瓷塑包括人物俑与动物塑像。釉色以青釉为主,可能兼烧白瓷、褐釉瓷。总体上器物的胎壁较厚,胎色灰白;青釉呈青灰、青褐等色,一般器物外腹施釉不及底,釉层薄而均匀,底部流釉与积釉明显。素面为主,有简单的花卉类纹饰,技法包括刻花、划花与印花三种,题材主要是莲瓣纹,有仰莲、覆莲,有的装饰在瓶的颈部,有的刻在盘子的内底。此外还有卷草纹、花叶纹、宝相花纹、几何纹、乳丁纹等。明火裸烧,碗类大口器物叠烧,器物之间使用三叉钉形间隔具。时代主要是隋代,下限可到唐代早期[12]。
此外安阳地区于1995年在辛店乡灵芝村清理了一处窑址,出土有少量的瓷器,有盒、罐、瓶和钵形器等,面貌上与城区发掘的窑址可能差别比较大,而与贾宝墓中出土的青中泛黄、近似青白釉的瓷器较为接近,可能属于另外一个窑业类型[13]。
曹村窑址[14]位于河北临漳县习文乡曹村附近的漳河河床上,邺北城东城墙外约500米,与安阳的相州窑处于同一流域,2009年调查发现。采集到的瓷器主要为青釉器物,器形以碗为主,另外亦有豆形的高足盘以及钵类器物。碗作深腹饼形底。胎质明显可分成精粗两类,精细者胎色浅白,粗者胎色较深。但不论精粗产品,胎质明显都较疏松。釉色泛黄,釉层薄,釉面光亮,剥釉现象严重。窑具主要是筒形的支烧具与三叉钉形间隔具。明火裸烧。调查者认为时代在东魏至北朝晚期左右。2016年进行了正式发掘,发现了窑炉、灰坑与灰沟等遗迹。出土的青釉器物主要是深腹饼足碗,发掘者认为绝大多数器物为低温青釉器,属于低温釉陶,而高温青釉瓷器的比例极低。对于其时代,发掘者认为在北朝晚期而不是东魏至北朝晚期[15]。
在邢台及内丘与临城邢窑的核心分布区内,还发现了多个隋至初唐时期的青瓷窑址。邢台的隋代邢窑大规模的发掘时间虽然在1997年,但资料的整理与出版则延宕至2006年,因此也是21世纪的重要考古成果之一。产品以白釉瓷器为主,其次是黑釉瓷器与所谓的黄釉瓷器,报告中所称的黄釉瓷器可以归入青瓷瓷器中。以深腹饼足碗为主,少量的钵与高足盘。胎体较为规整,胎质较细,胎色较白,里外均施釉,内底积釉明显,外腹施釉不及底,流釉与积釉明显。胎釉之间普遍施以一层白色的化妆土,衬托出釉面莹润的厚重感[16]。
在邢窑核心分布区的内丘与临城地区,隋、唐时期的窑址至少有白家庄、冯唐、内丘城关、西丘、中丰洞、北大丰、代家庄、陈刘庄等近10处窑址。从邢窑的初步分期来看,在北朝时期至隋代早期,以烧造青瓷为主,白瓷较少,主要器形以深腹饼形底的碗为主,包括钵、盘、罐、瓶等,青瓷器物的胎体粗糙厚重,黑点和气孔多。到了隋代,白瓷超过青瓷成为主流,青瓷尚占有相当的比例;器形总体上变化不大,以深腹的饼形底碗为主,包括盆、盘、钵、罐、瓶等,以深腹饼形的碗占主体,胎质有所进步,总体上仍旧较粗,胎体较厚,外腹施釉不及底,质量一般。从质量上说,这个时期是河北一带邢窑地区青瓷发展的高峰。初唐以后,青瓷的比例与质量不断下降,白瓷取代青瓷成为了主流[17]。这样,早期青瓷在北方地区的流变基本清晰。

图一 相州窑隋代青瓷

图二 耀州窑宋代青釉盖

图三 清凉寺窑址出土的临汝窑青瓷
豫中白河窑址的发掘,取得了重要成果[18]。白河窑遗址位于河南巩义市北山口镇白河村。发掘者认为窑址时代始于北魏,延及唐代。这个时代可能定早了,窑址主体年代还是以隋代为主。隋代产品以青釉瓷器为主,白釉瓷器次之,黑釉瓷器少见。青釉瓷器以碗为主,另有盘、豆、钵、盆等器物。胎体一般都较厚重,其中的碗作深腹饼状实足,口沿外饰弦纹一道。大口类器物如碗等一般器内腹均施釉,外腹施釉不及底,器内积釉现象较为严重,外腹则流釉明显。基本为素面,少见装饰纹样。均不见化妆土。明火裸烧,窑具有大型支烧具与三足钉足间隔具。唐代,其产品以白釉瓷器为大宗,黑釉和酱釉瓷器次之,不见青釉器物。
二、耀州窑址考古
北方地区的青瓷,始于北朝末期至隋代初期,兴盛于隋,延及初唐,中唐以后被白瓷所取代,胎釉质量进一步下降,由此形成北方白瓷与南方青瓷的大格局。但在北方唐代白瓷的大格局中,有一个窑址反其道而行之,晚唐以后青瓷逐渐成为主流,五代、北宋时期以青瓷名满天下,这个窑场就是耀州窑。
耀州窑唐代创烧于黄堡镇,五代成熟创新,宋代鼎盛繁荣,金代延续发展,金末蒙元时期日渐衰落,明中期以后逐渐停烧。唐代耀州窑先烧黑、白、茶叶末釉和唐三彩、低温单彩等,后又烧黄褐釉瓷和青瓷,水平逐步提高。五代则以青瓷为主,水平迅速提高。宋金耀州窑繁盛时期的青瓷以装饰工艺中的刻花和印花工艺大量使用而独具特色,装饰纹样达上百种,其中植物纹样以牡丹、菊莲为主(图二),动物纹样以鱼、鸭、鹅等为主;人物纹样则以体胖态憨的婴戏为最多[19]。
20世纪耀州的工作主要集中在黄堡镇一带,这里是唐宋时期耀州窑烧造的中心区,尤其是宋代的窑址,沿着漆水河两岸绵延十多里路,分布范围广、密度高、地层堆积厚。金代后期开始,规模逐渐萎缩,工艺水平粗糙,窑场日渐衰落。从1959年开始,至1997年,先后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发掘,并出版了三部上百万字的发掘报告,对鼎盛时期耀州窑的发展脉络与基本面貌有了全面深入的了解。
21世纪的工作则主要集中在陈炉地区,重点探索北宋衰落后的耀窑面貌。陈炉地区窑址群包括立地坡、上店与陈炉三大片,2002-2004年进行全面、拉网式的调查、勘探与重点窑址的试掘,基本搞清楚金元及以后耀州窑衰落时期的基本面貌及其流变过程[20]。
黄堡镇耀州窑随着金代的衰落,其中心窑场先是逐渐转移到立地坡与上店一带,明清时期再转移到陈炉一带,由此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耀州窑后期发展过程。
金代的立地坡规模不大,处于向黄堡镇学习的阶段,到了元代,规模与区域则迅速扩大,在立地坡3-5公里范围内,发现了20多个烧造区,几乎所有的烧造点均有元代的堆积层,由此完成了耀州窑从黄堡镇向立地坡的转移。
上店主要是金元明时期,规模一直不是很大,分布散,是立地坡的重要补充。
再往后,距立地坡约5公里的陈炉窑场兴盛发展,其窑场规模与制瓷工艺均超过了立地坡,明清以降,这里形成了新的耀州窑瓷业中心。
立地坡创烧时期的金代,产品以青釉为主,黑釉占极少部分,主要是日常的碗盘类生活用品,装饰以印花为主,刻划花不多。纹饰以植物花卉为常见,动物、人物纹比较少。青色较为纯正,胎质致密,胎釉结合较好,质量较佳。
蒙元时期是立地坡大发展时期,窑场分布广泛,产品中除了青釉类制品外,黑釉器物也有了较大发展。此外还有酱釉与茶叶末瓷器。种类仍旧主要是日用品。青釉泛黄,胎釉质量进一步下降。
元末明代,产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青釉只占极少部分,大量的为黑釉瓷器,也有酱釉、茶叶末釉、白地黑花、复色釉、白釉黑箍、青釉白彩等。青釉瓷器基本进入尾声[21]。
陈炉金代晚期开始出现,一直延续到1949年后的合作社。鼎盛则为明清时期,与立地坡相似,这一时期的青瓷生产,已占整个窑业中极小的比例,基本淡出历史的舞台[22]。
三、河南青瓷窑址考古——临汝窑、汝窑
河南、河北是北方地区最主要的两个窑业大省,两省交界处在北方早期青瓷的发展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是这一青瓷传统在唐代早期以后逐渐式微,并从此再未回潮。
而河南中部的伏牛地区,除靠北的巩义等区域有少量早期青瓷外,整体上窑业的出现时间相对比较晚,唐代的规模仍旧不是很大,成规模成序列的发展则要迟至宋代。与豫中北地区以生产白瓷与白地黑花瓷器为主不同的是,这一地区的青瓷在陶瓷史上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当南方在北宋晚期至南宋初期越窑衰落、龙泉窑未兴起的“空档期”,这里的青瓷生产异军突起。以临汝窑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而汝窑名气最大。当然,这一地区的钧窑也可以归入青瓷窑系中,但其产品与传统的透明薄釉、单色釉类青瓷已完全不同,这部分将在钧窑部分再论述。
临汝窑的名称是冯先铭先生1964年对河南省临汝县宋代瓷窑遗址调查后提出的。他认为汝窑由两个主要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专为宫廷烧制的瓷器,烧制时间短,生产数量少,而质量则很精;一部分是为民间烧制的瓷器,这是汝窑的主要部分,烧造时间长,生产数量多,质量也比较好,后一部分称为临汝窑[23]。现在多数学者认为汝窑是在临汝窑技术发展基础上因宫廷的需要而演变而来的。
临汝窑的分布以禹州市为中心,包括周边的禹县、宝丰、郏县、鲁山以及西北的新安、宜阳、东南内乡诸县。临汝窑大约北宋早中期创烧并初步发展,北宋晚期兴盛,金元时期逐渐走向衰落。产品丰富,以青瓷为主,亦兼烧白地黑花瓷、黑瓷、三彩瓷、酱釉瓷、花釉瓷和钧釉瓷等。青瓷以豆青、青绿为主,亦有青褐、灰青、天青等。青瓷在风格上可以分成三大类:一类是豆青和天蓝釉素面瓷,有的釉面青中偏黄;二类是具有耀州窑青瓷特征的刻、印花青瓷;三类是钧窑系的钧釉瓷。印花与刻划花装饰为主要特征,题材多为喜庆吉祥的牡丹、菊花、莲花、童子、鱼鸭、海波等。尤其是鼎盛时期的北宋晚期,题材丰富,纹饰繁缛,釉面光亮,胎釉质量高超(图三)[24]。由于伏牛山地区临汝窑、汝窑、钧窑类产品常在同一窑场中出现,因此21世纪以来临汝窑的发掘工作主要在宝丰清凉寺与禹州神垕地区展开。
官用天青色汝窑瓷器烧造地的确认,是上个世纪陶瓷考古的重要内容之一,1986年在宝丰清凉寺发现了一批天青釉瓷器,确认这里就是北宋汝窑的产地[25](图四)。由此,正式考古工作于翌年随即展开,1987年完成了第一次试掘后,分别于1988-1989、1998、1999年进行了连续的考古发掘,但这几次考古发掘发现的主要是民用瓷器。官用天青釉汝窑瓷器烧造区的发现与发掘,则主要在2000年以后。这其中2000-2002年连续进行了四次发掘,2011-2016年,为了配合汝窑现场展示馆的建设,又进行了连续的发掘,21世纪共完成了9次发掘,加上20世纪的5次发掘,清凉寺窑址前后进行了15次发掘。其中在2000-2002年的发掘中,清理了丰富的窑炉、作坊、陶瓮、过滤池、澄泥池、烧灰池、灰沟、水井、灰坑、瓷片堆积层遗迹现象,还出土了大量的汝窑瓷器,其中囊括了所有传世汝瓷器形和釉色,同时出土大量传世品未见器形,基本解决了汝窑产地、基本面貌与烧造工艺等问题[26]。2011-2016年的发掘发现了大量的素烧器(图五)与所谓的“类汝瓷”标本,这类产品继承了汝瓷的器类,有熏炉(图六)、瓶、盘、碗等,其中尤以盘类居多,且形体较大,在汝瓷器物群中尚不多见;瓷器釉色类汝瓷,也为天青、青绿、卵青和月白,但釉色光亮,玻璃质感强,但玉质感不及汝釉。胎质细腻坚实,多数胎色灰白,少有香灰胎,烧造时代晚于汝瓷,可能进入了金代[27]。

图四 宝丰清凉寺汝窑遗址

图五 汝窑炉

图六 汝窑素烧器
清凉寺窑址产品面貌相当复杂,时代上从北宋早期一直延续到元明时期。最早的产品以白瓷为主,其次是豆青和淡灰釉,少量的黑釉与酱釉瓷器。整个北宋时期白瓷比例逐渐降低,青瓷比例不断提高,纹饰增多。北宋晚期达到了鼎盛,并且出现天青色的汝窑制品。金元时期天青釉的汝窑器物不见,豆青釉瓷器质量逐渐下降,釉色变深泛黄。
清凉寺窑址是汝窑与临汝窑的重要窑址。
与汝窑相关的另外一项重要工作是汝州张公巷窑址的发掘。张公巷窑址发现20世纪晚期,2000-2004年先后进行了三次小规模的发掘,出土了一批全新的青釉瓷器,既不同于临汝窑的豆青釉,也有别于宝丰清凉寺汝窑的天青色,釉色可分为卵青、淡青、灰青和青绿等。常见的以薄胎薄釉为主, 釉面玻璃质感较强,有的器物表面满布细碎冰裂纹开片。胎质细腻坚实,胎色有粉白、灰白和少量浅灰色。器形有碗、盘、洗、瓶、壶、盏、盏托、熏炉、套盒和器盖等10余种。器底有支钉痕的呈非常规整的小米粒状,支钉分别为三、四、五、六枚。并出土大量素烧器残片。这批器物主要出土于多个器物埋藏坑中,与杭州老虎洞窑址有相似之处。同时还发现了窑具与制瓷作坊[28]。从出土器物质量、器形以及埋藏方式来看,该窑址产品应与宫廷用瓷有密切的关系,在窑业技术上,又与汝窑有紧密联系,大大丰富了汝窑研究的内容。这个窑址2017年以来又进行了再次发掘,相关的工作正在进行中。
四、主要收获
1.早期青瓷
通过对冀北豫南地区诸多早期青瓷窑址的发掘,明确了从安阳到临城一带的豫北冀南地区是早期青瓷的烧造中心。这里地理位置非常接近,同属于一个窑业中心区,除安阳的相州窑外,河北贾壁、临水、曹村诸窑址均位于漳河南北两岸,窑址的时代始于北朝时期,但早期产品主要是釉陶,生产瓷器则主要迟至隋代,到了初唐时期又逐渐成了邢台的中心,可以说这里是北方地区早期青瓷最为集中的区域。这一地区自东魏天平元年(534) 元善迁都邺城以后,政治中心转移,豫北冀南的漳河沿岸一带,成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到北齐时,这一带出现短暂的社会安定和经济繁荣的局面,陶瓷手工业才得以较快地发展。隋王朝统一中国,封建经济和文化发展,邢窑等窑口迅速兴起,开创了制瓷手工业的新纪元。因此这一带窑业的发展与繁荣应与这一时期以邺城为代表的北方政治中心的形成与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29]。
2.耀州窑考古
21世纪的耀州窑考古,主要在陈炉地区展开,目的是探索耀州衰落之后的去向问题。大约在金代,耀州窑的烧造中心逐渐转移到了立地坡与陈炉地区,窑业面貌亦由多烧造青瓷转向多种类型的瓷器,从而建立起耀州窑流变的基本完整的过程。陈炉地区的窑业一直延续到晚清民国甚至解放后,是晚清民国时期北方地区最大的瓷器烧造地,并留下了许多有关窑业生产与管理的碑文、档案与口耳瓷料,对于探索中国古代窑业的管理制度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3.汝窑
21世纪汝窑考古发掘与研究取得了重大的突破。20世纪清凉寺的考古主要集中在村南,其产品主要是民用瓷器,真正意义上汝窑天青釉瓷器烧造中心的确定,则是21世纪的事情,在村北所谓的第四发掘区不仅揭露了丰富的作坊遗迹,还出土了大量的汝窑标本,基本解决了汝窑的烧造问题。同时还发现了一批所谓的类汝瓷,加上张公巷窑址在本世纪的持续发掘,均为解决汝窑的去向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材料。
五、存在的问题
关于北方地区早期青瓷出现的问题,目前的诸多发掘报告与简报尤其是20世纪的调查简报基本都推到了北朝晚期甚至是北魏时期,但是从曹村的发掘情况来看,北朝时期的窑址产品绝大多数是低温的釉陶而非成熟的青瓷器。目前通过发掘,有明确地层关系的青瓷窑址,时代主要集中在隋代,整个北方地区,可能仅山东的寨里窑址时代可以早到北朝时期。因此北方地区制瓷业的出现,主要始于隋代。但北朝晚期与隋代器物的区别本身比较模糊,不可能一刀断成明确的前后两期;另外,隋代的窑业不仅完全成熟,而且呈多点状开花,处于快速的上升期,不排除之前有少量的试烧。从这两方面看,北方地区的制瓷业,从北朝晚期开始,也是完全可能的,但呈规模的出现,则要到隋代了。
[1]冯先铭:《河北磁县贾壁村隋青瓷窑址初探》,《考古》1959年第10期。
[2]河北临城邢瓷研制小组:《唐代邢窑遗址调查报告》,《文物》1981年第9期;内丘县文物保管所:《河北省内丘县邢窑调查简报》,《文物》1987年第9期。
[3]河北省邢台市文物管理处:《邢台隋代邢窑》,科学出版社,2006年。
[4]张松林:《荣阳翟沟瓷窑遗址调查简报》,《中原文物》1984年第4期。
[5]山东淄博陶瓷史编写组、山东省博物馆:《山东淄博寨里北朝青瓷窑址调查纪要》,《中国古代窑址调查发掘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
[6]宋百川等:《山东曲阜、泗水隋唐瓷窑址调查》,《考古》1985年第l期。
[7]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山东泰安县中淳于古代瓷窑址调查》,《考古》1986年第1期。
[8]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等:《山东枣庄中陈郝瓷窑址》,《考古学报》1989年第3期。
[9]冯沂:《山东临沂朱陈古瓷窑址调查》,《考古》1995年第8期。
[10]徐州博物馆:《江苏徐州市户部山青瓷窑址调查简报》,《华夏考古》2003年第3期。
[11]宋百川等:《曲阜宋家村古代瓷器窑址的初步调查》,《景德镇陶瓷》总26期(《中国古陶瓷研究》专辑第2辑,1984年)。
[12]河南省博物馆等:《河南安阳隋代瓷窑址的试掘》,《文物》1977年第2期;孔德铭:《安阳相州窑及相关问题研究》,《殷都学刊》2014年第1期。
[13]河南省博物馆等:《河南安阳隋代瓷窑址的试掘》,《文物》1977年第2期;孔德铭:《安阳相州窑及相关问题研究》,《殷都学刊》2014年第1期。
[14]王建保等:《河北临漳县曹村窑址考察报告》,《华夏考古》2014年第1期。
[15]沈丽华等:《河北临漳邺城遗址曹村青釉器窑址》,见国家文物局编:《2016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17年。
[16]河北省邢台市文物管理处:《邢台隋代邢窑》,科学出版社,2006年。
[17]内丘县文物保管所:《河北省内丘县邢窑调查简报》,《文物》1987年第9期。
[18]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河南巩义市白河窑遗址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11年第1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日本奈良文化财研究所:《巩义白河窑考古新发现》,大象出版社,2009年。
[19]禚振西:《中国耀州窑·前言》,见北京艺术博物馆编:《中国耀州窑》,中国华侨出版社,2014年。
[20]耀州窑博物馆等编著:《立地坡·上店耀州窑址·前言》,三秦出版社,2004年。
[21]耀州窑博物馆等编著:《立地坡·上店耀州窑址》,三秦出版社,2004年。
[22]耀州窑博物馆:《陈炉耀州瓷精萃》,文物出版社,2007年。
[23]冯先铭:《河南省临汝县宋代汝窑址调查》,《文物》1964年第8期。
[24]陈东强:《临汝青瓷研究》,郑州大学2010年硕士论文。
[25]汪庆正等:《汝窑的发现》,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7年。
[26]赵宏:《汝窑考古三十年》,《寻根》2017年第6期。
[27]赵宏:《河南宝丰清凉寺汝窑发掘再获重要发现》,《中国文物报》2014年11月25日第8版。
[28]孙新民:《汝州张公巷窑的发现与认识》,《文物》2006年第7期。
[29]孔德铭:《安阳相州窑及相关问题研究》,《殷都学刊》201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