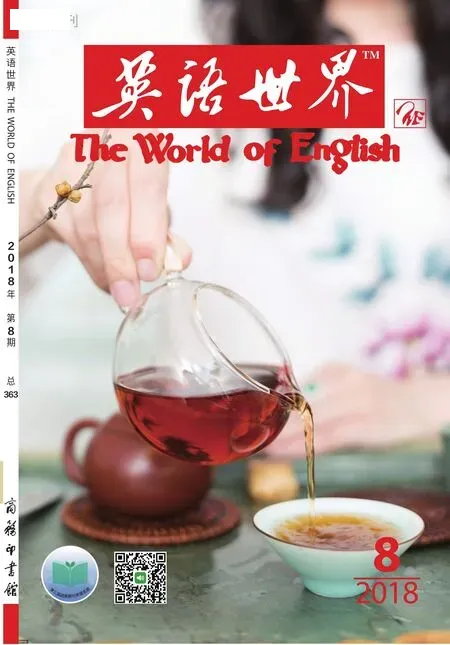缘,原来是圆的
文/金圣华
中国人相信缘,人有人缘,书有书缘,地也有地缘。缘到底是怎样的?这事玄妙而难解,只可意会,不能言传。但是最近,因为种种机遇,使我深信,缘,原来是圆的——起于一线相牵,飘飘渺渺,兜兜转转,似有若无,欲断还连,纵使相隔千山万水,历经长年累月,终会在冥冥中,穿过云,穿过雾,又回到源头,画出一个满满的圆!
早在几个月前,上海浦东傅雷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王树华先生就盛情来信,说是“傅雷诞辰110周年纪念大会”即将来临,邀约我赴沪出席。王先生是个有魄力的热心人,自从十几年前接下推广傅雷文化的重任后,就不断的主持各种纪念活动,多年来举办过傅雷著译研讨会,傅雷精神座谈会,傅雷手稿墨迹展,傅雷著作首发式,傅雷夫妇陵园安葬仪式等大型项目,这次推陈出新,又有什么特别的构想呢?他说,主要的是举办《傅雷著译全书》首发式,另外还邀请了一些法国专家来华共襄盛举,并以傅雷与巴尔扎克之间的渊源作为主题。
如所周知,傅雷毕生完成了五百余言共三十多部译作,其中巴尔扎克的作品就占了十五部之多,除了《猫儿打球号》在“文革”中遗失之外,其他十四部作品,如《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贝姨》《幻灭》等,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名著,在那相对封闭的年代,曾经成为一代年轻读者视为瑰宝的精神食粮。有一出名为《巴尔扎克与小裁缝》的电影,银幕上述说的就是“文革”时上山下乡的年轻人争相捧读傅译巴尔扎克的情景。
以傅雷与巴尔扎克为主题,这正是我当年研究的专项,因此,即使主办方在临近活动时才突然提出要我在会上发言的请求,尽管时间仓促、猝不及防,也就不得不欣然从命了。
当年傅雷出生的小镇周浦如今划为了大上海的一部分,在那里一家新开不久的旅舍中,邂逅了来自法国的巴尔扎克故居博物馆馆长伊夫·加尼奥(Yves Gagneux)先生,素未谋面,却感到一种暖暖的亲切。那似曾相识的感觉来自对方的所连所系,遥远的所在,悠久的岁月,瞬息缩短距离凝聚时间,鲜明真实的呈现在眼前。“巴尔扎克馆可是别来无恙?”我问道,虽询旧地,似念故人,那地方,确实牵起许多难忘的追忆,令人低回不已。
当年,负笈巴黎,为撰写有关傅雷与巴尔扎克的论文,最常到访之处,除了索邦大学,就是巴尔扎克故居,那里是作家自1840至1847年为了躲避债主而藏身匿居的所在,也是作家潜心创作撰写煌煌巨著《人间喜剧》的地方。从巴黎南郊的大学城出发,要换几次车,才来到位于城西十六区的小楼。那一带,人车稀疏;那一处,清静宁谧,每一次去,似乎都不见其他的访客,于是两层的故居就变成独自流连徜徉的场所了。肃穆沉默中,心静下来,坐在四壁皆书的台前,进入作家百年前创作,译家百年后翻译,后学者专心致志,研习传承的氛围。多少个漫漫长日,就如此消磨在纸堆书页间。偶尔,瞥见窗外风光明媚,自觉有负良辰,哪知道傅雷1954年在翻译巴尔扎克的《于絮尔·弥罗埃》时早有此叹:“近一个月天气奇好,看看窗外真是诱惑得很,恨不得出门一次,但因工作进度太慢,只得硬压下去。”(《傅雷家书》,1954年11月1日)原来自古伏案皆寂寞,信然!
那时候,巴尔扎克故居中,陈列了作家各种著作不同文字的翻译本,独缺中文,于是,就把手边傅雷翻译的《高老头》捐赠馆藏,当时是以谦逊虔敬之心,促成译者和作家在馆中首次百年相聚。谁想到几十年后的今天,巴尔扎克博物馆的馆长竟然越洋而来,不但如此,更亲自携带傅雷于1963年申请成为巴尔扎克研究会会员的信件和资料,以回馈译家的故乡!
“巴尔扎克的咖啡壶还在吧?他的镶宝石手杖呢?”作家当年为写作而殚精竭虑时,不得不依赖咖啡提神;作家完成杰构后行走沙龙时,又免不了以宝石手杖招摇人前,这两样镇馆之宝,如今可都安好?“都还在!”馆长笑着说,“现在的发展重点是,要访客垂注的不仅是巴尔扎克其人,还有其书,作家的作品,比其生活琐事更加重要!”的确,如今周浦要成立傅雷故居,呈现的该是傅雷的著作与译品、精神和气节,而不是供游客走马看花的一个旅游景点。“下次到巴黎,别忘了来巴尔扎克故居,我给你一个私人的特别导赏!”这是馆长的承诺。
在第二天的会议前,遇见了法国勒阿弗尔诺曼底大学现代语言教授韦罗妮可·裴(Veronique Bui)。听说她是研究巴尔扎克的专家,于是就趋前交流并向她请教。闲谈中,对方忽然非常认真的提起,她的研究是受到当年某某人论文的启发,说出名字时,让我先是愣住,继而迟疑,再而醒悟,“您说的那人好像是我呀!”Bui教授一听,非常兴奋,颇有他乡遇故知的感觉,虽然我俩也是素昧平生。为了证明其事,她急忙打开手机,翻到其中一处递给我看,赫然见到那是我当年在索邦大学所撰博士论文的书目。由于那时尚无计算机,只有打字,那一条条英法文书目中列出的中文译名,如《高老头》《邦斯舅舅》等,都是手写的。看到自己的笔迹,竟然于几十年后出现在一位陌生法国学者的手机中,那种惊喜与震撼,的确难以言喻!
缘,原来真的是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