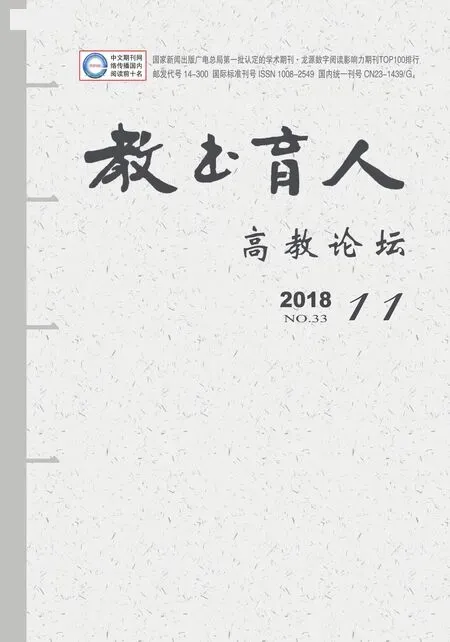高校教师参与课程建设积极性探析*
张怀英 (湖北理工学院)
尽管政府通过行政手段持续推进精品课程建设,效果仍不明显。朱清时认为我国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是课程体系不行,教材内容陈旧。“组织人员到全世界各地去调研,回来编写新大纲和新教材……开始进行得还好,后来却推行不下去了……教师缺乏内在的积极性,诸事很快就流于形式”。本文剖析了教师参加课程建设积极性不高的原因,具体如下。
一 科研强校目标下的功利导向
我国高校普遍进行目标考核制,以此确定中层干部的升迁和教学院的获奖排名。为了强调效率和政绩,考核指标越来越量化和具体,重点不外乎是科研项目、论文、获奖等。功利化的强校指导渗透到对教师发展影响最大的二类评价中,分别是岗位定级和职称评定。
根据《湖北省教育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的三个指导意见》,“要严格控制专业技术岗位结构比例,严格控制高级专业技术岗位的总量”。教师岗位级别决定工资待遇,由于结构比例固定,岗位晋级“先到先得,后到没得”。规定初衷是为了规范岗位设置,提高教师绩效,却引发了“职称大战”的“前战”。以湖北某本科高校为例,岗位竞级的硬性指标主要是参加省级项目、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或专著的数量、师生省级获奖、国家发明专利等。与课程建设相关的指标有校级教研项目、产学研项目、“本科教学工程”项目、精品课程建设,以及校级重点学科或重点实验室、讲课比赛获奖等。上述指标均强调显性量化的成绩,除了精品课程建设外,其他指标与教师提高教学积极性的相关性不大。各高校在评审中分数水涨船高,竞争加剧了上述量化指标的影响力度。相比而言,与师生关系最密切的课堂日常教学,由于指标隐性不好量化,体现为“教学工作量不少于64-208学时”“教学经验丰富、教学成果优秀”等软指标,无法在职称大战中加分。职称评定就这样演变成了论文、项目和获奖大战。
考核指标成为悬在教师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浙江工商大学教学院副院长徐斌离职,坦言“近年盛行的数字化考评、高校排名,让各级像疯了一样抓项目、课题、报奖、报点、基地之类,……穷于应付上级下达的各项‘创新强校’指标,没有精力认真考虑教学和科研事宜”。
二 学术权力被剥夺下的责任缺失
高校作为一个学术系统,理想状态是“有组织的无政府状态”。伯顿·克拉克认为,“和其他系统相比,高等教育系统更容易因‘过于集权’而运转失灵。”纵观西方多国的高等教育组织,不管是欧洲大陆型模式中“曾经作为国家机构一员”的柏林大学,还是国家协调机制最广和严密的瑞典和法国,底层专业组织的权力都是强有力的存在,与国家政治、行政权力和市场调节等势力抗衡。学术权力结构的基本特征是底部沉重,影响弥散和决策渐进。专业和学者的专门知识是一种至关重要的和独特的权力形式,它授予某些人以某种方式支配他人的权力。如果没有这种权力,高等教育系统难以有效地运转。
反观我国高校的权力运行,行政权力泛化和集中,学术权力弱化。高校在发展中,没有形成西方大学的自治专统,专业组织属于“弱势群体”,“是在没有自己‘象牙塔’的语境下谈论‘走出象牙塔’的”。高校权力分配体现为校级集权,中下层缺少自主权。校党委对大学实行统一领导,校学术行政机构实行集中管理,承担繁重的学术管理职责。校党政组织体系发达,职能部门众多。中层教学院主要执行上决策,沟通学校层次与教师之间的联系。政府规定的准则变得死板化一,严重地限制了较低层次进行创新和调整的条件。行政机构过度管理,追求秩序、等级森严,违背了学术组织特性。学术委员会等学术机构常由党政领导担任,体现了较强的行政干预痕迹。调查显示,有62.3%的人认为本校的学术委员会成员是由行政人员确定的,其中51.3%的学术委员会成员兼有行政职务。
教研室或系属于底层组织,是按专业或课程设置的教学组织,实际上是大学内部学术、行政管理的基层机构,承担了大量学术以及人事等管理任务,但并不拥有相应的决策能力,由此淡化了需要承担的责任。任何大学的改革如果不能调动基层人员的积极性,只能如同“刮风”,流于形式。
三 市场缺位下的动力不足
我国高校的办学资源来自政府投入和学生学费,办学资源单一,政府投入有限。社会力量对高校办学的支持力度很小。一方面我国缺乏社会力量支持高校办学的传统,另一方面高校长期依赖政府,对市场需求反应不够敏捷,创新不够强烈,缺乏能力引领企业的发展,也很少根据市场变化调整高校战略规划、项目评估等,有人戏称“大学是市场经济的最后一块堡垒”。以湖北某应用型高校为例,一个重要指标是双师型教师的引进。拥有“注册会计师”“注册建筑师”等高级职业注册证书的人才却因学历问题很难引进,或是引进了也很难安排到教师岗。即使学校有意愿引进,也受到省厅高校人才引进政策的管制。
伯顿·克拉克提出,矩阵结构代替传统系科组织,能较好适应学术组织的特点。他强调“三重矩阵”,即教师不但加入了所在系科,而且又为某个社会部门服务,还是某项研究的参与者。“三重矩阵”使得教师在专业领域内能更好地与其他团队、学科,或是社会服务构成交叉关联。通常高校与政府、市场形成稳固的三角形,但是我国高校与市场的关系是“先天不足,后天跛腿”。高校缺乏市场力量的激励与约束,在发展中显得“不食人间烟火”。社会资源也很少投入高校,高校变得更加依赖政府,侧重于管理内部现有资源,倾向于形成封闭的管理结构。高校与企业脱轨,双师型教师难以引进,教师从学校到学校,害怕或缺乏动力走进市场,可能在学术理论领域走在前沿,却无法运用成果去指导企业的发展。尤其是应用型高校工科专业,课程内容应当经过市场检验。许多工科教师不知道本专业的最新技术,教学内容滞后和“无用”。
四 教师淘汰制中的约束不足
我国法律对教师淘汰制的规定不健全,使得实施困难重重。《高等教育法》规定:“高等学校实行教师聘任制。”《教师法》规定:“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应当逐步实行教师聘任制。”教师“故意不完成教育教学任务”“体罚学生,经教育不改”“品行不良、侮辱学生,影响恶劣的”将受到行政处分或开除,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法律规定了教师淘汰制的底线,但是如果教师无品行问题,又完成了教学任务,不管课程如何陈旧,教学质量如何差劲,高校都无淘汰依据。
组织文化观念加剧了教师淘汰的困难。单位制度是当代中国的特色,是集体主义文化的组织表现,它与北美大学的“雇员”观念截然不同。据调查,中国大学教师绝大多数不认为自己是学校的“雇员”,而认为自己是学校的“主人”。因此高校应当接受分配来的教职工,不能以“不称职”为由开除教职工。
按合同解聘是当前教师淘汰的主要方式,存在的问题有:解聘理由的模糊性、转岗和低聘的随意性、聘任合同的形式化,三者均体现了管理的不规范。另外两种分别是“学术标准淘汰”和“学科末位淘汰”,后两种从教师科研业绩着手,教师在职务任期内不能晋升则“非升即转”或“非升即走”。2003年北京大学以“学术标准淘汰”推行的教师聘任制度改革,引起了社会各界广泛争议,褒贬不一。有学者认为北大提高了教师淘汰制的标准,却没有法律依据。此外,高校还出现优秀教师流出,低素质教师则无法淘汰的“逆淘汰”现象。
强校目标导向下的功利化。当前政府普遍以“项目”“工程”等形式管理高校,以此来决定对高校的资源投入,但是论文、项目和获奖并不等于科研,只是科研的几个量化代表参数。其次为了多、快、好地出成果、评职称,教师难以静下心来把科研成果转化为课堂教学内容。
学术权力被剥夺下的责任缺失。在我国行政与政治权力的侵袭下,底层组织剩余的生存空间被不断压缩,权力被剥夺的同时责任也被屏蔽了。如果个人拥有的只是被动执行的义务,那他也不愿意积极主动地承担责任。
市场缺位下的教师课程建设动力不足。课程建设需要与服务社会发展有机结合起来。美国高校倡导在底部学术组织厚重的基础上侧重于科研或社会服务职能,各有特色和生存空间。我国高校科研和市场的两翼相对折损,教师的“三重矩阵”身份只剩下了“教书匠”。教师既缺乏能力,也缺乏动力去进行课程建设。守着陈旧的课本内容,“重复着昨天的故事”,成为许多大学教师的课堂生态图。
教师淘汰制不规范下的约束不足。现行法律规定不完善,一些高校推进的“学术标准淘汰”和“学科末位淘汰”主要以科研业绩为中心,并不必然会提高教师参加课程建设的积极性,相反过度强调科研业绩,可能会损害其积极性。课程建设与其他显性指标相比,显得很不过硬,也不太重要。制度的疲软挫伤了教师的积极性,负责任地对学生讲授课程似乎成为教师对自己的一种道德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