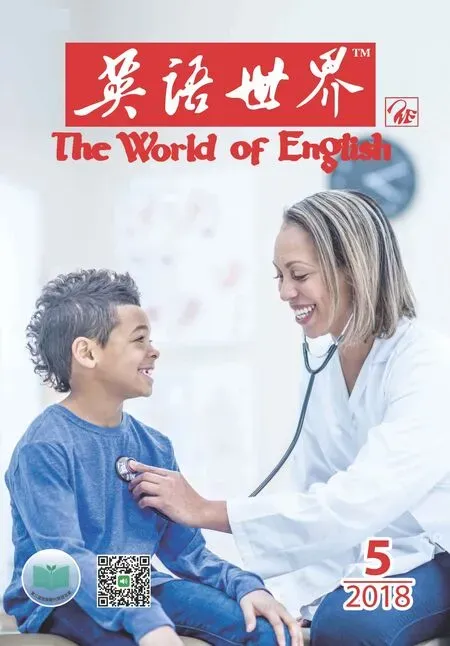回忆袁士槟教授
文/孟宪波
袁士槟1袁士槟(1932—2012),上海人,原籍浙江宁波,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现为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专业第一届本科班和印度阿拉哈巴德大学(Allahabad University)。在英语和印地语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是外交部屈指可数的双外语高翻之一,因主持中央电视台英语教学节目《跟我学》(Follow Me)和英译《孙子兵法》而名扬天下。主要作品有:《联合国机制与改革》(主编);《新时代汉英大词典》(英语顾问,商务印书馆);《孙子兵法概论》(汉译英);《世界文明史》《白求恩》《金山华人》《企业应审时应变》《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法规汇编》等(英译汉合译或审校)。教授曾任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现更名为“中国翻译协会”)副秘书长、中国联合国协会理事、原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新闻发言人、外交学院联合国研究中心首任主任和英语系主任等职。20世纪70年代曾数度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和日内瓦联合国分部担任同声传译;80年代初,应中央电视台之邀,担任英语教学节目《跟我学》 (Follow Me)的主播之一;90年代曾兼任美国长岛大学(Long Island University)国际政治系客座教授,主讲“联合国”“中国外交”和“现代中国”等课程。
“1950年,当抗美援朝运动席卷祖国大地时,正在念高三的我居然瞒着父母,放弃了报考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志愿,毅然报名参了军。曾在第三野战军服役,最后被分配到当时的北京外国语学院学英语。1953年,曾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解释代表团的英语翻译入朝工作了五个多月。1954年,还没来得及做毕业鉴定就被调入外交部。接着,就被借到当时的经贸部,赴当时尚未建交的叙利亚,参加大马士革世博会,在那儿工作了近半年。回部后,连板凳还没坐热,1955年5月又被外交部选派至印度留学。”袁回忆说。
这是我国首次向社会主义阵营以外的国家派遣留学生。在印度留学时,他所学专业为印地语和印度学(包括历史、政情和文化等课程),成绩出众,获硕士学位。
1959年年初,他被留在中国驻印度使馆工作。1960年,周总理访问印度时,由袁担任口译译员,主要用印地语,同时也使用英语,圆满完成了工作任务。1964年奉调回国时,他已在印度学习和工作近九年之久。回国后,他被分配到第一亚洲司印度处。此后,还曾多次为刘少奇、朱德、宋庆龄、陈毅、贺龙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外交部主管亚洲事务的韩念龙副部长充当翻译。
1980年,享有“中国外交官摇篮”美誉的外交学院复校,盛情邀请袁士槟到该校任教。他开始了教书育人的职业生涯。他曾先后担任英语系主任、教研处副处长等职,后被评为英语二级教授和研究生导师。他在外交学院首创“多边外交和联合国”课程,并成为该校引进“模拟联合国”活动的第一人。
20世纪80年代中期,袁老师被派往位于纽约的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任参赞和安理会候补委员兼英语新闻发言人。
若干年前,香港报纸上曾刊登过一则消息:内地袁士槟先生翻译的《孙子兵法概论》在美国再版,西点军校的师生人手一册。该书于1987年在美国首次出版后,曾多次再版,在国际上流传甚广,并产生了一定影响。1987年,纽约斯特林出版社出版了袁士槟翻译的《孙子兵法概论》英译本,该译本被收录进《大师经典文库》,该文库为广大学者提供高质量的阅读文本,也为各类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提供必备的学习资料。
凡是在20世纪80年代看过央视播放的《跟我学》(Follow Me)教学节目的人,大概都不会对袁老师感到陌生,该教学节目正是由北外胡文仲教授、外交学院袁士槟副教授和英国专家Katherine Summer共同担任主讲。
当被问及自己对人生的感悟时,袁老师回答道:“自己工作了50年,一半在外交部,一半在外交学院。虽未对外交事业做出多少突出贡献,但使我感到欣慰的是,我的学生遍布世界各地。我不论是在美国当客座教授,还是在联合国总部工作,抑或去欧洲旅行、参加国际问题研讨会,走在大街上,常会听到‘袁老师,您好’的招呼声,其中多数素不相识,但对方却说‘我认识您——英语启蒙老师’。”因此,如果说袁老师桃李满天下,一点都不为过。姑且不算那些通过电视节目和录像带学习英语的人,单说他直接教过的外交学院的各届毕业生,就难以计数。
20多年前,笔者在外交学院读书时,便是袁老师班上的学生,当年老师认真讲授“多边外交和联合国”一课的情形仍历历在目。2000年,笔者从美国回来后,便与袁老师夫妇结下了深厚情谊,从此来往不断。由于恩师的力荐,笔者得以在母校培训中心任教数年,讲授自己所喜欢的翻译课。
袁士槟教授因罹患前列腺癌,于2012年1月2日22时48分逝世,享年80岁。2012年1月8日9时,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304医院举行。参加告别仪式的有近百位袁老师的亲友以及生前故旧、同事和学生等。
笔者默默地立在恩师的遗体旁,跟他做最后的告别。泪眼朦胧中,师徒如父子的一幕幕情形再次浮现在眼前——
有一次,笔者问袁老师:“您当年是外交部最好的印地语翻译之一吧?”
“没有‘之一’,我是最好的。”袁老师正色纠正道。
袁老师指着客厅里一张红木餐桌告诉笔者:“这是我父亲留给我的传家宝。”
“现在可是金不换的值钱宝贝!”笔者赞叹不已。
就这样,一对师徒,一老一少,经常在一起笑得没心没肺,开心无比。
2011年深秋的一天,师母给笔者打电话,说老师想见我。次日一早,我便陪同师母赶往医院。当时,袁老师正靠在床头,整个人枯瘦如柴,手腕上的表链显得宽松无比。笔者给恩师带来各种各样的蜜饯,问:“有山东产的,也有上海产的,您想先尝哪一个?”老师答:“上海产的吧。”
笔者到现在都后悔,埋怨自己当时没有送给恩师一个装满鲜果的果篮。
袁老师逝世后,葬于故乡上海南汇区的一处陵园里。师母汤影梅是风景园林规划设计师,她亲手为丈夫设计了简洁自然、朴素小巧的圆形陵墓,并撰写了墓志铭——你是国家优秀的外交官;教育界的良师益友;妻子心目中的好丈夫;孩子们所崇拜的慈父。他们夫妻恩爱一生,共同走过了无数风风雨雨。
笔者在家里最显眼的地方摆放着两帧照片,一帧是自己父亲的照片,还有一帧就是恩师袁士槟和吴鹤年二位教授的合影。
袁老师一生淡泊名利,为人谦和,心地善良,虚怀若谷,是笔者最为钦佩的老师(没有“之一”)。
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斯人已逝,懿范长存!
愿恩师在天之灵安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