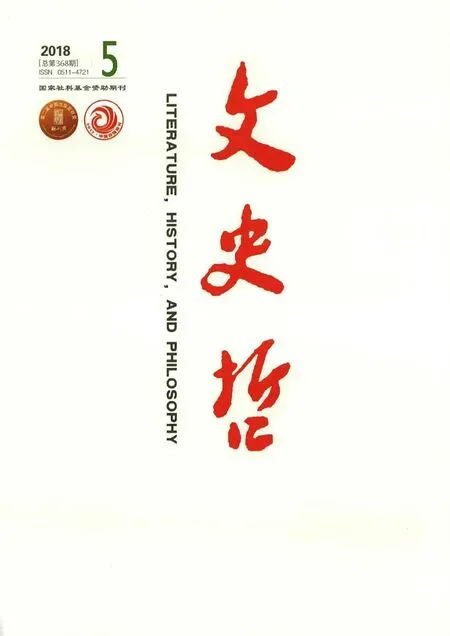感通本体引论
——兼与李泽厚、陈来等先生商榷
蔡祥元

下面我们将以考察实体论与情感论之间的张力为契机,重溯宋明道学开端处的文本,表明其中蕴含着一个以感通为本体的思想维度。此维度可以吸收情感论不离仁者的思想初衷,以仁者为仁体的“身体”保证,避免仁体成为抽象的形而上实体。与此同时,通过追溯仁者之仁的发动端倪,从经验情感的根子处剥离出一个不同于经验情感的先行开道的可能性,以此表明它为何能超出自身而达乎他人、达乎天地万物,从而又确保了仁道的形而上之维。
一、儒家思想哲理的根本问题
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概念,在不同的语境中有不同含义,大致包括如下三个层面:情感经验层面的仁爱,伦理层面的仁性与形而上层面的仁道。
仁爱指的是一种仁者爱人的具体情感。“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这种情感经验层面的爱并不直接体现儒家思想的特征。爱的情感,每个人都可以有所体验,每个民族、每种文化都会有相关的观察与描述。仁性则是在观察、体验到仁爱的基础上,对仁爱情感之何所来的一个推定。我们为什么会具有仁爱的情感?它肯定与我们天性里的某些东西有关。把这种天性称为仁性或仁爱之性,这也没有什么问题。没有它,仁爱的感情就没有着落。但是,这个设定本身也不必是儒家的。儒家思想哲理的独特性在于把这个仁爱天性作为人之为人的根本,也即作为人的本性。至此,儒家的特点才显示出来。
但是,问题也就来了。人有七情六欲,它们在人的天性里皆有其根据,为什么偏偏把与爱相关的天性作为人的本性呢?当孟子把恻隐之心作为人性之本的时候,告子就提出了反对意见。但是告子没有意识到,孟子辩护的关键在于他区分了两种不同的性:一种是自然的天性,这是人与一般生物尤其是动物所共有的自然本性;另一种是人与动物相区别的性,那才是人性。孟子说的性善是着眼于后者而言的。“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孟子·离娄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孟子·公孙丑上》)孟子所观察到的那几个“善端”,是动物所不具有的,动物不会恻隐、不会羞恶。告子的辩驳则是着眼于第一种性展开的,在这个意义上就没有切中孟子思想的要害,也就不构成对它的反驳。
不过从证明的角度看,孟子的理由还不能说是充分的。他只是表明了恻隐之心是源发的,是动物所没有的,但是要论证仁性就是为人之本,还需要进一步表明,除了仁性以外,人与动物没有其他的本质性区别。这方面讨论,告子没有继续,孟子也没有展开。我们知道,西方文明传统从苏格拉底甚至可以说从巴门尼德开始,就把一种与感觉相对的理性(或理智)作为人的本质特性。与仁性不同,理性着眼点是对真理的认知与把握。至于仁性根本还是理性根本,这是可以争议的。不过,既然它们都关乎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它们之间也就没有截然的对错之分,只是一个方向性的选择。在文明发端之初,选择哪个方向,会影响后面整个文明形态的开展。关于它们各自的是非得失,这里就不展开了。现实就是,孔子、孟子为华夏文明作了一个选择,因此影响并塑造了华夏文明的基本形态。
选择仁性作为人的本性,也还只是一个开端。儒家之为儒家,单靠这个选择,它的独特性并不能得到完全彰显。仁之为仁,还在于它的第三个维度,也即作为形而上层面的贯通物我内外的天人之道。仁道说的是这一形而上层面的仁。在儒家传统中,对于形而上层面的仁有不同的命名,比如仁体、仁理、仁道乃至仁心等,都是着眼于这一层面而言的。就像牟宗三指出的,这几个词在宋儒那里是可以通用的*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79页。。虽然仁道思想已经隐含在孔孟的文本之中,但是,到明道这里才以“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二程遗书·二先生语二上》)的形式得到明确的表述。明道的论断,与孟子性善之论有一个关键不同。孟子的论述更多还是从伦理层面考量人之为人,“仁也者,人也”(《孟子·尽心下》),明道则将这一考量提升到形而上的高度。在他这里,仁不仅仅要使人成为人,还要与天地万物的存在相互贯通。由此,儒家的思想哲理被注入了一个新的视角,也即:从孔孟的人伦之道走向了贯通物我内外的天人之道。
由此而来的问题就是,这种源自人性的情感如何能够超出人的主观性限制,达到与天地万物共为一体的状态?这个道理就不像前两者那么自明了——不仅不自明,甚至有违常理。这个道理如果讲不明,那么儒家哲理的独特性也就出不来。当代儒学界的实体论与情感论都是针对此问题展开的。
二、仁学本体论之得失
陈来的《仁学本体论》是对儒家形上本体的最新发明。正如他在该书前言中指出的,此书不只是单纯介绍仁学思想,而且是重构一个新的仁学本体论*陈来:《仁学本体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1页。后引此书皆随文夹注书名及页码。。该书对仁学本体的重构,也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可,被认为是原创的、精细的,能够代表当代儒学研究的最新发展*参考杨立华、赵金刚整理:《中国哲学再建构的当代路径——由〈仁学本体论〉展开的对话》,《哲学动态》2015年第5期。。该书对其思想切入点的展示主要集中在前言与第一章“明体”中,其核心内容可以概述为仁体。虽然仁体的观念在宋明时期已经提出过,但是陈来指出,在宋儒那里,仁体主要被理解为心性之体,而在他的论著中,仁体主要作为本体论、宇宙论的观念来使用(《仁学本体论》,第29页)。

进一步阅读论述“仁体”的相关章节可以发现,此有机实体的思想来源主要是斯宾诺莎的实体论与怀特海的过程哲学。一方面,该书把实体解读为万物存在及运动变化的根本原因,比如,“宇宙万象及其运动的根源和依据”(《仁学本体论》,第17也)、“活动流通的内在动因,是宇宙活动力的动源,……动之‘机’就是动力因”(《仁学本体论》,第42页)、“天地之心是指天地运动的内在动力因,是宇宙生生不息的内在根据和根源,这与作为法则、规律的理的含义是不同的”(《仁学本体论》,第43页)等等。这一从“原因”角度理解本体的思路明显带有斯宾诺莎实体观的影子。该书“绪言”中也明确指出,斯宾诺莎的实体论与中国哲学的实体观是相当接近的(《仁学本体论》,第15页)。
另一方面,把仁体作为万物有机关联的思想则借鉴了怀特海过程哲学的视角,比如说仁体“乃是此物生生不已的生机,由此仁而有此物之生长不已,由此可知仁即是万物充满生命活力、生生不已的生机”(《仁学本体论》,第43页),是“一个整体的存在,动态的存在,过程的全体”(《仁学本体论》,第13页)。该书也提及怀特海的观点作为自己思想的佐证,“还是怀特海说的对,‘哲学的关键就在于要在个体性和存在的相关性之间保持平衡’”(《仁学本体论》,第71页)。对比作者对仁体的设定与怀特海形而上学的原则,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它们的对应关系:
吾人仁体说之本体的设定,乃在设立世界存在、关联、生生与运动的根源,此根源不是宇宙发生义,故本体非第一推动者。而是宇宙时时而有、永不枯竭的内在根源。(《仁学本体论》,第12页)
怀特海重建形而上学必须依赖于几个主要原则,动态原则、过程原则、关联原则和生成原则。(《仁学本体论》,第72页)
因此,该书的仁体观可以看作是斯宾诺莎的原因观与怀特海的过程观的结合,也即:把有机关联的整体作为万物的根本原因,从而使仁体具有了本体论宇宙论的意谓。借助西方哲学的视野,重构中国哲学基本论题,这是没有问题的。当年宋明理学的整个思想建构就是通过与佛老的对话展开的,在拒斥佛老的同时,也暗中吸收了不少它们的思想。问题在于,这个视野是否足够契合儒家哲理的思想内涵。
在笔者看来,无论是斯宾诺莎的实体或原因概念,还是怀特海的有机或过程思想,都难以完成这个使命。以此来建构的仁体说或有机实体论,将面临如下问题与挑战。
首先,将这两个概念整合在一起是有问题的。作者没有明确意识到,斯宾诺莎的原因观与怀特海的过程哲学是两个不同层面的东西,它们之间充满难以调和的张力。怀特海建构过程哲学,其目标就是要消除传统形而上学中的本源、原因等实体概念,欲借过程自身来说明实在。这是一种主张过程即实在的思想立场。在怀特海看来,正因为万物本身就是有机关联的整体,就是变化不已的实在自身,所以,根本不需要在此实在背后再设立一个“终极原因”来作为“推动者”。事实上,他对斯宾诺莎的实体观提出过明确的批评:
有机哲学与斯宾诺莎的思想体系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与之不同的是,有机哲学抛弃了思想的主—谓形式,因为它关注这种形式直接体现事实最根本特征的前提。结果就避免了“实体—属性”概念;并且以动态过程的描述代替了形态学的描述。……一方面,使过程成为终极的东西;而另一方面则使事实成为终极的东西。*[英]怀特海:《过程与实在》,李步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5页。
怀特海的过程哲学与斯宾诺莎的实体论之间的矛盾,在陈来的论述中也有体现。比如,他一方面指出仁体是宇宙的动力因,同时又指出它不是亚里士多德实体论中的第一推动者(《仁学本体论》,第72页)。我们知道,动力因概念源自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说法,事物的运动变化总有一个导致其运动变化的推动者,这个推动者就是动力因。既然运动者必有推动的原因,如此推下去,必然推出存在一种最终的、最初的动力因,它是不动的。因为如果它也是运动的话,那么,还需要一个新的动力因。这个不动的推动者,就是第一推动者*[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1071b5,苗力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49页。。由此可见,第一推动者与动力因这两个概念是互相关联的。如果把仁体解读为动力因,那么作为仁之本根的道体,也即太极,作为不动的推动者(“但太极实体自身则不动,无一息不停止”*陈来:《仁学本体论》,第20页。),就是第一推动者——除非首先表明,文中的动力因不是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动力因。这是过程哲学与传统实体哲学之间的矛盾。根据传统实体论,应该存在并设定一个根本原因。根据过程哲学,这样一个设定是多余的。所以,陈来一方面循实体论思想指出仁体乃是根本的动力因之后,另一方面又按照过程哲学的思路,否定了第一原因的存在。

第三,仁体观念并不能克服朱子理学之蔽。陈来明确指出,朱子的理学思想是其仁体观念的思想来源。“无论如何,朱子的仁体论和仁气论,特别是他重视流行统体的思想,他的以仁为实体、总体的思想,为仁体论建构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和方向。”(《仁学本体论》,第46页)与此同时,陈来也对朱子理学提出了明确的批评。在他看来,朱子将伦理法则提到本体的高度,夸大了规律的独立性与普遍性,从而导致了理在气先、理在物先的错误观点*陈来:《朱子哲学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50页。。《仁学本体论》构思仁体观念的思想动机,就是要把“流行统体”的“气”作为本体,以克服朱子理学中“理在气先”的思想困境。如果说朱子理学的基本思路是把人伦法则先天化,使它成为物我所共有的“天理”的话,那么《仁学本体论》的仁体则是将这一基于人伦的“先天法则”替换成“先天实在”(“有机关联的整体”)。相比“有机关联”这种“先天实在”,在我看来,先天法则更接近道。毕竟,道乃万物由之以成的东西。如果朱子的天理都因此而可能有沦为抽象、空洞道理的危险,那么,这种先天的有机实在如何能避免陷入同样抽象的形而上思辨呢?
因此,虽然该书的仁体观切中了儒家思想哲理的关键问题,并意欲打开一个理解儒学道统的新视野,但是,要将此视野贯通下去而完成对仁学本体的重构,在我看来,还有不少问题需要得到进一步回答。
三、情感本体论之得失
与陈来所主张的实体论建构不同,不少学者试图从情感角度重建仁学的形而上学。他们都对实体论建构提出了批评,认为仁爱情感才是儒家思想哲理的立足点。他们对情感有不同的理解视角,大致有如下几种代表性观点,分别是李泽厚的原始情感论、蒙培元的普遍情感论与黄玉顺的纯粹情感论。
(一)原始情感论

在李泽厚看来,此传统的根源在先秦原典,它可进一步追溯至远古的巫史传统。而只有追溯至这样一个远古传统,中国古代的“天命”“天道”“天意”才具有某种直接的可理解性:
我以为,对中国文化和中国儒学特征的探究,应该再一次回到先秦原典。我多次指出,中国之不同于西方,根本在于它的远古巫史传统,即原始巫术的直接理性化。它使中国素来重视天人不分,性理不分,“天理”与人事属于同一个“道”、同一个“理”。从而,道德律令既不在外在理性命令,又不能归纳为与利益、苦乐相联系的功利经验。中国人的“天命”、“天道”、“天意”总与人事和人的情感态度(敬、庄、仁、诚等)攸关。*李泽厚:《说儒学四期》,第14页。
考虑到李泽厚希望回归远古的巫术传统来获得对天人合一的原初理解,他的情感本体论可以称为原始情感论。他指出,巫术传统的礼仪制度与规范并不是世间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约定,而被强调为天地宇宙的普遍法则,这套法则由巫师们所掌握,用来与天地和神明相沟通(《由巫到礼,释礼归仁》,第51页)。所以,巫礼中的原始情感自然包含着某种天人合一的观念。据此李泽厚又进一步指出,儒家传统的基本观念都需要回归这种原始情感才能得到清楚明白的说明:
因之孔子所要“追回”的,是上古巫术礼仪中的敬、畏、忠、诚等真诚的情感素质及心理状态,即当年要求在神圣礼仪中所保持的神圣的内心状态。这种状态经孔子加以理性化,名之为“仁”。(《由巫到礼,释礼归仁》,第30页)
但是,这种原始的情感体验是多数原始思维都会具有的。根据列维布留尔的考察,原始思维是以“万物有灵”为基础展开的,它们相信灵魂可以脱离身躯而存在,万物之间(包括人与物之间)存在着一种神秘的“互渗”关联*[法]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丁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80页。。巫术就是他们与自然打交道的方式。李泽厚也明确指出,他之提及“巫”所着眼的就是“自人类旧石器时代以来各民族都曾有过的原始人群的非直接生产性的歌舞、仪式、祭祀活动”(《由巫到礼,释礼归仁》,第39页)。儒家的礼仪与远古巫礼有某种渊源关系,这是正常的。儒家德性背后有某种原始情感的渊源,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既然这种原始情感乃是原始民族所共有的,对它的考察就不足以显示出儒家情感之独特性。

如果说西方文明对原始思维的超越是以理性、逻辑为特点,那么,儒家的超越则是以德性为立足点展开的。理解儒家天人关系思想因而就不在于回到原始情感,而在于把握它对原始情感的超出。没有这种超出或“超越”,儒家的天人合一就只是一种具有迷信色彩的原始思维而已。儒家仁道传统与原始巫术存在某种事实上的渊源关系,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仁道的本质更在于它是如何超出原始思维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原始情感论的整个讨论并未抓住仁道的思想焦点。
(二)普遍情感论
蒙培元同样立足情感本体的立场对实体论提出批评。他认为,中国哲学本体的立足点在人的作用心上,本体离不开此本心之大用,而熊十力的体用论与牟宗三的心体、性体都走上了实体论,没有真正立足“作用心”来开显本体。他说:
中国哲学讲“本体心”或“心本体”,但这并不是实体意义上的本体,而是指本体存在或存在本体,它是本源性的,但又是潜在的,没有实现出来的。它要实现出来,则必须通过“作用心”,或呈现为“作用心”。由作用而显其本体,或由功能而显其本体,本体必然表现为作用或功能,这就是中国哲学的“本体论”。对此,熊十力先生曾有过精辟的论述,但他没有同实体论划清界限。后来,牟宗三先生也大讲“心体”与“性体”,却完全走上了实体论。*蒙培元:《心灵超越与境界》,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1页。
此作用心的立足点就是人的情感。当然,个人的情感体验不可避免地具有相对性、主观性,因此,能够为本体奠基的情感不应只是个体的仁爱之情,而是需要对它有一个超越,从而成为某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情感体验:
仁作为心灵境界,是人的生命价值和意义的最高标志。它虽以心理情感为基础,但又必须超越情感,成为普遍的存在方式,这样,就同个别的心理现象、个人的情感欲望有了区别。只有从超越的层面看,仁才是境界,否则,便只是一些个别具体的情感活动,没有普遍意义。*蒙培元:《心灵超越与境界》,第139页。
那么如何超越情感的个人性而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仁爱情感呢?蒙培元指出,仁的根源不在对象之中,而在人心之中,它的基础就是同情心与爱这种道德情感。虽然这种道德情感源自个人内心,但是,人会设身处地为他人考虑,我认为痛苦的事情,别人也会认为是痛苦的,从而我不愿意的事,也不会施加于别人,这是人之常情。这种推己及人的人之常情就是仁,这样它就已经不单是个人的情感体验,而是包含了某种“理性”,从而成为一种普遍化的情感*蒙培元:《情感与理性》,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7页。。这种普遍化的情感不仅可以超出个人达乎他人,还可进一步达乎天地万物。
但是,这种意义上的普遍化和超越,并没有真正超出经验。首先,此种普遍化主要是一种基于同情心的推己及人。这就表明,它的基础是“同情心”,这依然是一种情感。其次,虽然同情心可以帮助我们超出个人化情感,将对自己的爱投射到他人甚至一般的事物上去,从而将“私爱”转变为具有普遍性的“仁德”,但是,这不过是转移并增加了爱的对象,从爱个人转变为爱他人、爱万物,这里的“爱”始终还是同一个层面的东西,都是经验情感层面的爱。根据这一思路,仁者与物同体,就会失落为对天地万物的“关怀”或“情怀”。“前面说过,仁的境界不仅是普遍的人间关怀(如‘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而且是一种宇宙关怀,比如‘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同上),就表现了这样的情怀。”*蒙培元:《心灵超越与境界》,第144页。引文中的“同上”,指的是《论语·雍也》。这种普遍关怀只是增加了关爱的对象,把它作了数量上的推广,关爱本身依然是情感经验的,依然是个体性的情感。
(三)纯粹情感论
黄玉顺的生活儒学中同样蕴涵着一种以仁爱情感为本源的思想。他通过区分仁爱的三个层级——也即本源之仁,形而下之仁与形而上之仁——来表明仁爱情感的本源性地位。本源之仁是生活儒学的思想立足点,形而下之仁与形而上仁则是他对以往乃至当代种种仁爱观的总结与批评。
简言之,形而下之仁指的是日常经验层面有关仁爱的道德情感以及相关的行为规范。这与笔者开头提出的经验层面的仁爱大致相当。这是仁爱思想的出发点。当我们从哲学上反思仁爱情感以及相应行为规范来源的时候,就走向了形而上之仁。形而上之仁是针对所有仁爱观念的形而上学建构。在黄玉顺看来,无论是形上实体,还是形上主体(包括“心体”“性体”),它们都是形而上的设定。他认为,这些设定的根源都是未明的,还需要得到进一步的追问,由此导向作为生活儒学思想核心的“本源之仁”。“本源之仁”不仅是形而下之仁(包括经验层面的相关道德情感与道德规范)的根源,而且是一切形而上层面绝对本体或实体(形而上之仁)的根源*黄玉顺:《儒教问题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7页。。为了更好地理解本源的仁爱,他还区分了道德情感与本源情感。人的情感发动起来以后,情感有善有恶,这种与善恶相伴随的情感就是道德情感。但是,本源情感不同,它指涉的是情感的原初发动本身。在情感的发动之初,还无善恶,见孺子入井发动怵惕恻隐之心,这种情感是先于善恶的,这是仁之端。这个是本源层面的情感。当我们随后把这个扩而充之,把它作为人心之大者确立以后,它才成为道德情感*黄玉顺:《生活儒学讲录》,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1页。其中引文出自《孟子·告子上》。。

与原始情感不同,纯粹情感不必回溯到原始社会状态就能得到理解,它就在我们生活的当下运作着。在这个意义上,它比李泽厚的原始情感更具本源意味。由于它明确悬置并区分了经验层面的道德情感与本源层面的“善端”,从而也有可能比蒙培元的普遍情感更具“普遍性”。但是,纯粹情感论虽然克服了观念化的瓶颈,它由此却可能走向观念的对立面,也即走向经验,因为这种“真切的仁爱情感”很容易被看作一种仁爱的“纯粹经验”。虽然它不同于传统的经验主义,但是它很难与当代改良过的经验主义划清界限,后者同样意识到了日常经验的不纯粹性,里面总已经夹杂了不少“思想观念”。詹姆士把那种未经任何观念加工过的生活之流称作“纯粹经验”:

总之,与实体论不同,情感论强调儒家哲理的立足点是人的情感。虽然论者们看到了传统经验论的困境,但无论是原始情感论、普遍情感论还是纯粹情感论,都无法说明情感相对经验本身的超出,从而也就无法恰当地说明儒学传统中的那个“超越”维度,也就无法说明儒家的天人一贯的超越传统。在这个意义上,陈来对情感论的批评是恰当的。他认为只有爱的情感,不足以挺立仁学传统。“西方哲学是爱智慧,中国儒学是爱的智慧。爱的智慧就是仁学,就是仁学本体论,没有仁学本体论,即使有仁爱,也还不是爱的智慧,不是仁的哲学。”(《仁学本体论》,第11页)但是,既然仁学是爱的智慧,这就意味着它也不能脱离仁爱情感。如果说实体论之蔽在于将本体脱离了仁者之仁,从而失落为抽象实体,那么情感论之蔽则在于从根子处抹去了形而上之本体,将其还原为情感之用。
通过上述与实体论和情感论的对话我们可以发现,以仁为本体的儒家形而上学传统应当既立足仁爱情感,又能超出情感经验的主体性限制,这才是仁道之所依。陈来也注意到了此“超越”的重要性,“仁既是最后实在,故能超越经验,但又不能脱离经验。仁是本体、生机、本性,故不是情感,情感只是用,但仁学本体论立体而不遗用,但不能以用为体”(《仁学本体论》,第39页)。事实上,李泽厚也曾指出过仁爱情感具有一个“既……又……”的维度,“这种文化精神以‘即世间又超世间’的情感为根源、为基础、为实在、为本体”*李泽厚:《论语今读》,合肥:安微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29页。。可惜的是,这样一个“既(即)……又……”的思想精神,无论在陈来的仁学本体论中还是在李泽厚的情感本体论那里,都没有得到充分的剖析与展示。
感通本体论将以此问题的可能性为引线,尝试在实体论与情感论“之间”走出第三条道路。
四、感通本体论的思想立足点

事实上,蒙培元已经指出了感通在儒家哲学思想中的重要性。他指出,儒家哲学的本体离不开作用心。这里的作用心是就心灵与外界事物的相互感通而言的。他还表明,这种感通不是感知或认识意义上的,而是存在意义上的。这就已经具有了某种感通本体论的意谓。“中国哲学所谓‘感应’或‘感通’之学,在很大程度上是指心灵与外界事物的相互关系而言的。但不是感知与被感知的关系,或认识与被认识的关系,而是存在意义上的潜在与显现的关系,即所谓‘寂’与‘感’、‘隐’与‘显’的关系。”*蒙培元:《心灵超越与境界》,第4页。但是,蒙培元这里的感通主要指潜在的东西进入了显现状态,这种“显隐”视角下的感通,在笔者看来,还不足以真正彰显感通的本体义。如果感通只是把潜在的东西显现出来,那么这就意味着那潜在的东西才是“本体”,感通在这里只不过辅助性地帮助潜在的本体显露出来。感通本体论与此不同,它要凸显的是,此一感通现象的背后并无潜在的东西隐含着,感通本身就是本体自身的终极运作。这是感通本体论的思想立足点。
从本体角度谈仁道,是宋明道学相对于先秦儒家的突破。而在宋明道学的发端处就已经隐含了以感通为本体的理路。周子是宋明道学先驱,其思想主要见于《太极图说》和《通书》。前者是对儒家道统之形上本体——“此所谓无极而太极也,所以动而阳、静而阴之本体也”*周敦颐著,陈克明点校:《周敦颐集》,第1页。——的建构,并把此本体即太极作为人之为人(“人极”)的内在根据。《通书》则是对此太极人极何以能够相互贯通的思想蕴意的进一步阐释。在朱子看来,此思路同时构成了二程天道性命思想的开端。“盖先生之学,其妙具于太极一图。《通书》之言,皆发此《图》之蕴。而程先生兄弟语及性命之际,亦未尝不因其说。”*周敦颐著,陈克明点校:《周敦颐集》,第44页。
周子论述本体的关键在于明确区分两种不同的动静:一个是太极或本体之动静,一个是物之动静。两者的区别是,太极之动静相互贯通,“动而无动,静而无静”,物则不同,物之动与物之静是各自把持自身而相互排斥的,“动而无静,静而无动”(《通书》)。在指出本体之动静与物之动静的区别之后,周子又进一步点出两者区别的关键:“物则不通,神妙万物。”(《通书》)这里的神,当指太极本体的运作。由此可见,物与本体的根本区别在于:一个是不通,一个是通。这就表明,“通”才是本体所在。结合《周易》对易之本体运作的描述,这里蕴涵着的、以感通为本体的理路可以看得更为清晰:“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易传·系辞下》)合而言之,易即太极即本体,此本体以感通的方式运作,从而不同于事物。在将太极或本体确定为感通以后,周子进一步确定人极。人之为人,在周子看来,就在于他能够将把太极作为人的本体,“得其秀而最灵”(《通书》)说的就是人能够得此本体以为自己的本体。在这里,周子也明确点出人性的关键在于“感动”,“五性感动而善恶分”(《通书》),这里的“感动”应当是感通本体在人这里的具体体现。可以说,人的灵性、人之为人就在于这一点感通之性。圣人之为圣人,就是能将感通之性充分彰显出来。“无思而无不通,为圣人。”(《通书》)当感通之性完全实现出来以后,人就能够与天地万物合而为一。
但是,由于周子文本的简约,他实际上只是粗线条地勾勒出了孔孟之道的本体论构架,其中的道理还远没有达到令人信服的地步。大致说来,它还有如下两大问题需要回应:
是日晚,琵琶仙在闹春楼里开场弹唱。因有日本人横行城里,前来听歌的票友廖廖无几。琵琶仙扫视台下,心中暗喜。
其一,太极的存在如何得到保证?虽然周子指出天地万物背后具有一个无极而太极的本体,但是,这个本体能否被确证?若否,它就只是一个泛泛的思辨。我们可以思辨出各种各样的本体论,比如西方哲学传统中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莱布尼茨、斯宾诺莎、黑格尔等等,他们都建构了一套自己的本体论思想,并且它们都有严格的展开与论证,周子不可能就凭那几十个字就完成儒学的本体论的建构。
其二,感通何以能够是人之为仁,从而也成为人之为人之本?周子同样也只是指出,得太极本体是人与万物的区别所在,得此本体人才能够成其为人。但是,周子同样没有给出足够的理由。
只有以上两个问题都得到合理的辩护与回应,援太极以立人极,也即孔孟之道的本体论奠基,才算告一段落。但是,正如牟宗三所言,周子本人对于孔子的践仁知天、孟子的尽心知天领会得并不十分真切*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上),第305页。。在笔者看来,周敦颐只是给出了一个本体论奠基的方向,具体的工作主要是由明道来完成的。“先生出,倡圣学以示人,辨异端,辟邪说,开历古之沉迷,圣人之道得先生而后明,为公大矣。”*程颢、程颐撰,王孝鱼点校:《二程集》(上),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640页。在明道这里,蕴涵在周子文本中的感通本体的思想得到了进一步展开与发挥。不管明道在思想上的发明是否直接受周子影响而来,从其留下的文本可以看出,他的思考是承接周子的思想框架而来。他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就是周子思想中的天人关系问题:“尝喻以心知天,犹居京师往长安,但知出西门便可到长安。”(《二程遗书·二先生语二上》*程颢、程颐撰,潘富思导读:《二程遗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后引此书,仅随文夹注书名及篇名。)明道这里“以心知天”的思想,与周敦颐援太极以立人极的思路是一贯的。
相比周子,明道有关天人关系的论述在以上两个问题上都有关键突破:
观天地生物气象。(《二程遗书·二先生语六》)
万物皆有春意,便是“继之者善”也。(《二程遗书·二先生语二上》)
“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生之为性”。万物之生意最可观,此元者善之长也,斯所谓仁也。人与天地万物一物也,而人特自小之,何哉?(《二程遗书·明道先生语一》)
明道这里的“生物气象”“春意”“生意”,说的并不是万物生成或生长发育这一自然现象,而是天地的“生物之心”,也即天地之仁。“‘生生之谓易’,是天之所以为道也。天只是以生为道,继此生理者,即是善也。善便有一个元底意思,‘元者善之长’,万物皆有春意,便是‘继之者善也。’”(《二程遗书·二先生语二上》)天地生物之心,也就是天地之心本身,此乃天之所以为天。那么,为何天地有此生物之心?为何此天地之心不是人心的虚构?明道的上述观点就是对此问题的回答。
理解明道上述回答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观”。这里的“观”自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肉眼观察,因为如此只能看到天地生物的自然现象,但看不到其“气象”,可以看到万物生机勃勃,但看不到“生意”盎然。明道的“观”天地生物气象,与老子讲的“万物并作,吾以观复”(《老子》第十六章)的“观”,道理是相通的,都是一种感通式的观感。观察通常预设被观察的对象相对于观察者是独立存在的。观感则不同,它需要观者自身参与其中,因此被观感的对象是由观者参与其中构成的。
这里还需要区分两种不同的“参与”。我们知道,经验主义者也主张感觉经验是主体参与构成的,比如色、香、味等感觉对象也都需要我们的参与,它们都不是自在的客观对象。但是那种参与可以说是一种完全被决定的过程,主体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什么“自由”可言。孩子天生就能看到不同的颜色、听到不同的声音,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也正如此,它们通常也被当作客观对象来看待。但观感中的参与不同,观感需要某种后天的训练,也即儒者所谓的修身的“工夫”。因此,它并不是一个完全被决定的自然过程,里面是有主体的“自由”可言的。比如我们观摩书画艺术。一个小孩子可以天生看到色、香、味,但没有一定的训练,却是看不到书画作品的“气韵”的,他看到的无非是一笔一画、一黑一白,看不出涂鸦与艺术作品的区别。观天地生意、观天地生物气象也类似,它需要的则是儒者的修身工夫。只有通过仁者的此种修身养气工夫,实现了与天地万物“相摩相荡”,才能“观”到天地生物“气象”。麻木不仁者是看不到这种“生意”“气象”的。明道曾明确指出,“观”天理的关键在于放开心胸,如此才能合内外而观天地之仁。“观天理,亦须放开意思,开阔得心胸,便可见,……须是大其心使开阔,譬如为九层之台,须大做脚须得。”(《二程遗书·二先生语二上》)这种放开心胸的观感与那种擦亮眼睛的观察因而也就不是同一个层面的事。由此也可看出,观天地生物气象与实现仁者之仁,是同一个过程,它说的都是在内外贯通的意义上的观感、观摩,而不只是一个外在的观察。在观摩的过程中,与天地万物相摩相荡,而后得其气象,得其生意。
不仅如此,明道还以感通式的体察为人心之仁提供了辩护。这方面论证主要是借助医书所言的手足痿痹现象展开的,他以此来指点出人心之仁:
医书言手足痿痹为不仁,此言最善名状。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认得为己,何所不至?若不有诸己,自与己不相干。如手足不仁,气已不贯,皆不属己。”(《二程遗书·二先生语二上》)
医家以不认痛痒谓之不仁,人以不知觉不认义理为不仁,譬最近。(《二程遗书·二先生语二上》)
医书有以手足风顽谓之四体不仁,为其疾痛不以累其心故也。(《二程遗书·二先生语四》)
以上几处引文思路基本一致,均系以医书所言的手足麻木不仁来指点人心之仁与不仁。大家都知道,手足在麻痹的时候是没有感觉的。医书说此状态是不仁,不仁也即不通,“气已不贯”。这就反过来表明,仁是一种与通相关联的状态。那么,我怎么知道自己的手足是不是麻木的?这同样不能通过观察来把握。在手足痿痹状态,从观察的角度来看,手足与身体还是一体的,并无两样。用明道的话说,对感通也即对自身是否处于仁态的把握,可以称之为“体察”,如所谓“独能体是心而已”*黄宗羲原著,全祖望修补,陈金生、梁运华点校:《宋元学案》(一),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553页。。这里的“体察”与前面的观象一样,都不是外在的观察,而是感通自身实现出来的过程。明道提出的识仁或“仁体”,就是以这种感通式的“体察”为立足点的。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并不只是说天地万物关联成一个整体。从明道所举的例子中也可以看出,在手足痿痹时,它们与身体依然是连结在一起的,但这种连接在一起,并非明道心目中的“一体”。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深切地体察到手足不是自己的。“若不有诸己,自不与己相干。如手足不仁,气已不贯,皆不属己。”由于从麻木不仁到内外感通,大家都可以有切身的体察。明道就以此指点出人心之本就是此种感通。
陈来把万物关联一体的本然状态作为仁体,在笔者看来,就没有注意明道所暗示的两种不同的“一体”。明道的一体或仁体,说的不是万物简单地相互关联在一起(可称之为“关联体”),而是一种以仁者为“中介”而发生的内外感通状态(可称之为“感通体”)。一旦不麻木了,一旦通了,手足与身体就处于一种活生生的“一体”状态。这个一体,是以感通为本体的“一体”。感通是此万物一体的枢机。唯有与天地万物相感通,也即能“体天地之化”,而后才有“万物一体”。“言体天地之化,已剩一体字。只此便是天地之化,不可对此个别有天地。”(《二程遗书·二先生语二上》)“天地之化”并不是一个等待着我们去体察的外在对象,它并不外在于这个体察过程,此“体察”即是感通,从而即是天地之化之“体”。这是感通本体论与实体论的根本区别。西方现当代哲学中的过程论者、要素一元论者等等,都说的是万物一体,但是它们的一体与儒家的一体有根本的区别。前者是某种思辨性的先天关联实在,后者则有待于仁者之仁。
由此我们还能看到感通本体论与情感论的区别。此处的感通不同于经验层面的感觉。手足痿痹不仁时,我们就没有感觉了,不再能通过它们去感触外物的存在。而这同时就表明,感通不同于感觉。当手足处于感通态的时候,它能感觉外物的存在,能具有不同的感觉,这种感觉本身是流动的、变易的,而这种感通状态本身却是相对恒定的。可以说,感通是感觉得以可能的“通道”。作为仁道的感通不同于情感,它能够打开一个新的物我内外关系之通道。在此通道中,我们可以有新的感觉。这种通道的开启,先乎感觉。它暗中引导我们的感觉,引导我们的情感体验。
这种感通的能力或可能性可以称之为“仁心”,也即人心那一点“虚灵不昧”之灵明。人一出生,就有此仁心,就能够与父母、与他人乃至与外物发生感应。此种感应互通,是一个人能够成为人的关键。仁爱的感情以及语言的习得,都以此感通为前提。刚出生的小孩如果没有这种感通能力,他是不可能学会语言的。鹦鹉能听见并模仿人的语言,但是它不能学会说话。为什么?因为它缺少这种感通能力。感通是一种被动发生,它不是理智可以随意控制的。另一方面,被动发生又不意味着它是一个完全被动接受的过程。感通之为感通,就在于它能够生出一个通道,而这个通道恰恰是朝向未来的,并因此能够事先引导我们的行为方式。这是一种先行开道的能力。为什么小孩子能学会语言?小孩子听见大人对他说话的时候,不只是单纯的记忆与模仿。如果只有记忆与模仿,那么,他就只能鹦鹉学舌,永远不可能学会说话。此过程最关键的是,在听到大人声音的时候,他能够有“回应”,能够“预判”其中的“意谓”。虽然此种意谓在这里还不是明确的意义,但它是意义的前身。这就是感通,它不只是接受,而且还能借助所接受的东西获得一种往前伸展的“趋势”,从而有一个对接受内容的“超出”。
感通能力即是仁心,人之为人的“种子”(“心如谷种,其生之性乃仁也”*黄宗羲原著,全祖望修补,陈金生、梁运华点校:《宋元学案》(二),第1525页。),此乃人心之本。成人以后,仁心逐渐成为成心,使得人与人之间、人与物分离开来。人有七窍,此仁心可以称之为第八窍。这是人之为人最重要的一窍。此窍在人出生时是自然开启的。否则你不能成为人。你看小孩子,成天都手舞足蹈的。成人以后,思虑日深,成心、机心渐重,此窍逐渐闭合。随着年纪增长,我们拥有的东西越来越多,而拥有的快乐反而越来越少。为什么?这是因为这第八窍闭合得越来越紧。
此感通开启的通道影响我们的感觉与认知,从而也直接影响我们对存在的把握与体认。这个意义上的感通已经不只是人伦道德层面的东西,同时还有本体论的意谓,因为它还暗中引导着我们对事物的直接感受,从而也引导着事物向我们的“呈现”。如此,根据感通本体论,“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中的“一体”,不是先天自在的一体,不是概念思辨的一体,而是感通之后生成的一体。
五、结 语
最后,回到我们开头提出的那个问题,也即,一种源自人心的仁爱情感如何能超出自身而成为贯通天地物我的仁道?从感通本体论的角度看,这不是因为人与万物本来就是一个先天的关联整体,也不是通过爱的情感来实现一种后天的关联,而是在仁爱情感的根子处揭示出人之为人的另一种可能性,一种能够超出自身从而能够与他人以及他物相互感通的可能性。此可能性正是人之为人之“枢机”,也是儒家仁道思想之所依。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离不开“仁者”之“仁”。由于此感通之可能性最直接、最源发地体现在亲子关系之中,这就从整体上决定了儒家思想强调孝悌、强调亲亲的哲理特征,“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中庸》)。我们知道,父母甚至可以比子女自身更能深切地感受其冷暖痛痒。这里的“感同身受”正是人心之感通本性的生动体现,它表明,人心在根子处有一种能够超出自身去代替他人感受的能力。儒家重视孝道,不只是为了给老人养老送终,让他们有个好的归宿,而是同时希望能以此更好地唤醒并更长时间地维持住人在幼年时期与父母亲的那种互相关联的“感通”关系——“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论语·为政》)——从而守住自己的“仁心”。此种“感通”状态或仁态,不只是孝道之根,也是一个人能够与他人、与万物和谐相处的出发点,“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论语·学而》),“知者乐水,仁者乐山”(《论语·雍也》)。只有复其感通之性,人才能够与他人相唱和,也才能纵情于山水之间,如此,才有万物一体。这种“一体”,才是“活”的一体。
因此,情感论虽然强调仁道离不开人心,但它无法恰如其分地说明仁道何以能够超出人心的主体性限制而成为贯通物我内外的天人之道。没有这样一个超出与贯通,儒家乃至中国文化的精气神就立不起来,甚至会沦为某种“实用主义”。李泽厚把儒家的理性解读为实用理性,安乐哲把儒家伦理归结为角色伦理,在笔者看来,都没有很好地看到此贯通天人的仁道在儒学思想中的奠基地位。实体论虽然看到了此超越与超出之贯通的重要性,但是,它将仁者之仁所达到的内外一贯的“结果”作为本体,并将它普遍化,这就使得如此而来的“关联整体”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失落了何以能够内外一贯的“本源”。事实上,虽然实体论与情感论在立场上针锋相对,但它们都没有看清仁者何以能够发动仁心而能够达到与天地万物相互一贯的道理,也因此都将它归为某种神秘体验。李泽厚就这样评价“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作为个人体验,确乎可以承认有某种神秘经验,但神秘体验一般颇难具有客观普遍性,经常是偶发、短暂、独特和充满个体差异的,……”(《由巫到礼,释礼归仁》,第131页)陈来也暗示,通过仁爱达成的人与物的合一具有某种神秘性,因此他要提出一种万物本然关联的实体论来消除仁者与物同体的神秘性(《仁学本体论》,第34页)。从感通本体论看,这里的情况就不同了。此处的“体”既不是什么神秘体验,也不是本然的关联实体,而正是感通本体所在。
此“体”不仅不是神秘体验,也不是“先验幻相”。根据康德哲学,当我们超出经验领域去使用知性范畴,去把握经验背后的本体时,就会产生幻象,这种幻象是理性自身构想出来的“思想存在物”*[德]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李秋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72页。。但是,根据以上对感通本体思路的考察,我们发现,儒家思想传统中的本体是可以回避康德的批判的,它与先验幻象之间有关键区别。虽然此天地之仁、人心之仁并不是感觉经验的对象,具有一个对纯粹经验领域的“超出”,但是,此“超出”并不意味着它仅仅成为单纯的概念思辨或康德所说的“思想存在物”,因为它可以被“体察”、被“观感”,而非单纯的概念设定。由此亦可看出,中国天道中蕴涵的哲理“超出”了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经验与理性的二元对立,也正因此我们才需要“另辟蹊径”,才可能接近它、通达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