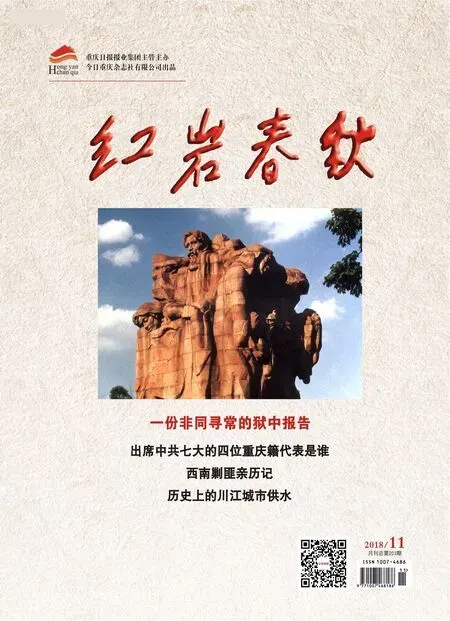起义失败后他们来到重庆
■林向北

◇巍巍华蓥山(陈云栋/摄)
1948年,这是风起云涌的一年。我们三年前就开始准备的华蓥山区武装起义,因为叛徒出卖不得不仓促提前,从8月10日曾霖大哥他们在广安代市打响第一枪开始,只进行了短短42天,就在敌人的重兵“围剿”下失败了。
起义震惊了当时正在重庆召开的四川省参议会上的要员们,省主席王陵基当即指令:不能让华蓥山变成四川的“盲肠”。成渝各报也纷纷披露:共产党此举在于利用游击武力,发动农民运动,接应共产党的部队入川。那些上层人士都慌了,纷纷给蒋介石打电报,要求派出“得力部队进剿”。蒋介石很快给四川的保安部队来电,责询华蓥山“土共”情况,命令迅速扑灭。
我们在这场斗争中的牺牲是惨重的。据不完全统计,我们牺牲了45人,被捕后被送进渣滓洞、白公馆关押并最后牺牲的有70多人,至于起义失败后在敌人“铁箅式大清乡”中和群众一起被杀害的,更是不可估算。这其中,不少是和我们一起战斗过的同志和亲人。
城里城外寻找从战场撤退下来的同志

◇华蓥山游击队员使用过的枪械
起义失败后,领导同志迅速分散隐蔽,被打散的战士和基层的同志们纷纷退到重庆。敌人派出大量特务,在大街小巷游荡,见谁不顺眼就跟踪,还兴了身份证、连坐法、查户口……特务们随时随地都可能带着叛徒,在任何地方搞突击搜查,甚至沿街抓人。重庆大大小小的看守所里,塞满了以种种荒唐理由逮捕的人员,等待叛徒特务和当地的地头蛇来逐一指认。我们也经常被跟踪,怎样甩掉这些“尾巴”,成了专门的“技巧”。
一天,宁君(廖宁君,林向北妻子)走到观音岩,发现后面又被“尾巴”盯上了。她走得慢,跟她的“尾巴”就慢,她走快了,那“尾巴”也快。她假装进百货店买东西,“尾巴”就在对面街上的铺子前等着。到了七星岗,她快步从小路进入江苏同乡会会馆,闪身进了一个房间,躲在角落里往外偷看。那“尾巴”眼看目标跟掉了,正在东张西望地着急,趁着那人一转身,宁君终于看清楚他的面目,原来是从华蓥山下来的冯群生。
宁君连忙从屋里出来,喊了一声“冯胖娃”,有些埋怨地说:“你怎么不打招呼,我还以为是特务跟踪呢。”
冯群生喘着气说:“哎呀我的个天,前几天好不容易找到你,就低头抽个烟锅巴的工夫,你就不见了,害得我又找了三天,今天才终于把你找到了。你打扮得这样摩登,我敢在大街上认你?刘石泉有要紧的事情找你们,急得很呢。”
第二天,老刘早早在约定的茶馆等我。我打破了秘密工作的纪律,把他带到了歌乐山我们的临时住地。诗伯(陈联诗,“双枪老太婆”的原型之一)看见刘石泉高兴得不得了,这些天她最担心的,就是老刘了。
老刘是从战场上撤退下来的,因为是上了特务“黑名单”的要犯,处境相当危险。我建议他像其他离队同志一样,去外地躲一躲,可是他最担心的,却是从山上撤退下来的数以百计同志的安全。这些退到重庆的同志,有的本来打算投靠亲友,但是亲友怕事不敢收留;更多的在重庆没有任何关系,有几个小钱的还可以到鸡毛店或者是江边小船上暂且栖身,没有钱的只好流浪街头。天气渐渐冷了,他们没钱吃饭、没衣御寒,万一再落到敌人手里,麻烦的事情就多了。
老刘长叹一声,说:“自从今年4月份重庆市委的刘国定、冉益智被捕叛变后,我们先后有130多个同志被捕,起义被迫提前,连王璞同志也在武胜牺牲了,我们可是被叛徒害苦了。目前我们还没有与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失散的同志们群龙无首,更可能出问题,你我要主动负起责任来,找到一个算一个,不要让他们去乱闯乱碰。”
老刘自1945年就受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派遣到华蓥山区,起义前是第七工委副书记和第七支队副政委,对起义的干部和战士都很熟悉,寻找和联络这些来渝人员,当然由他负责。我在重庆待的时间比他长,社会关系比他多,这些人员的安置工作主要由我来承担。我们每天上午九点钟,在指定的茶馆见面,交流情况,确定任务,然后分头去忙各自的工作。
刘石泉不幸被特务装进了“口袋”
老刘找人,有时候还有点线索,更多的时候是和冯胖娃一样,到大街上去碰。他心急火燎地整天在城内外跑来跑去,很少有空手而回的时候。在这特务如麻的山城,我每天都在为他担心,不得不提醒他:“你是上了黑名单的人,是特务捉拿的头头,这样到处抛头露面,很危险哦。”
老刘说:“那么多人举目无亲身无半文,他们整天在街上乱窜,那才危险呢。”
老刘很辛苦,我也不轻松。歌乐山离城里还有20多里路,我每天早上六点起身,要走两个多钟头才能到城里,晚上八九点才回到歌乐山。老刘把找到的人交给我,我就得解决他们吃穿住的问题,还要给他们找工作作掩护,保障他们的安全。那个时候,肯为我们帮忙的人,是要承担风险的,我全靠一张嘴和一双腿,利用旧关系,寻找新门路,到处说好话,求菩萨,不管是守门的,打杂的,担水的,卖菜的……只要是人干的活路(重庆方言,即“事情”)都行。短短三个多月的时间,我们已经联系到岳池、合川、武胜起义地区的撤退人员近百人,其中有半数以上是老刘找到的,其余的也是一个串一个联系上的。
不久,我终于和上级联系上了,来人居然是和我在江油一起工作过的黄友凡。一天,我同宁君在市中心的米亭子与老刘碰头,告诉他这个好消息,并约好第二天上午十点钟在民生路一个茶馆里相会。
次日,我和黄友凡来到接头地点,等了一个钟头,还不见老刘的影子。按照地下时期秘密工作的原则:接头时间如果过了五分钟,就要立即撤退,并且马上改变自己的住处。可是对于老刘,我们压根就没往坏处想,于是第二天又去,第三天再去,依然不见人。我们这才担心:是不是出事了?
不幸的消息终于传来:那天我们在米亭子分手后,老刘去了和平路一个同志家,谁知这个同志头天已被逮捕,特务在他家里设下埋伏,老刘一去就被装进了“口袋”。
老刘是一个很重情义的人。起义失败后,很多领导都隐蔽起来不再露面,诗伯也曾经让我为老刘找个地方躲一躲,他却为了大家的安危在重庆城里四处奔走。他的被捕,让大家都很震惊,不少人为他痛哭失声。
老刘在监狱里,受了很重的刑,除了坐“老虎凳”,敌人还把他吊在房梁上打,他也没有吐露半点秘密。他被捕之后,与他有关联的那么多人,没有一个因他而受牵连,我们的一切活动照样进行。后来我们收到老刘从渣滓洞送出的一张字条,大意是:不必为我担心,我这里没有什么东西……我们时刻准备着。
这时候,人民解放军南下势如破竹,一向乐观的老刘在监狱里作好牺牲的准备,同时也在积极争取迎接解放。他用指甲和铁皮在囚室的墙壁上刻下监狱里发生的“大事记”,这样即使难友们全都牺牲了,以后人们也能够了解敌人的罪恶。同时,他还暗地里挖空墙壁准备越狱,不幸被敌人发现。1949年11月27日,蒋介石下令对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的政治犯进行大屠杀,老刘在解放军的炮声中走上刑场,年仅36岁。
给同志们安排职业解决生活
刘石泉被捕后,给我留下一个大摊子:这么多人要吃饭、穿衣、住宿,还要给他们找工作作掩护,一有风吹草动还得赶快转移——这些事情原来由我和老刘一起承担,现在都落到我一个人肩上,把我急得焦头烂额。我和宁君还有诗伯,动用了所有的社会关系,成天到处跑。
我们首先要解决的,就是那些从来没有进过城、人生地不熟的乡下农民。好在他们虽然没文化,却有的是力气,什么活都能干。
我在万县时的好朋友吴昌文,此时也到了重庆,在城里夫子池艺术馆当总务主任,他大姐也在重庆,与别人合开了一个冰糕厂。八九月份,天气还燥热,正是卖冰糕的好时节,我马上安排了几个人去吴大姐的厂里,有的在车间做冰糕,有的背冰糕出来卖。冰糕箱是从厂里借的,冰糕也是从厂里赊的,卖完冰糕后才付钱。

◇1940年,林向北和廖宁君订婚,与家人合影。左起:陈联诗、林佩尧、林向北、廖宁君
但天气一凉,冰糕厂停产,靠卖冰糕生活的人也失业了。我就安排他们去卖报。我拉了几年的广告,在报界混得很熟,城里的《国民公报》《大公报》《新民报》《新蜀报》都有熟人,由我出面去接洽,可以卖了报纸再付钱。
城里遍地都是特务,听到谁的口音不对就要抓,郊区的防备相对宽松一些,我们就把好多同志安排到北碚、南温泉、巴县、马王场、土桥、蔡家场等乡下。他们可以到农民地里买来一些菜,在小河沟里洗干净后,再挑到街上去卖。秋冬季节,正是水果成熟的时候,他们可以到码头上的水果市场去批发由附近各县运来的橘子、广柑、梨子、柚子,或是挑着担子沿街叫卖,或者在路边摆个小摊。这些行当虽然辛苦些,但赚的钱也要多些,而且不限时间,不限地点,不上税,不交费,出了什么事情大不了扔下就跑,我们把这叫作“自由职业”。
重庆人临江居住,由此衍生了一个行当:挑水夫。当时重庆只有极少的地方有自来水,大多数居民还是吃的江水。比如从合川撤退下来的张大汉,有的是力气,又不怕吃苦,就到长江边去挑水卖。张大汉每天挑着两只能装百来斤水的大桶,来到临江门,涉水走到江边荡起一大挑水,再一步一步登上二三百步石梯,再走一大段路,挑到较场口去卖。这一段坡高路陡,路途较远,每天只能上午一挑下午一挑,所以工钱也特别高——每挑水要卖一块大洋。那个时候,我们发给同志们的基本生活费每天只有两角至五角钱,张大汉辛苦挣来的两块钱,可是个大数目。他只给自己留下很少的一点儿钱,其他的都给了那些生活没有着落的同志。
除了这些农民同志外,还有一些党和游击队的骨干,早已成为特务注意的重点,不能满街转,必须找一个可靠的职业或单位作掩护。好在他们大都年轻,有些文化和交际能力,我们就通过关系,把他们安排到年轻人成堆而且流动性大的学校去当学生。当时重庆的大学中学很多,有公立的也有私立的,如重庆大学、省教育学院、勉仁学院、南泉新闻专科学院、东方人文学院……甚至诚善中学都有我们的同志。
还有一个重要的去处,就是利用国民党军队大崩溃正四处招兵之时,趁机安插我们的人,既可掩护自己,还可进行策反工作。我的妻弟廖亚彬带了几个人,打入杨森20军79师一个连里去当兵;冯群生被安排在一个师管区当文书;从武胜来的王香西,去了市中心的小什子派出所当文书;到后来,还派了张平和等人打入了看守渣滓洞、白公馆的特务武装。
度过寒冬迎接曙光到来
冬天紧随而来,让人头疼的是,这么多人要吃饭穿衣,钱成了个大问题。因为打内战,国统区的经济很萧条,市面上物价飞涨,工商业纷纷倒闭,以前很赚钱的拉广告也不容易了,我得另寻门道。可是做什么呢?卖中成药吧,不赚钱;做买卖吧,物价一天几涨,用刚刚卖出的货款就买不回新货来,肯定赔本。我成天在城里寻找机会,终于发现了一个行当。
当时国民党为了强迫老百姓用他们发放的金圆券,就禁止银圆流通。可是由于物价飞涨,法币贬值,发行的金圆券成了废纸,银圆非但禁而不止,反而成了保值存储的“硬通货”。别说手里有些积蓄的达官贵人,就是一般的小职员,手里有几个钱的小老百姓,都纷纷急着把手里的法币换成银圆。城里的银圆市场上,从清早到深夜都是人来人往,拥挤不堪,其中有资金雄厚的投机商,成千上万的买进卖出,操纵市场;也有不少小市民和无业游民,凑上十块八块的本钱,整天在市场里窜进窜出,逢低买进,有赚卖出,赚几个伙食零花钱。这行当不但可以赚钱,还因为形形色色的人进进出出,能够掩人耳目,是我们接头活动的好场所。
找准机会后,我就把过去做广告挣的钱,连同手里的那点中成药卖了凑点钱,加入银圆贩子的行列。那时候人年轻,脑子灵活,没几天工夫,赚钱的诀窍就弄得一清二楚。我每天拿着几块银圆叮叮当当地敲着,从人群的这头挤到那头,口里喊着“三年呢——闭眼!”意思是我手里拿着的是民国三年造的银圆,上面有袁世凯闭着眼睛的头像,这是当时最值钱的货色。运气好的时候,我一天能赚上一两块银圆。分散在各地的联络员,也在这里和我碰头,向我汇报情况,要我解决什么问题,我们大都长话短说。对那些生活困难的同志,我以每天五角的伙食费为标准,给两元以解燃眉之急。
有一次,我正在和一个买主做交易,远远看见几个便衣警察手执敷满沥青的警棍,追赶着银圆贩子和看热闹的人。我跑慢了一步,被警察追上来,照着我就是一警棍。我一转身,那警棍打在我背上,一件还有几成新的白衬衫“哗啦”一声挂破了,沥青沾了我一背。好在人多,我在人群中挤来挤去,边跑边把衬衫脱下扔掉,光着个脊梁跑到艺术馆老吴家里。老吴夫妇看我背上青一块黑一块,还以为我挨了打。
冬天寒风凛冽,同志们来时还是暑天,穿的衣服很单薄,天气一冷,大家吃饭都很困难,哪有钱去缝制棉衣。我只好发动一些家在重庆的同志找亲友想办法借点旧的,在清华中学教书的汪国桢也在学生中发动募捐,加上我们在旧货摊上买些便宜的旧货,总算解决了一批棉货,帮助同志们勉强度过了严寒。
这些同志一共214名。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市民夹道欢迎人民解放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