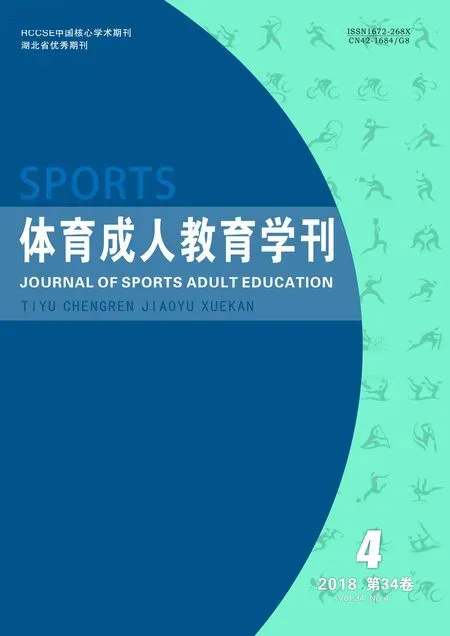我国体育赛事产业规范的演进与成效
张现成,徐秀芬,李成菊,樊 浩
(1.广州大学 体育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2.湖南文理学院 体育学院,湖南 常德 415000)
2014年底国务院46号文件中“取消商业性和群众性体育赛事活动审批,加快全国综合性和单项体育赛事管理制度改革,公开赛事举办目录,通过市场机制积极引入社会资本承办赛事;将赛事功能需要与赛后综合利用有机结合的规定”[1],不仅为社会力量最大程度地盘活体育产业提供了契机,也标志着我国体育赛事的产业化改革进入到一个新的博弈阶段。但是正如俗语所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没有规范就没有秩序”。规范,就是规则和标准,主要包含道德规范、行政规章、法律规定、团体章程等[2]。如果缺少对体育赛事产业有效监督管理的规范,体育赛事的产业化难免会有“失序与失控”的危险。因此,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体育赛事产业化的相关规范进行系统性梳理与解读,不仅可以了解我国体育赛事产业化发展的现状,更能预测我国体育赛事产业的发展趋势,推进体育产业健康发展。
1 我国体育赛事产业规范演进的梳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体育赛事产业规范的演进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共63个文本,主要是国家体育总局(原国家体委)、国务院(含国务院办公厅)、国家旅游局、教育部等部门颁发的文件。
1.1 我国社会主义计划商品经济时期的赛事产业规范(1978—1991年)
这一时期的体育赛事产业规范主要是顺应我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转型发展而做出的政策性调整。涉及体育赛事产业化的规范主要有:《关于充分发挥体育场地使用效率的通知(1980)》、《国务院批转国家体委关于进一步开创体育新局面的请示的通知(1983)》、《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发展体育运动的通知(1984)》和《关于体育体制改革的决定(1986)》等规范性文件。其具体内容主要包括,发挥体育协会功能推进体育赛事改革,首次提出体育场地可以出租给文化部门,并通过体育电视、广播、广告等渠道,拓展体育赛事的商业价值、倡导体育场馆由行政管理型向经营管理型过渡的多种经营模式。这些内容为政府回收财政投入、减少体育事业的财政负担做出了有益贡献,标志着以体育场馆场地出租为开端,带动体育赛事吸引社会资本投入的赛事产业化改革的萌芽[3]。
1.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期的赛事产业规范(1992—2001年)
这一时期以1992年“红山口”会议为起点,围绕运动项目协会、俱乐部制及体育赛事产业化改革试点工作,进行了顶层设计,出台了诸如《全国体委主任关于培育体育市场,加快体育产业化进程的意见(1993)》、《国家体委关于深化体育改革的意见(1993)》、《关于运动项目管理实施协会制的若干意见(1993)》、《国家体委关于加强体育市场管理的通知(1994)》、《体育产业发展纲要(1995-201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1995)》、《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国家体委关于进一步加强体育经营活动管理的通知(1996)》等一系列推进体育赛事产业化改革的规范性文件和法规。其内容上不仅确立了以足球为突破口的赛事产业化改革试点,还提出了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运动项目协会制、俱乐部制和体育赛事经纪人制度,倡导体育赛事产业作为我国体育产业的支柱产业,引导体育竞赛与其他产业融合,鼓励社会资本以合资、合作、入股等形式,投资体育赛事产业,推进体育竞赛体制和运行机制的改革。这些规范为推进体育赛事的实体化、产业化、社会化和法治化,提供了有益指导。如《国家体委关于深化体育改革的意见(1993)》中“要加快运动项目协会实体化建设步伐,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协会制,积极开发以体育竞赛为主体的,与经济贸易、文化、旅游、科技、卫生等相融合的体育产业……鼓励以合资、合作、入股等形式进行投资,大力发展竞赛产业的目标是通过竞赛体制的改革和运行机制的转换,推进竞赛的社会化、产业化……使竞赛产业成为体育产业中的支柱产业”[4],就是推进赛事产业化改革,加快赛事产业与其他产业融合的顶层设计。
1.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期的赛事产业规范(2002—2017年)
这一时期,为克服金融危机给中国经济社会带来的消极影响,国务院相继出台了众多中国特色的振兴产业计划。体育赛事产业作为朝阳产业和绿色产业,成为中国特色产业振兴计划的重要内容和实现国民经济新增长点的重要手段。国家政府部门颁发了诸如《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的指导意见》(2010)、《体育产业“十二五”规划》(2011)、《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2013)、《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文化部等部门关于做好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工作意见的通知》(2015)、《体育产业“十三五”规划》(2016)、《国家体育总局关于推进体育赛事审批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2014)和《国务院关于加快体育产业消费的若干意见》(2015)、《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2016)、《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2016)、《关于进一步激发社会领域投资活力的意见》(2017)、《国家旅游局、国家体育总局关于发展一带一路体育旅游行动纲要》(2017)等一系列涉及发展体育赛事产业的规范性文件。这些规范在内容上主要从深化足球产业改革、健全职业联赛赛制、扶持职业体育组织、加大冰雪体育产业投入、推进体育行政放权、赋予职业体育组织高度的自治权、保障公民健康权益、着力体育赛事与一带一路经济建设融合、创新市场运行机制、挖掘赛事产业中的肖像权、举办权、冠名权、转播权、转会权及其他可以进行市场交易的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方面入手,进行市场开发,最大程度地发挥其产业价值,积极倡导赛事产业服务的政府购买机制。这些规范为消除赛事资源政府垄断的壁垒,推进赛事的行业化、社会化和产业化,提供了政策性保障。如2015年7月颁布的《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总体方案》明确规定,“取消行政机关(包括下属单位)与行业协会商会的主办、主管、联系和挂靠关系。行业协会商会依法直接登记和独立运行。行政机关依据职能对行业协会商会提供服务并依法监管”[5]和《体育发展“十三五”规划》明确指出,“完善职业联赛,探索运动项目产业化道路……建设品牌赛事”[6]。上述赛事产业化条文不仅赋予了赛事运行主体高度的行业话语权,而且指明了以项目为中心、打造品牌赛事的产业化发展道路。
1.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赛事产业规范(2017年至今)
这一时期,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7]。体育赛事产业规范将迎来服务于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发展新矛盾的供给侧结构改革新篇章。
2 我国体育赛事产业规范运行的成效
2.1 服务赛事产业的体育社会组织得到蓬勃发展
自从我国推行体育行业改革,实行以项目为中心的协会制以来,体育社会组织在全国得到蓬勃发展。据统计,仅2017年湖南省常德市就成立了市(县、区)体育协会30多个,成立体育文化社团187家,体育类创新创业单位450家,民政局备案私营体育健身俱乐部387个,举办民间赛事300多场。2016—2017年,常德市政府为扩大柳叶湖度假区的有利区域优势,出台鼓励和支持体育社团承办各类体育赛事的政府补助制度,于是体育社团先后承办了诸如国际龙舟赛、国际马拉松常德赛、全国高校龙舟赛、湖南省龙舟赛等较高级别的赛事。2017年全市体育协会及相关项目分会还先后承办了区县市篮球赛、羽毛球赛、健美操、足球赛、广场舞、健美操赛、环湖自行车赛、垂钓、竞走、冬泳和沙滩排球等群众性赛事400余次,赛事参与者多达80万人,体育社团遍布到村落乡寨。体育社会组织的蓬勃发展为赛事产业服务的不断升级提供了良好运行保障。
2.2 政策红利激发社会资本对赛事产业的关注与投入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2014)》、《国务院关于加快体育产业消费的若干意见》(2015)、《体育产业发展“十三五”规划》(2016)、《体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2016)、《关于进一步激发社会领域投资活力的意见》(2017)等一系列鼓励体育赛产业发展的规范性文件的出台,进一步激发了社会资本对赛事产业的关注与投入。据统计,在体育赛事产业政策红利的刺激下,仅在2013至2016年上半年,体育赛事产业融资案例就达到247起,总融资达到159.91亿元左右[7]。就赛事产业融资趋势而言,2014—2015年的融资案例和融资规模均出现大幅度增长,融资案例同比增长率为380%,融资规模同比增长率为231%,这与2014年底国务院46号文件出台引发大量社会资本涌入体育产业的趋势相吻合[7]。而阿里体育和腾讯分别于2016年8月和2015年1月获得了里约奥运会网络播映权、优酷体育独家运营权和NBA五个赛季的网络独家直播权,百度的“够力足球”和京东体育的体育生态圈也充分利用互联网进行赛事营销[8]。2017年5月浙江章兰朵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在浙江金华市体育中心主办了国际标准舞(体育舞蹈)公开赛暨中俄友好对抗赛。比赛吸引了俄罗斯、英国、波兰、新加坡等13个国家和地区近2 000名中外选手参加,还邀请了德国、意大利等国际裁判评委按照国际领先的体育舞蹈竞技管理系统为选手打分[9]。
2.3 建立了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的社会机制,民生体育赛事产业得到快速发展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3〕96号)和《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文化部等部门关于做好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工作意见的通知》(2015)两个文件的颁发,标志着我国已经逐步建立起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的社会机制。在这一机制的催生下,各地政府颁发了一系列探索建立政府财政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体育服务的规范性文件,如2014年江苏省颁布的《江苏省本级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体育服务暂行办法》的通知〔苏体规(2014)2号〕、《常州市关于购买公共体育服务的实施办法》(2014),《常州市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体育服务实施办法(暂行)》(2016)的通知、沧州市的《政府关于购买公共文化体育服务实施办法(2016)》、金华市的关于印发《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体服务的管理办法(试行)》(2016)的通知、威海市的《关于加快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2017)等,规范了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赛事服务的内容与流程。2015年10月27日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发布了《关于购买2016年全国残疾人体育赛事服务的通知[残联函(2015)249号]》,将全国轮椅舞蹈锦标赛、全国盲人跳绳比赛、全国残疾人羽毛球锦标赛、全国脑瘫足球锦标赛、全国残疾人冰壶锦标赛(轮椅组、听障组)、全国越野滑雪锦标赛、全国聋人田径、游泳、乒乓球、网球锦标赛、全国特奥足球比赛、全国特奥乒乓球比赛等9项赛事全部以254.7万向社会购买服务的方式举办,并予以基础办赛经费每赛事5万元,赛事补助150元/人/天的补差进行补助[10]。2016年3月瑞安市体育局发布公告,安排预算18万元,通过公开招标的形式将武术、健身跑、篮球、登山四个项目赛事承办工作向社会购买服务[11]。2017年上海市体育局把开发区运动会、亲子运动会及篮球赛、足球赛等共20个赛事,实行社会招标、政府购买的方式,吸引了66家体育协会和企业参与竞争[12]。政府购买体育赛事服务的社会机制推动了民生体育赛事产业的健康发展。
2.4 “体育赛事+”成为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有力手段
2014年国务院46号文件明确规定,将创新体制机制、培育多元主体、改善产业布局结构和促进融合发展作为其主要任务。在促进体育产业与其他产业融合发展过程中,以“体育赛事+”为核心的体育产业经济引起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如2017年大荔县通过举办“2017全国竞走锦标赛、2017世界名校龙舟大赛、2017大荔国际马拉松赛、2017中国自行车大会”等四大赛事,组织大荔旅游文化展示、名特优新农产品展示展销和美食文化展示等活动,充分体现了“赛事+经济”、“赛事+旅游”和“赛事+农业”的产业融合发展理念。正如大荔县委常委、县人民政府常务副县长王德强所说,充分利用举办大型体育赛事活动的有利时机,以丰富赛事活动供给,大力发展体育旅游,推动产业升级,为地方经济社会转型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动力,是大荔县在相互融合发展中走出的一条新路子[13]。
2.5 优秀运动员的道德品质和项目本身关注度在赛事产业中的商业价值越发凸显
长期以来,“优秀运动员的道德品质”一直成为大众关注或企业赞助体育赛事的重要条件。随着赛事举办、赛事标志、赛事转播、运动员肖像、运动员转会等具备交易条件的无形资产版权开发与流转的政策性松绑,使得优秀运动员和关注度高的运动项目的商业价值在赛事产业结构中的作用越发凸显。优秀运动员的道德品质和项目本身的高关注度不仅可以成为企业品牌形象的代言,为企业创造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而且也可以吸引社会力量竞争赛事举办权或对赛事进行巨额投入。关注度低、参与度少、观众基础薄弱的体育项目,其商业价值就低,如冰球、射箭、举重等项目。优秀运动员的道德品质在赛事产业中具有重要价值,运动员一旦出现道德品质的滑坡,即使他再优秀,他所参与的赛事也很难实现收益。比如以众所周知的泰格·伍兹为例,由于“对婚姻的不忠”,遭到逾10家赞助商的撤资,并取消了他的代言合同,甚至停止播出他的广告[14]。由此可见,优秀运动员的道德品质及从事的体育项目决定着赛事产业商业价值的强度和方向。
2.6 PPP运作模式提升了大型体育场馆在赛事产业链中的商业价值
众所周知,在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大环境下,大型体育赛事举办后的大型体育场馆深受体制的制约,竞赛场馆的国有运营机制,造成部分公共体育场馆维护资金严重匮乏,最终导致国有资产的流失与浪费。投资大、回报收益低且周期长的体育场馆不仅是链接体育、社会和个人的重要节点,也是体育赛事产业生态链的重要一环。《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激发社会领域投资活力的意见》中针对社会领域投入平均收益低、回报周期长、抵押融资难等特点,出台专项债券发行指引、商业银行押品管理指引,有条件的地方可设立市场化运作的社会领域相关产业投资基金,鼓励各地通过风险补偿金等措施为行业增加信心,同时,推进税收政策的落实,加大水电气热等价格优惠政策的监督检查等内容[15],为大型体育场馆在赛事产业中商业价值的提升提供了巨大空间,也为社会力量投资提供了新亮点。例如2015年国家发改委建立的PPP项目库中,把深圳大运中心项目列入首批的13个项目中,也是其中唯一的文体行业项目案例。大运中心成功升级后将打造国际体育运动基地和培训中心、华南音乐节胜地、国际演艺中心等。民间资本的介入,将引起公共体育场馆管理机制发生变化,也使大型体育场馆赛后商业价值的提升获得了生机[16]。
2.7 职业联赛备受关注,本土赛事产业发展迅猛
自1992年红山口会议确立以足球改革为突破口进行体育事业改革以来,经过20多年的尝试,诸如中超联赛和中男篮球职业联赛等本土特色的体育赛事备受投资者关注。以中超足球联赛为例,广州恒大为了打造“中国皇马”,先后花费350万美元、320万欧元、1 000万美元、850万欧元、1 000万欧元的代价引进了巴西猎豹穆里奇、欧冠射手克莱奥、巴甲MVP孔卡、多特蒙队前锋巴里奥斯、世界著名冠军教练银狐里皮[17],创造了“中国职业足球联赛的神话”,引起了世界的关注。乒乓球中国大奖赛、斯诺克上海大师赛、网球中国公开赛和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等本土赛事收视率不断攀高,发展迅猛,2016年《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颁布后,社会资本投入热情高涨,体奥动力公司签下5年80亿人民币的中超联赛媒体版权,校园足球方面已经选定了8 627所足球特色学校、38个校园足球试点县(区)和3个综合改革试验区,足球产业链日趋完善。
3 结语
结合上述我国体育赛事产业规范的演进过程及取得的成效,我们不难得出:(1)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所引发的体育产业规范的变革,反映了体育赛事产业规范的演进与完善,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使然与应然。(2)体育赛事产业规范为体育社会组织蓬勃发展提供了保障,并决定着赛事产业发展的方向和强度。(3)借鉴足球产业经验,推广项目协会制和俱乐部制为核心的职业联盟竞赛制度,加强体育赛事产业与其他产业的融合成为深化我国体育赛事产业规范研究的重点。(4)积极扶持社会企业或体育社会组织投入体育赛事产业,是优化社会资源,解决新时代体育产业发展矛盾的重要措施。(5)优秀运动员的道德品质与品牌赛事的商业价值以及PPP体育场馆运行模式成为提升体育赛事产业价值的重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