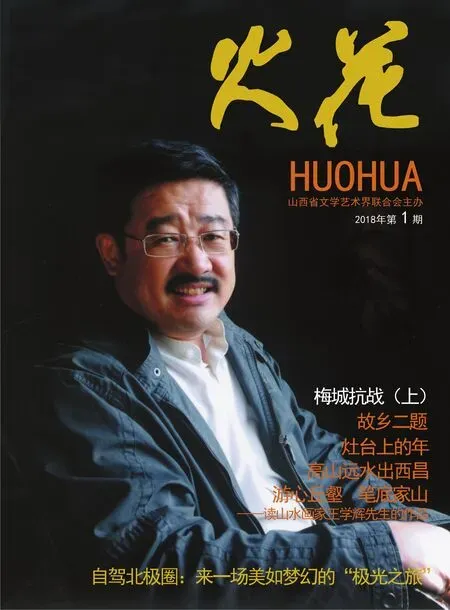黄豆酱
李兴柏
前几日与友人小酌,期间老板见我们唠得十分畅快,瞬时为我们桌加了一盘“大丰收”,内有黄瓜条、尖椒条、小葱段、心里美、苦苣、生菜,又上一小碗农村黄豆酱。忽然想起了在乡下大葱蘸大酱的日子来,过去的岁月,好像仍旧保留着一丝值得回忆的余香。
东北是满族人的聚集地,也是清朝的发祥地。据说:黄豆酱是满族人发明的。满族人在行军打仗时,将炒熟的黄豆背在身上,便于食用。但黄豆被雨淋湿发霉。后来,满族人又把发霉的黄豆弄碎,加进粒盐,几经试验,终于做出来了黄豆酱。
乡间流传一句老话,叫做“忙做忙要记笔账,穷做穷要下大酱”。可见农村人在精打细算、勤俭持家的过程中,酱是不可少的。有一首顺口溜:“烀黄豆,摔成方,悬挂发酵百世香;蘸青菜,调菜汤,舀上一匙油汪汪。”
做大酱要遵循节气时令,一过农历二月二,父亲选好上等黄豆五六十斤,用簸箕又簸又筛,去掉杂质、草棍、石子,再用水洗净,倒入十八刃大铁锅中,加足凉水泡上,盖上锅盖。头一天晚间烧火开烀,大火烧开,小火还要继续烧它一个小时,用余火余温焐它大半夜。烀黄豆添水很关键,不能太多,应稍干点儿。水放多了,如果太稀,做酱块子不好做。
经过一整夜的烀焖,早上揭开锅盖察看,黄豆成了黄褐色,一看就有食欲。舀点熟黄豆,倒入酱油一拌,趁热送进嘴里,那才香呢。
父亲与人把石磨上扇揭开,母亲用热水把石磨和磨盘刷洗干净,把上下磨一合,向磨眼倒进熟黄豆,拉磨几圈后,磨碎的豆渣从磨缝中淌了出来,这叫“拉大酱”。
豆烀得黏稠,不爱往石磨眼里走,必须有一个人站在石磨上,用一根圆柱形、气头的、上有横柄的酱杵子,不停地向磨眼里杵压。把磨碎的湿豆渣一团一团拿到屋内的饭桌上,将其团成块状,“啪啪”摔成不到二十厘米见方,长约三十多厘米,类似小孩睡觉枕头形的,俗称“酱块子”。
母亲用纸把酱块子严密地包上,免得落进灰尘,污染原料。父亲先用八个秫秸瓣放在酱块子四面,一面上下各放一个,免得勒紧破坏形状,防止纸嵌入酱块子内。再用稻草编成“十字花”,吊在通风阴凉的外屋,将其吊在小木梁上,促其发酵。
室内零上十来度的环境,就能使酱块子发酵。两个月后,干裂的酱块子外皮和缝隙里都长出了绿茸茸的细毛。农历四月十八是辽宁中部平原“下大酱”的日子,这个“八”,可能与“发”谐音有关。如果放在以后下大酱,老人们说那将是臭酱。这些说法有何依据,从来没人考证过。人们就是这样,年年按照习俗而做。
父亲取下酱块子,解开稻草绕,撕掉包装纸。母亲用温水刷去绿毛,用刀剁成小块,再用手掰成更小的块儿。
母亲要把酱缸清洗干净,把酱块放进酱缸内,再加入适量清水,用白布盖在酱缸口上,免得苍蝇、蚊虫和灰尘及树叶进入,再用一条细绳紧紧地系住白布蒙缸的周边,最后盖上用秫秸编的“酱斗篷”,防止阴天下雨酱缸流进雨水生蛆。
半个月后,酱要用细筛子过滤一次,小块儿要用手捏碎。俗话说“省了盐,酸了酱”,就是说盐如果放得不足,大酱会变酸。这时要用舌头舔一下,若发现盐量不足,须马上采取补救措施,继续加点盐。
酱在缸里经太阳暴晒,发热会发酵冒泡泡,这时要用酱耙(长形木杆扣住巴掌小的四方形木板)一天打三遍耙,每次得打(搅合)上百下,由缸底向上打动,让盐、水、豆泥融为一体。这个耙的杆与板是隼卯结构,不能用铁钉,防止生锈,否则,易有铁锈味。捣酱会使酱里的气泡消失,促使小块分解,上下大酱翻腾均匀,发酵加速。
好酱是伺候出来的。随着气温的上升,酱的表面会生出一层黑色的泡沫,需用勺盛出扔掉。经过一个多月的晾晒和打耙,把晒过太阳的打下去,没晒过太阳的打上来。慢慢使缸里的大酱由稀变稠,越来越稠,颜色越来越深,香味越来越浓,就变成了焦黄细腻的纯大酱了。
大酱的吃法,可谓丰富多彩,既是烹调用的调味品,更是乡下人最爱吃的开胃菜。大酱是个神奇的东西,甭管辣的、酸的、苦的、涩的菜,一旦蘸上大酱,就变成可口的美味了。农民们吃了大酱,才有力气干活,才能抵挡风寒。
盛夏里,气温高,午饭时,有人将一勺大酱倒入高粱米水饭中,用筷子拌一拌,连吃再喝,几大口就把酱水饭消灭掉,增加了体内的盐分。好家伙,大酱还能兑成防暑饮料。
在东北吃面条,无论是打卤面,还是炸酱面,没人用豆瓣酱,也没人用甜面酱,都用黄豆酱与五花肉丁和鸡蛋相配,炸出的酱那满嘴的香味,使我至今记忆犹新。以鸡蛋酱为例,其做法很是简单,锅内放油,油热放入鸡蛋,将鸡蛋弄散,随后把葱花、黄豆酱倒进锅里加热,可以放入点西红柿丁或辣椒丁,一两分钟之后,香味就飘出来了。土豆炖茄子、土豆炖芸豆的炖菜,人们喜欢用黄豆酱爆锅。油开之后,把浓浓的大酱倒进热油里,油与酱发出滋滋声,香气喷发出来,菜勺把油与酱搅动几下,放进葱花就可以炖菜了。酱香在水汽里蒸腾,满屋飘香。而饭店和家庭里的酱焖鲫鱼、酱焖泥鳅、酱脊骨、酱炒茄子等东北名菜都用黄豆酱来上色和调味。
母亲是做大酱的能手,有人问母亲“做大酱有什么诀窍”,母亲总是笑着说“哪有什么诀窍,做多了熟能生巧”。母亲的话不假,打我从上世纪六十年代记事起,母亲做大酱四十多年,从未中断过一次。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手法,味道自然也有微小的变化,看来做大酱,也有技术含量。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东北人做腊肉也离不开大酱。老家杀年猪时都会切出几块五花肉,去掉肉皮,涂抹上一层大酱,撒上一层用菜刀压过的盐面,用尖刀在猪肉上扎几个眼,穿上细麻绳,挂在通风仓库或木梁上,使其自然晾干,以留到第二年农忙时家中劳力补养身体。经过几个月的浸润,酱料就充分渗透到肉中。因保鲜的五花肉略咸,又都是腊月腌制的,故称为咸腊肉。这种保鲜方法最为简易,在旧时农村也最为普遍。炒炖肉不发硬,嚼在嘴里有酱香的味道。
我们离开故乡后,每次回到父母身边,没等走之前,母亲已把空罐头瓶清洗干净,瓶内已经装满了黄豆酱,盖已经封严,等待我拿回市内。
柔和、鲜美的黄豆酱,伴随我走过了童年、青年时艰难的岁月。如今,我再也吃不到母亲父亲酿制的黄豆酱,可它仍散发着芳香。黄豆酱,似质朴的母爱父爱,那爱,暖心暖胃,齿颊留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