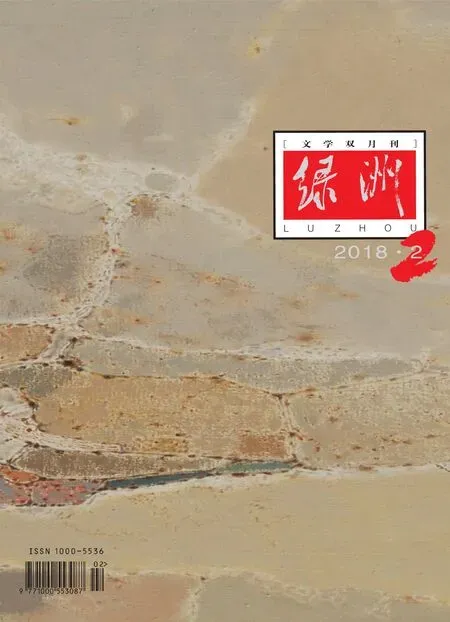阅读的耐心
毕亮
书边的安静
我知兰姆、读兰姆,始于梁遇春。七八年前,大概是春夏之际,我还在兵团的一个最基层的边境连队谋生。连队有间破办公室兼做图书室,平时几乎无人进去。数个书架摆得满满的,地上堆着的也都是书;上面各个口子、部门配发的书,送来拆都不拆就堆在地上。其实,都知道,拆了也没地方放。书多是些农牧养殖业知识用书,教人怎么养牲畜家禽、怎么种麦子油菜。书堆在那里,也是没人看的。我初来乍到,也没多给我安排工作。上班无事,就一头钻进了图书室,在科普读物丛书,竟然无意中发现了一本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的《梁遇春散文》。两个月后,我就调离连队到其他岗位工作。在那两个月里,这本《梁遇春散文》成了我常看之书,也是我看梁遇春之始。
我离开连队时,《梁遇春散文》还在图书室的书架上。现在应该也还在我当年放它的位置上,无人动过吧。也许,图书室已另作他用……
梁遇春二十六岁时便因猩红热离世。而去世前三天,即1932年6月22日,他还在老师温源宁的书房讨论英国作家弥尔顿。后来有一年,看温源宁的《不够知己》,有一篇写梁遇春,在老师温源宁眼中,梁遇春“作风低调、衣着朴素、少言寡语,但“不知为什么,倒比言行张扬以求显达的人更加令人难忘。没有一丝想要炫耀的念头,置身于人群之中,他总是力图避人耳目而隐身在笑容背后。”
因为早逝,梁遇春留下的作品并不多。只要遇到,我也都细致地看看。最近正看的是梁遇春家乡福建出版的《梁遇春读本》。书前有梁遇春的小传,在看时才发现,过去一些年里,看的仅只是文字,对作者的短暂人生,关注得实在不够。梁遇春说他最怕人生的旁观者。我倒是无意中做了一回文字的旁观者。也是在看梁遇春小传时注意到,我初读梁遇春,其时正是二十五六岁的年纪;所以在三十岁以后看梁遇春小传,便忍不住地唏嘘,对其文字看得也更细致了。
据说梁遇春自幼就乐于活在想象的愁苦世界。这样的据说,我是深信的。他后来的作品,和此大概关联不小。
梁遇春的作品,深受兰姆等人小品文的影响,这是毋庸赘言的,如他在谈英国小品文家杰罗姆·凯·杰罗姆《懒惰汉的懒惰想头》时说的,集里所说的都是拉闲扯散,瞎三道四的废话。梁遇春之作,多是这样“拉闲扯散,瞎三道四的废话”,却也让人看得余味难绝。如果不是早逝,假以时日,之后的作品该是让人更加回味吧。这是我三十岁多时的瞎想,毕竟历史不容假设。
如今看书,多是零碎时间的拼接,看《梁遇春读本》,竟然断断续续地用了几个月,在之前,这自是不可能的。我现在每看梁遇春,就很怀念在团场时的安静读书时光。离开以后,就很少再有了。
沈从文的家书
家里有一套《沈从文文集》,十一大本,偶尔也翻翻,常翻的还是捡自乌鲁木齐旧书摊的这本《从文家书》,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的,是陈思和、李辉策划的“火凤凰文库”中的一本。
忘了是哪一年,肯定是来伊犁以后,有一年回乡,在乌鲁木齐转车,中途有点空闲去看同学。结果是,同学未见到,遇到一个摆地摊卖书的,空闲时间就消耗在这里,带走了这本《从文家书》,在火车上翻阅。这本跟我回了趟老家,又从老家跟着我回新疆。随我奔波万里的书,在我书架中,还真不多。有些书是看完就放在老家,下次回去接着看。
书中所收家书前后跨度近三十年。最近一次重读《从文家书》,常是深夜,一个人在台灯下,一页一页地翻看,沈从文、张兆和两个人的三十年就在不到一个月的晚上翻过去了。深夜的边城,寂静,偶尔有几声对话传来,也都是夜归的人。然而,正是这样的夜晚,看着沈从文、张兆和上世纪三十年代的通信,想起来的,却都是沈从文的后半生。这本书中也收了一些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们的通信,从中看出更多的是感慨。
早期给张兆和的家书中,沈从文的敏感以及作为“乡下人”的自卑,在文字中是很明显的。也是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沈从文在湘行途中,给张兆和信中这么写: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地方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放到现在,是要在朋友圈刷屏的。
在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日给张兆和的信中,沈从文表达了“想印个选集“的想法,这也是作者第一次提到印选集,并在信中大致罗列了目录。殊不知,两年后《从文小说习作选》才由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了。也是在这封信中,沈从文不无“狂傲”地“大言不惭”:“说句公平话,我实在是比某些时下所谓作家高一筹的。我的工作行将超越一切而上。我的作品会比这些的人作品更传得久、播得远。”这个观点,沈从文大概一辈子都没变过。十几年后,他在家书中依旧认为,他之前的作品现在很年轻,将来也会很年轻,说的都是同一个意思。距离这封信已经过去八十多年,沈从文也已离世即将三十年;当年他的预言,如今正是现实。
到一九五六年,沈从文在外出途中还会再看看《湘行散记》,并在当年十二月十日给张兆和的信中说:觉得《湘行散记》的作者究竟还是一个会写文章的作者。这么一支好手笔,听他隐姓埋名,真不是个办法。
除了家书外,书中还收了几篇沈从文处于“癫狂”状态中的呓语。其中一九四九年五月三十日在北平宿舍里写下的手记,现在读来依旧悲从中来:“我似乎完全孤立于人间”,“世界在动,一切在动,我却静止而悲悯的望见一切,自己却无份,凡事无份”,“就是我手中的笔,为什么一下子会光彩全失,每个字都若冻结到纸上,完全失去相互关系,失去意义?”,后来我们知道,此后沈从文放下手中文学之笔,转行进入文物方面研究,许多研究成果都是开拓性的。沈从文的转业之谜,也成了沈从文研究绕不过去的课题。此时,再回头看看上世纪三十年代他写给张兆和家书的“狂傲”“大言不惭”,便再也忍不住生气造化弄人的慨叹。如他在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日给张兆和的家书中所言:一只直航而前的船,太旧了,调头是相当吃力的!
沈从文的家书内容真是事无巨细,凡事都“汇报”。一九五六年在长沙,坐船时遇到卖脚湿气膏的小贩,见其口才好、言语顿挫而富于节奏感,认为吸收到博物馆做讲解员必然是一把好手。——沈从文的“敬业”,真是着迷了。
这本《从文家书》出版时,张兆和先生还在世,并为本书留下了一篇《后记》,后记很短,却非常值得重视,她在短文中写到: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过去不知道的,现在知道了;过去不明白的,现在明白了。写这些时,张兆和八十五岁,她晚年最重要的工作是整理沈从文遗著、编辑《沈从文全集》,在《沈从文全集》出版第二年,张兆和以九十三岁之龄与世长辞。这些是在看《家书》时不由自主想到的,忍不住吁叹。
“说说”贾平凹
有一个时期,每天上下班公交车上集中看贾平凹的文章,偶有所想所感,便随手写了发在QQ空间说说里。是谓“说说”贾平凹。
用微信读书软件花了好几天时间看了《贾平凹作品精选》,陆陆续续地看一周多时间读完。之前看过贾平凹两三本书,印象也没多深,从这本开始慢慢看出好的。虽然有些篇幅口味偏重,但总体观之,他的作品是很值得读的。汪曾祺称他为鬼才。继续再找其他他的作品来看看。
一九八一年,贾平凹二十九岁。三十六年后的二月二十一日黄昏,我在公交车上看完他的《哭婶娘》。他写作时心绪的汹涌不定,溢出了文字,三十六年后我读起来还被淹没其中。记得家中有本他的《商州初录》,是他二十几岁三十岁时的中短篇小说集。西安友人文彦群去年送我贾平凹的第一本散文集《月迹》,也是二十几岁时写的。最近越来越觉得一个作家早年的作品应该多读。
三十一岁时的贾平凹写给十八岁的妹妹中的一段:邻居妇人要我送你一笔大钱,说我写书,稿费易如就地俯拾,我反驳,又说我“肥猪也哼哼”,咳,邻人只知是钱!人活着不能没钱,但只要有一碗饭吃,钱又算个什么呢?如今稿费低贱,家岂是以稿费发得?!读书要读精品,写书要立之于身,功于天下,哪里是邻居妇人之见啊!这么多年,兄并不敢侈奢,只是简朴,惟恐忘了往昔困顿,也是不忘了往昔,方将所得数钱尽买了书籍。——这是一篇教人读书之文。
看贾平凹上世纪八十年代写的散文,文后多标注详细的日期,我常见有“草于病房”字样。那时候,贾平凹也才三十多岁,身体多恙却还勤于写作。“草于病房”不是集中出现在某年的某个时期,而是不同年。不知近年身体状况如何,但这几年时有新作问世,有些还是长篇。想来身体应该还可以。想想八十年代,电脑写作还未兴起,贾躺坐病房,或写作,或为文。那期间的小说我还未集中读,写于病房的应该也不在少数。他的文章风格形成,和他的身体脱不开关系的。
和友人谈及贾平凹时,我说:我现在才开始意识到,能用大白话写文章,再寻到合适的词,如此,我觉得就可写成好文章了。贾平凹的师承,还是中国文学的传统。但是,他真是才气逼人呀。我看他三十一二岁时写的一些评论和序言、散文;才气显露无疑。但是也可以看出比较明显的雕琢痕迹和刻意为文的痕迹。这也是看他的早期作品的感受。有这样的印象是看他早期散文留下的,小说还未读。
看贾平凹的《哭三毛》《再哭三毛》,他写得很动感情,这种感情他也没收敛,看文后写作日期便知道,他是在情绪激动不平时匆匆而就的。所以感情满溢得厉害。我在看这些时,常注意他人不太注意的,由此也生了一点感慨。三毛能那么快地收到贾平凹的信和赠书,二十多年后的现在简直不可思议。三毛一九九一年一月一在台湾写的回信(寄出时间不清楚),贾平凹一月十五日就收到了,这在现在的邮政好像也做不到,那个年代是没有快递的。
贾平凹的《孙犁论》写得好。好在他懂孙犁。贾平凹一走上文坛,孙犁就给予了很大的关注,写过贾平凹的短论。贾平凹好像还在孙犁家里吃过饺子。熟悉孙犁性格之人,都明白这是不容易的。贾平凹的第一本散文集《月迹》在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不知可有孙犁之功;但应贾平凹之邀,孙犁给书写了序,这是1982年的事。这年贾平凹三十岁,孙犁六十九岁。二十年后,孙犁去世。《孙犁论》写于1993年,孙犁肯定是看过的。贾氏此文篇幅虽短,但多是知人之论,睿见很多。后来看孙犁女儿的《布衣:我的父亲孙犁》,书中提到,孙犁生前对这篇文章评论甚高,他对女儿说:“贾平凹出手不凡,一语中的,一句顶一万句。九三年那么多人写我,数他写得最好。”我们现在知道,以《废都》发表为界限,孙犁和贾平凹之后似再无交往。近十年后,孙犁去世。
看完《安妥我灵魂的这本书》这篇文章后,我又返回重看了一遍。这是大名鼎鼎的《废都》的后记。《废都》写于1992年,大概贾平凹把自己关屋里正写着呢。后来,他的一篇散文,记得是《丑石》还是关于桃树的文章被选入了我们的语文书里,供我们学习、背诵;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记得清楚的是,有一位比我大几岁的邻居还是谁,给我说,贾平凹这个人是写黄色小说的。这个印象,我至今记得深刻。当然,多年后,我知道他说的黄色小说指的就是这本《废都》。我唯一一次看《废都》,是大一还是大二,书是从图书馆借的,黄土色的封皮,就像三秦大地黄土高原。图书馆的这本书应该是被人借过多次的,中间还有几页被撕了。我也是匆匆翻过,大概也是一解早年的好奇。对贾平凹的这篇《后记》是一点印象都没有。现在距离这本书写完,已经二十五年过去了,一个当年出生的孩子也该成家或者已经成家了。贾平凹在《后记》里说,“我便在未作全书最后的一次润色工作前写下这篇短文,目的是让我记住这本书带给我的无法向人说清的苦难,记住在生命的苦难中又惟一能安定我破碎了的灵魂的这本书。”贾平凹大概也没想到这本书带给他的更多的苦难是在出版以后。
贾平凹在给彭匈的《向往和谐》写序,最后提到汪曾祺,“手稿还堆在案头,未来得及给彭匈去信,却听见汪曾祺老先生在北京病逝的消息,真是如雷轰顶,闷了半日。”谈到他们的南游,当年汪曾祺和贾平凹参加笔会,放着大宾馆的酒席不吃,跑到街巷去吃小吃。看这篇序的写作日期“1997年5月23日”,那时,汪曾祺去世刚一周。当年一起吃小吃的人已经走了二十年。后读到王干的《夜读汪曾祺》,在第一三二页见一帧彭匈、汪曾祺、贾平凹的合影,那时他们都很有精神,现在贾平凹也活到了当年跟汪曾祺一起吃小吃的年龄了。
《给尚X的信》,必将是贾平凹作品中最不易被忽略的文章之一。文章主要围绕给他带来“巨大的荣誉和羞辱”的《废都》获法国费米娜文学奖来展开,中间的过程让二十年后的读者读起来还依旧唏嘘。《废都》出版后,引起了巨大论争,后来遭禁二十年。当贾平凹获得法国这个文学奖时,新闻媒体播报而不提《废都》之名,贾平凹、穆涛等人写的新闻通稿中说“中国作家贾平凹的一部长篇小说(《废都》)荣获“法国费米娜外国文学奖”。”,“之所以在稿子中将《废都》写入括号内,即担心有的报纸不敢使名字出现,便可以删去括号而不影响原文。”真是用心良苦。。研究贾平凹,尤其研究《废都》的出版史,这是一篇绕不过去的文章。
《废都》越往后看,越觉得有问题。是作者意淫过度抑或其他的?也越来越粗俗。当年孙犁看中贾平凹,也很欣赏贾平凹,《废都》前后,孙犁和贾平凹逐渐疏远,对此天津的张莉教授有过比较长的论述,我比较认同。看过了《废都》,偶然地想,如果写成中短篇可能会更好?
贾平凹在散文集《天气》的序言中说:读散文最重要的是读情怀和智慧,而大情怀是朴素的,大智慧是日常的。这本《天气》几年前曾买过一本,看过放在家里,也不知隐在哪个角落了,这次用微信读书再看。贾平凹自己交代: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一些人说我散文写得比小说好,我说那我就不写散文了,专门去写小说。三十年过去了,我集中看过我一些他的书,还是觉得他的散文比小说好(并不意味着他的小说不好);尤其中年后的散文,大道至简。当然,贾氏自己对这期间散文也是满意的。书中有些篇目,看过了,又倒翻回去再看一遍。
看《浮躁》常想起沈从文的边城,不是因为都写了少女撑船。这种阅读感觉很奇怪,也很强烈。记不得在哪里好像看过,贾平凹从自言受沈从文影响,不知这种阅读感觉是否对应着老贾之言。然而,《浮躁》看到后面,也是有个人物叫“翠翠”,只是不再是沈从文的翠翠。初看《浮躁》,感觉应该是贾平凹早年的作品,看至最后,作者写明了时间,一九八六年,当时贾平凹三十四岁。后来便网上搜了下,出版时是在一九八七年。再多看了几个网页,拿《浮躁》和《边城》比较者,甚多。
因为近日集中看贾平凹,便把家中那本破旧的《商州初录》翻出来重看。书是从本地旧书摊买的,买回来放了几年。初次看还是在两年前,犹记看《小月前本》时的感受:此为贾平凹三十岁时的作品。正是我现在的年纪。许多时候是越看越绝望。
《心迹》(四川文艺出版社)里许多篇目以前没看过,或者看过没留下印象,但这回看,仅前面一些篇章,就被镇住了。这个老贾啊,怎么就写得那么好。当然,书中也有不少早期到底流于技巧和痕迹,不比中年后无迹可寻的自然。然而又一想,如年轻时无痕迹无技巧,又该如何渡过年轻?如此想,瞬间变得释然。
几年前,跟着鲁迅文学院到陕西去社会实践,共待了七天。去了西安、黄陵、延安等地,几年过去了,对看过的风景,几无印象了,记得清楚的是三秦大地的吃食,至今真是难忘,常常怀念,还想再吃。看完《心迹》后紧接着看的是贾平凹的《舌尖上的西北》(武汉大学出版社)。看得直吞口水,书中所写,有些我吃过,更多的是没吃过的。吃过的,没吃过的,都想吃。看书时,又想起了陕西之行,那次回来后也写过几篇饮食。那时没看到《舌尖上的西北》,如看了,我的那些小文大概是不会写的。
作为休息的阅读
我大概受汪曾祺的影响越来越深了。写作的风格自不必说,连看书也受他影响越来越大。和他一样,我也变得开始喜欢看杂书。前几天路过一家旧书店,拐进去逛逛,遇到一本《新疆蚤目志》,厚厚的,随手翻翻却也看得有味,便买了回来,和汪曾祺常提到的《植物名实图考》放在一起,随时翻阅。
年轻的时候,看书喜欢追求有阅读的意义,追问阅读的意义。只是至今都还说不清楚什么的阅读算是有意义。二十岁的时候,从图书馆借了一套上下册的《名家谈读书》,翻来覆去地看,寻求他们说的读书的意义、趣味。这套书翻来覆去地看了几遍,谈的多是读书的经历,没发现多少读书的意义,却对每个作者提到的书,认真地作了记录,成了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的购书指南。这套书也成了我在图书馆所借不多的书之一。
尽管爱默生曾说过:图书馆是个魔法洞窟,里面住满了死人。当你展开这些书页时,这些死人就能获得重生,就能再度得到生命。但我不喜欢在图书馆看书,也很少从图书馆借书看。
我买书,不为藏,只为看。所以家里的书,珍贵的版本少,都是自己爱读的书。书房就不提了,客厅的沙发、电视柜,卧室的床头柜,暖气包,背阳面卧室的窗台上,堆得到处都是书。很多书,抓起来就看,看得常常走神,却也乐在其中。
读书,也使我在浮华社会变得安静。任他外面世界多热闹,我自拥书而度过春夏秋冬。“饥读之以当肉,寒读之以当裘,孤寂读之以当友朋,幽忧读之以当金石琴瑟也。”这是宋朝人说的,我还远远未有此种感受。但,读书,改变了我的生活是毋庸置疑的。读书,挤占了我的时间;家里的存书,也在不断地挤占我的生存空间,却也不觉得苦,反当是一种享受。再忙再累,一册在手,烦恼自走。如此,阅读给我的已经足够多,比想象中的还要多。
作家张宗子说,同样一本书,二十岁时读到,和四十岁时才读到,意义不一样。我还没到四十岁,但也常有这样的感受。读书的意义,对于不同的年龄,肯定也各自不同。在看到这句话之前,我曾在一篇读书随笔中如此写:年岁渐长,许多以前读不进去的书,现在一读,滋味绵长,余味长存。“咽一口酽茶觉得爽快,这是大人的可怜处。”,这是周作人喝苦茶的经验,我读书,也是如此。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看书时习惯喝一杯茶。书不离手,茶不离口,茶中滋味长,书中岁月短。看书,于我,大概成了一种习惯,一种不可缺少的自然而然。
我的看书,很多时候是一种休息,而且还是一种很好的休息。因此,我看书也很少正襟危坐,怎么舒服怎么读,躺着读书是经常的。阅读时的身心是最放松的,读时偶有所获,或记在纸上,或记在手机便签中,几本书看完,所记的内容稍作连串,即是一篇随笔。我的许多读书随笔,都是这么写成的。
小说家的心事
看过了毕飞宇的《牙齿是检验真理的第二标准》和《写满字的空间》后,便迫不及待地想找他新出的《小说课》来看。好在前几日逛书店见书架上有便买了回来。应该说,前两本书为我看《小说课》,做了不少课前准备;所以“听起”小说课来,滋味绵长,回味良久。
曾在某杂志上看毕飞宇分析汪曾祺《受戒》的文章。那篇分析文章不短,一口气看完又接着一口气再看了一遍,看完长吁了一口气,接着又长叹了一口气。写得真好,服!汪曾祺的《受戒》写得真好!毕飞宇的《倾“庙”之恋——读汪曾祺的〈受戒〉》讲得也真好!作为一名钟爱汪曾祺的读者,我也曾读过多遍〈受戒〉,然而对照毕飞宇的解读,我如同没读过。
这篇谈《受戒》的文章被放在了《小说课》正文的最后一篇,却是我看《小说课》中的第一篇文章。然后看的是海明威的短篇小说《杀手》。看之前,把《杀手》网上找出来重新看了下,再看照毕飞宇的解读,发现毕飞宇之所以为毕飞宇,他在以作家这个身份来解读这些经典时,用的是自己写作的实践经验,如他自己所说:“就是想告诉年轻人,人家是怎么做的,人家是如把‘事件’或‘人物’提升到‘好小说’那个高度的”。
在一次访谈中,毕飞宇坦言,小说家最要紧的,第一站在哪里说话,第二,面对什么说话。在《小说课》中,作为小说家的毕飞宇的每篇文章似乎都是在做同样的事:被解读文章的好以及为什么好。此刻,他站在讲台上,面对的数百上千的听者、读者。看了这些文章,忍不住心里默默念叨了句:毕飞宇,真是中国好读者。可是,毕飞宇在《刀光与剑影》中说过,阅读是需要才华的。当我看到这里时,回想了看《受戒》的经历,原来我的“如同没读过”是没有才华的表现。紧接着的半句话是:阅读的才华就是写作的才华。也因此,我感觉一个初写小说的人看了《小说课》,要么悟有所得,越写越好;要么再无勇气动笔,像毕飞宇分析的那样,努力做个好读者也说不定。
作者解读的几篇作品里,《促织》《故乡》《项链》等几篇(包括《红楼梦》《水浒传》中的部分章节),都是在中学语文课本上学过的,那些年纠结于作品的时代背景、段落大意、中心思想。在读《促织》时,我们的眼睛多少次一滑,就滑过了“夫妻向隅,茅舍无烟”这8个字?在学习《项链》时,有多少老师或学生会注意到小说中的契约精神、忠诚?在学习《故乡》时,对杨二嫂、闰土的分析,又是怎样大而化之。
那些年我们在课堂上错过的精彩分析,在毕飞宇的《小说课》里重新找了回来。他解读鲁迅时,如此简洁明了:一部中国的现代文学史,其实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一个部分是鲁迅,一个部分是鲁迅之外的作家。在中学语文课上,在大学专业课上,有哪个老师会如此分析鲁迅?在中学语文课本里,蒲松龄的《促织》和鲁迅的《故乡》都是要求全文背诵的篇目吧,有哪个语文老师会这样分析解读作品?恐怕不多。尽管毕飞宇说他可以“武断地说”:每一个好作家的背后最起码有一个杰出的语文老师。好老师可以呈现这种好,好学生可以领悟这种好。
毕飞宇解读的许多好,我这样“一个不会读小说的人”,真是无法体会。至此,我总算找到写不好小说的原因了:“人家的小说好在哪里你都看不出来,你自己反而能把小说写好,这个是说不通的。”
看过了《小说课》,赶紧把毕飞宇解读的那些小说找来重看。看时发现思路自觉不自觉地跟着毕飞宇的分析走。这是阅读之悲啊,被牵着鼻子走。尽管小说阅读是一件非常个人化的事情,但或许如李敬泽所言,天下的坏小说总是一样的坏,天下的好小说却各有各的好。毕飞宇的小说课,说出的只是他认为的好,讲的是一个小说家的心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