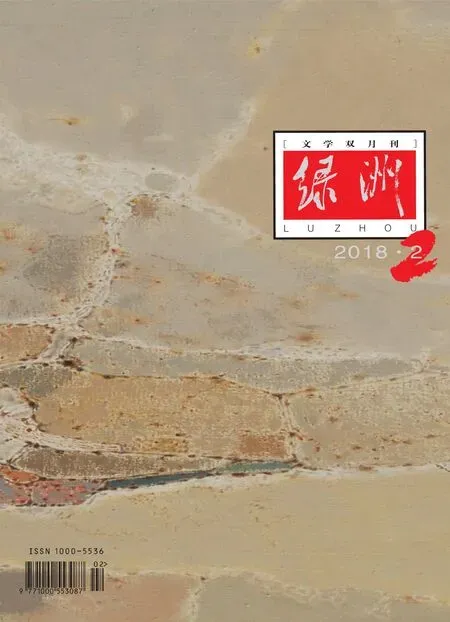星城记忆
苏亦薇
木 桩
文庙街不认识刘老头,刘老头很熟悉文庙街。
刘老头每年秋冬时节在文庙街卖烤红薯,一卖就是七八年。看着客人递钱时仍盯着手机的双眼和行色匆匆的背影,他明白,就是再卖上七八年,他仍然是文庙街的陌生人。
这座城市的冬日漫长酷冷,但刘老头每天都会诚恳地缓缓推着他烤红薯的铁皮车子,出现在昏暗的晨光中。那时辰,路灯通常还没有熄灭,他坐在暖黄的灯光里,不吆喝,也不像其他商贩那样把钱盒放在趁手的位置,连人带车像一棵古老又踏实的木桩,不粗壮,但足够稳妥。
刘老头以前是个教师,每月有退休金;他儿子很出息,在一个大城市工作,每月汇来的钱足够让他活得更安逸。亲戚朋友没人明白他干嘛非得寒冬腊月里跑到街边卖红薯,隔三差五会有人苦口婆心地劝他回家享福。对此,刘老头只是报以微笑,就像他每卖一个红薯也都会对每个顾客微笑。
绝大多数顾客无暇看他那一笑。偶尔会有人的眼神对上那笑容,他们会一愣,然后匆忙离开。
“这老头子就是犟噢!”亲友看到他这笑呀,便明白说再多也无济于事,于是刘老头就那么在文庙街日复一日地卖烤红薯。
偶尔走进街内的我,感觉刘老头摆弄那些烤红薯的样子,很有些“写意”——小铁皮车子擦得锃亮,车身被细心地分出了许多许多小抽屉,抽屉里躺着红薯,既不沾马路扬尘,又能借炉温加热。
刘老头侍弄烤红薯,像是在安抚自己的孩子。他顺着一种小曲儿似的奇妙韵律错落地打开那些抽屉翻动那些红薯,时而捏一下;那烤炉是烧柴的,他细心地把木柴分成小把小把,隔三岔五放进炉膛,从来不一次扔一大把。
烤红薯摊边偶尔会跑来街口小超市店主的孙女,小姑娘约摸六七岁吧,长得不算漂亮,但那双大眼睛总泛着亮丽的水光。她是很少能对刘老头的微笑回报一个大大的笑容的人。刘老头慈爱地看着她,他总觉得这小姑娘专心啃红薯的样子,像一朵大晴天里的铃兰花。
“爷爷你为什么不把柴一次性都加进去,多省事啊?”小姑娘奶声奶气地问。
“小宝贝儿呀,一次性全加进去火太旺,烤糊了就不好吃喽!”
很多时候,刘老头叹息除了这个小姑娘,很多顾客好像并不在意口感。自己生意之所以还算过得去,是因为那七八年都没有涨过价的烤红薯用来充饥,又省钱又节约时间。
刘老头用心地这么做,他觉得自己像个老得一塌糊涂的木桩,已经没法再向上长了,但根部仍然紧紧抓着深深的土壤;他想为高楼鳞次栉比的城市和匆匆来往的人们,用最质朴最平凡的烟火味道,添个有温度的生活细节;他想用深埋炉膛里的火星,把时光里那点情感留得久一点,再久一点。
他觉得自己还是个老师,课堂是陋巷,教具是红薯,教学表达是微笑,如果能被感受到,就算功德圆满。只是,他的多数学生意识不到有人在教他们。
那些深冬的晨光里,刘老头总爱盯着炉膛里飞出的火星看,那么小小的,耀眼的,滚烫的一簇,飞出短短的一段距离后,泯灭在呼啸的北风里。
刘老头感觉到在自己心口也有这么一团炉火在燃烧,火苗来自遥远的过去,不断地有火星飞出来;他是馈赠世人火苗的木桩,扎根在温柔的土壤里,盼望着耀眼的、小小的、安和的、滚烫的火星,飞得远一点,再远一点。
老 巷
从小学到中学的很多日子,我总是住在外婆家。那儿周边有很多很老旧、很老旧的房子和院子,外婆家院子南侧和另一个紧挨着的老院子之间,挤出了一条深深的老巷子。
巷子在地图上没有名字,我们院的人管它叫南巷。我很少走进巷子,但它却总像陪着我成长。从我书桌前的窗口恰巧可以俯视它,聆听孩童的欢闹声,摩托车启动的马达声,三轮车的吱呀声。妇人晾衣时敲打铁丝的声音和老头儿高谈阔论的方言乡音,伴着我长大、长大。
不消走近,光是闭上眼睛,我就可以细细地为你描绘出老巷砖瓦里夹着的鲜绿青苔,烟囱里残留的旧时光油渍,砖壁上斑驳的深色水痕,水泥门槛边斜靠着的老式生锈自行车……
偶然一个初秋月圆之夜,我走进被月色和灯色染成橘黄的老巷。那晚空气很透,微风中融合着草木味。月亮很薄,很轻地贴在樟树浓重的阴影下面,那些亮堂而皎洁的光华从小而密的叶片中漏下来。
巷子粗砺的石墙边,一位老妇拄杖而立,晚风擦过她瘦削的肩膀,衣袂飘飘。老妇的脚边,突然不知从哪儿溜出一只小白狗,一个劲儿地用爪子扒着她的裤脚。月光从天空的角落里倾泻下来,透过茂密的枝叶与清澈的空气,零散地摆布在老人和小狗身上。妇人眼神在月光的润泽下充满生机与暖意,她费力弯下腰认真抚摸着小白狗,借着月光一绺一绺细心为它挑去毛发间横七竖八的落叶枯草。小白狗很安心地蜷曲着,不动,不叫。我知道,这是生命与生命的交流……
从那天开始,我儿时思绪每次天马行空总是以南巷为起点。多少次,快活地盯着那狭窄的麻石路凝望,想象力顺着它开始弯弯绕绕至我再也看不见的地方,之后的世界便是无限冥想——那里有茂密的森林,悠长金块铺就的小路,坐落在深海的城邦和一天能够看33次日落的黄金岛。那是最惊人的、无忧无虑的“奔腾年代”,我最生机勃发的创造力埋藏在那里。
我就这样用这种童话般的方式守着南巷,直到,我渐渐地因为学业太忙碌忘却了它。
再后来,南巷被拆掉了。那天,没有阳光,天色却足够亮,足够让我看清废墟和空寥的荒地。那条幽深的巷子,先是失去半边臂膀,继而半边身躯,最后完全消失。
我没有作出太多反应,我也不知道该作什么反应,只是为童年冥想中那座能看33次日落的黄金岛叹了口气。
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巷子后楼房对着大街,大街对着楼房,我越来越感觉城市被隔成一个一个越来越独立的单元,铁门之间彼此缺乏交流,思绪因为单调和缺乏延伸空间会在一潭死水中缓缓下沉。
南巷的风物,让我学会放飞梦想和与其他生命共鸣;南巷的消失,像是将我的未来划开了一道巨大的口子。我知道,我得乘着小船奋力向前划,溯游而上,逆水行船。但岁月的流水啊,总会把我的思绪带回南巷,这是我的乡愁,无比深刻,无比执着。
烟 花
我所在的城市,每逢重要节日都会在江上一座沙洲燃放烟花。江边一处餐厅靠窗那溜餐位,恰好正对着沙洲,最适宜观赏烟花。
在提前好几天定下的位子落座,我隔着巨大的落地窗,可以清晰看见头尖、身长的黑背乌篷船缓慢地驶过江面,划出鱼尾似悠长、柔腻的波纹,一片水光潋滟静静地、静静地张开。有微风,涟漪显得繁复;有灯火,城影变得璀璨。
耀眼哟,耀眼哟……
周遭不知不觉围上了好些个捧着相机的人,看得出,他们彼此之间并不相识——但这并不妨碍当他们看到这个观景“广角”时,眼中跃动出一模一样的欣喜。他们大多是退休者模样,容颜老去,容光仍在。
我很久以前也曾深爱摄影,沉迷于用镜头记录生活。在我看来,这儿玻璃很厚,不算干净,距离也有点远,其实不适合拍照。可这些人毫不介意,礼貌地询问能否在这个地方拍照,随后熟练地架设机器。
那一刻,我便觉得,他们不是来摄影的,他们是来生活的。
室内暖气温度开得很高,即便没穿外套也能感到浅浅的一层燥热。他们也在脱外套,却并不挂到衣帽架上,而是盖在支着三脚架的相机上。
然后,对岸亮堂起来。
起初只是火树银花的轻描淡写线条划破夜空,渐渐飞旋、升高、绽放,变成雍容的花朵,像是美的新世界中经历过精挑细选的精英,荟萃在隔岸的沿线。
那夜的烟花,一举一动都完美,远方连绵的群山,身边深沉的夜幕,青烟蔓延,夏花掩映,华彩怒放,大地在轰鸣声中颤抖着复苏。
我和身边的人群开始激动欢呼,进而放声尖叫,气氛一浪接着一浪升温!当五光十色向你扑面而来,整片江面都像是被点燃似的闪烁、照亮、渲染起来时,餐厅里只剩下热情的血液在翻滚!
耀眼哟,耀眼哟……
突然,我发现有人没动。
是的,在近乎失控的人群里,有人没动,就是那群摄影师。他们用厚实的外套遮住那块反光厉害的玻璃,将身子探了进去。
在烟花燃放的二十分钟里,他们一直是这样弓着背、猫着腰,手不断移动着镜头,调节机器,按下快门。只有烟花炸响、人群欢呼的间隙,才能听见他们透过棉衣传来兴奋的低吼,能看见三脚架下滚落的汗珠,隔着江,隔着路,隔着玻璃,与那头的炽热交相呼应。
耀眼哟,耀眼哟……
不知为何,我脑海中回响着《格言诗》中的句子:“知道为什么亲吻的时候要闭着双眼吗?因为彼此都太耀眼。”
这一刻我明白,其实他们不是来生活的,他们是来专注生活的。他们年华正步入迟暮,容貌和健康正在老去,但他们举手投足间,有的是很多年轻人都没有的张力——纵使在这一刻整个世界都崩塌下来,他们的世界,也是相机镜头中的视觉盛宴和无边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