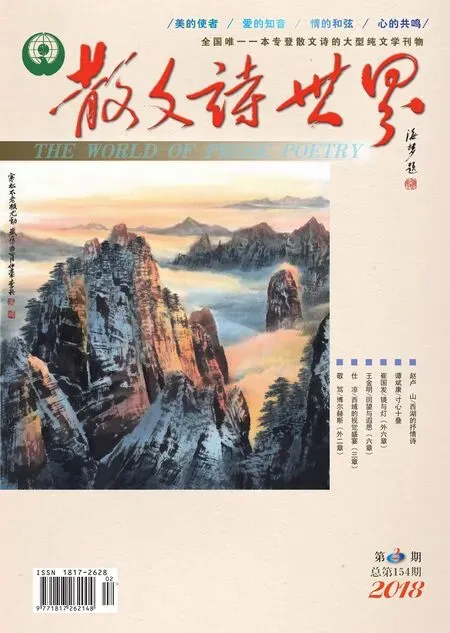┃小镇轶事(二章)┃
2018-11-21 08:17湖南益阳第六中学高中部沈隽永
散文诗世界 2018年2期
湖南益阳第六中学高中部 沈隽永
潋 滟
山的绿如墨洇开,然后,与江水汇合。
而我伫立在棚改区的另一头。放眼望去,是拆迁旗帜的鲜红。宛若风马旗,将寂静拓印在了经文的轮回中。
我在轮回中聆听着潮水声声,与小镇的自己相逢。却没忘记,潋滟中那是身着素白裳的尼姑招来的苦涩。她曾经被迫蛰居在朱红的庙宇里,披上长袍,削落满头青丝。从此,她与眉目慈爱的佛相伴,一待,便埋没了整个韶华年暮。甚至,连她近在咫尺的女儿都想认不得。只剩下一管唇膏作为念想。谁让人与佛一旦牵扯,七情六欲,只得放手。
可那时的孩子不懂,不懂人与佛的交战,也不懂一管唇膏的内幕。只觉得,新鲜物什是她可以从乡土抵达摩登的船舶。于是佛说,偷窃的罪孽犹如暗流……
如今,在虚与实的光景外,我思至此,心不由得被潋滟的苦涩淹没。
野生香蒲
总要有风从水面拂向河滩,睡在我的臂弯。植物女子嗬,我把自己化作野生的香蒲,与似飞白书的大雁群在夕烧下吻别。暮色四合,我便把伸出来偷懒的根须重新扎进土壤,目睹暂住在桥洞里的流浪汉用半截粉笔在水泥地上书写着小楷。一旁草花覆盖着的碎石说,他是被十年禁忌贬入波月洞的黄袍怪……
但仍愿将生活当诗。就连桥下的算命先生手捧易卦、候在巴掌大的板凳上的模样,都有一种静笃的仪式感。而我疯长,却淡然。日复一日,直到奶奶携带她的猫走来。她轻轻摘下我的叶,说,满崽,我们回家。
恍然大悟。原来小镇的人啊,不管以哪种方式,终会回到小镇。植物女子嗬,我将融入一缕末夏,成为奶奶手下系着长命缕的蒲扇。蒲扇的一端,是小镇;一端,是现在。——野生香蒲,摇晃在这方言的人世间。
猜你喜欢
散文诗世界(2022年4期)2022-04-08
华人时刊(2021年17期)2021-12-02
科教新报(2021年2期)2021-05-17
少儿画王(3-6岁)(2020年8期)2020-09-13
科教新报(2020年26期)2020-07-31
学苑创造·B版(2019年11期)2019-12-05
东坡赤壁诗词(2019年5期)2019-11-14
阅读(中年级)(2019年8期)2019-10-08
小天使·一年级语数英综合(2019年5期)2019-06-27
小小艺术家(2018年1期)2018-0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