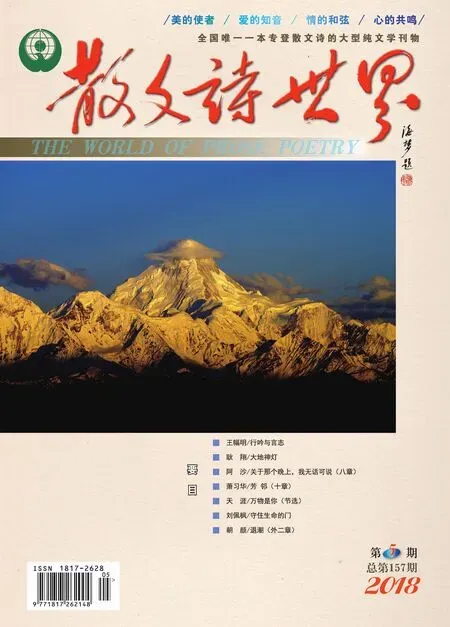《水的声音》:水之思与存在之叩问
——清水的散文诗简评
甘肃 王小忠
《水的声音》是一组纯粹、纯净的散文诗。它意境澄澈,思想透明,意象纯粹,语言纯净。它的本质如此之“纯”,以至于使人除了只能静静阅读、欣赏之外,而无法对诗本身言说什么。就如同你面对一杯纯净的水,一时无话可说,如同你面对一个赤裸的灵魂,词语成为多余之物一样。面对这样的沉思与冥想,我们最好的沟通方式也是跟着她的文字一同进入沉思与冥想,而不是阐释。
诗人清水著文似乎很少,而当我面对她的这组诗时,我只好从她的诗中走出来,打破自己的冥想,走出自己的沉思,写下自己的这些零碎感想。我知道这些声音只是属于自己的,就像水杯外面的一些喧嚣与噪音,它无法进入“水”中,无法与她的“水”的世界中那希声的大音进行交流对话,更不可能改变她的“水”的流向。
《水的声音》是一种典型的海德格尔式的“思”物的产物。诗人由对物的凝视冥想,进入一种纯粹的“存在”之思。这个被诗人用心灵凝视的“水”,是一个源始的东西,它创造万物,催生新的东西(包括在诗人的心灵里源源不断涌现的那些东西),显现被我们所熟悉的物质世界和工具逻辑所遮蔽的事物。在这些新生事物的包裹和托举中,诗人获得了重新审视自我的来路和“存在”之意义的一个根基。由此,诗人在水、日常生活之间掘出一个诗意、审美的第三度空间。这是一个纯粹的诗思空间,在这里,诗人把当下的日常生活的喧嚣和烟火气息隔绝在外,诗中没有出现任何与诗人置身其中的那座国际化大都市有关的任何意象,哪怕是蛛丝马迹。也没有出现任何个人日常生活的痕迹。她隔绝了日常生活的气味、气息、声音、色彩,而保持了她的意象的纯净、诗思的纯粹。这样,诗人也完全放弃了叙事。如果要说这一空间与现实生活有什么关联的话,那也是一些时间性的事物,久远的事物,比如故乡、往事,比如生命意识的来路与归宿。这是一座因为在现实中无处安放,而建在空中的诗思的花园。
诗人的心灵一直在几条思绪上游弋。一条是对“水”的寻踪、追随与追溯,与水的对话。在这一条路上,诗人也与鱼群、花卉、草木对话:“我看见时间之手渐渐破开水的纹路。遥远而神秘的水域,你从哪里来,又往何处去?”(《风轻叩桥面》);“为了取一些干净的水和桑叶,我跟随迁徙的鱼群,渡过了三条大河。”(《途经的水》);“下一个季节来临,河水开始变得清凉,它们又会无声无息地回到原来的地方。”(《静默的事物一无所获》);“一些水驮着月亮涉风行走。”(《旅程》);“川杨河日日夜夜向两岸诀别前行,一个黑夜又将过去,一簇火焰又将燃起。”(《旧物的火焰》);“河流下沉,河流也向上缓缓生长。河水拥有着巨大的幽深的寂寞,现在,你马不停蹄,要去向哪里?”(《雨意》)“远去了。/玫瑰在更远的地方秘密开放。我热爱的湖水去意已决,无法挽留。”(《无法挽留一片湖水》)……在这样的诗句中,“水”是一个与时间俱生的、同行的精灵,它穿过大地,穿过爱恨,穿过命运,穿过生死,独自幽暗前行,无始无终。而在流经的大地上,“水”包裹着一切,创造着一切,“水”开拓出一个更大的世界,那是一个与水息息相关,共生共荣的世界:泥土、青草、鱼群、野鸭,清新的空气……“那颤动的水影忽闪在一棵云杉树上,叮咚作响。”沿岸的风景,生机蓬勃,恍若一个江南水乡的时空,其中鲜花开放,草木茂盛,水汽氤氲,诗人给我们呈现的是一种葳蕤、细密、绵长的南方式抒情。
而在对水的形态进行时间性的沉思、冥想与追问之后,引出诗人对于水的品格的深沉的“存在”之思。组诗《彼岸的水声》中的十章,诗人集中叩问了水的有形与无形,水的弱与强,乃至水的美德。无疑,诗人将水人格化了:“水,在很远的地方流着。面容纯净。姿态优美。”“致虚怀,守静笃,是水的美德。”“一些水,淡泊。宁静。它们是真君子。”“除了身体洁净,灵魂剔透。水,更有着深邃的生命的本质。”这个被人格化的水的形象,从一个自然的人,到一个文化的人,从一个单纯、美好的人,到一个孤独、深沉的人,这个形象在不断地演化、深化。在第九章里,诗人将水比为孔子,梭罗,而从第六章中对《蒹葭》意境的化用:“苇丛起伏,水清烟波处的小洲,已是灵光氤氲,宛然在目。谁在梦里恍惚而来?”我们更愿意将这个被人格化了的水看作是诗人的化身。在第七章中,诗人也讨论了水与人的关系:“水以其大慈大柔滋养了人类。人,却离水越来越远。”在现代工业社会,的确如此,人与水是冲突、对立的关系,人“掠夺、玷污”水,水忍着被玷污、屈辱的悲痛,逃离或者流浪。
这一组诗有内在的节奏、起伏、旋律。诗人的抒情和思考在不断延伸、深化,在中间部分甚至有激烈的隆起,到最后一节,又复归平静:“一只陶罐。盛满了一条银色的河。”“彼岸啊,水声很近。也很远。”这是一种巧妙的控制还是神示般的暗合?诗人的思绪竟然也有着水的形态和节律。
另一条思绪是对隐约可见的故乡、往事、亲情的追忆。诗人试图通过“思物”而踏上返乡之路,重新回到那段时光之中。试图通过对“旧物”的气息、光芒、温度的摩挲,唤醒往日时光的质感。“在无数个明媚的、孤独的时光里,有我幼年细小身体里爱情的羞怯和离别的伤愁。”(《旧物的火焰》),“旧物”是一个串联起整体意象与情感的词,它包括旧的事物、时间、人、感情,还有记忆。“黄昏的时候,父亲独自在小树林。黄昏的树影延宕于寂静的风……晚歌散入夜色。我看见父亲的脸,那长久注视清凉的星星的眼睛。夜的影子落满在他的身上。”“光线微微倾斜着坠落。那些香樟,含笑,木槿,石榴。那些桑树,海桐,海棠,栀子。银白色的鱼和果实倾斜着坠落。”(《无名河》),诗中把岁月以及岁月中的事物都看作一条河,这是一条无名河。而诗人对于故乡与亲情所有的回忆、思念、留恋、怅惘,都在“无名河”这个意象中得到了释放与托付。
诗中还有一条思绪,是对“自我”的审思。作为一个远离故乡(我只是从诗意中揣测)、寄身于都市的现代人,诗人还试图给自己无处安放的隐秘的激情和丰沛、敏锐的心灵,找到一个出口。
“难以入睡的身体,多么需要一场雨!”(《失眠》);“在通往某个其他存在的通道上”(《通道》)。“事实上,它们进入了另一个国度。黎明前的一小段时光。”(《翅膀》)……“失眠”与“雨”有什么关系呢?事实上,“雨”是一种言说方式,只有通过雨或水,才能发现事物的另一面,也只有通过雨,才能感知到“时间”一类抽象的事物。雨(或水)是一种从具象事物通向抽象事物的媒介,一条感觉通道。而诗人的写作,始终是在勘探这条“通往某个其他存在的通道”。有时它向诗人自己敞开,有时它也向读者敞开,而有时它在幽闭的远处,诗人只是给我们一些方向性的暗示。有时诗人就置身在那通道之内,有时已经是在另一个“存在”之中。《和平中路》暗示的就是诗人已经在另一种存在里。而这样的进入,是需要一双翅膀的,这是一双超验的、精神性的翅膀。诗人擅长描写轻的、细的、薄的、透明的、有细微颤动的事物。善于跟随、捕捉、定型那些容易变化、遁形、消失的事物,比如自己的情绪,让它们在另一种存在里显形。
这种对自我的审思也包括诗人对世界的客观性和人生的冷峻性的本质思考,“假如……/我才明白——世上的喜悦多么贫乏。世上的感激多么不值得一提。”(《野浆果》)这个情感逻辑三段论,十分简洁有力。是少有的充满张力的诗句。“湖水轻漾。透明的枯叶落入了泥土。稍不留神/一些卑微之物转眼就变成了金子。”(《卑微之物》)事物的新陈代谢,是一个不断“失去”的过程。所有所失去之物,皆是客观的、自然的,但也是值得珍惜的。“静默的事物一无所获”,这是一句哲理性很强的感悟。在现实功利的意义上,像橘的果、地黄花这类事物因为缺少投机的本领和严肃的热情而被时光静默地带走,但它们是永恒的,下一个季节来临,河水开始变得清凉,它们又会无声无息地回到原来的地方。而那些看上去辉煌耀眼的、坚固的事物,事实上是易逝的事物:我看见一个古老的故事在瞬间发生,又在瞬间消失不见。而那些所谓有所获的事物,则往往是附着在人心上的赘余的、容易掉落的东西:河流巡行,一路清洗窗子。瓦片。清洗一些匆匆赶路的内心。《静默的事物一无所获》这首诗不仅哲理性强,当下感、现实感也很强。但诗人沉浸在自己的诗意空间里,只是发出一种感慨,即使批判,也是柔和的。
诗中的人称代词“谁”、“你”,以及其它一些反复出现的意象,它们承担着庞大的叙事功能,构成诗中的对话情境。这个“你”多半是指自己,有时也可以是一个抒情、言说对象,这个对象可以是一个具体的人,甚至是陌生人,也可以是泛指。例如《和平中路》中的“你”可以看作是诗人自我。而诗中多处反复出现的“是谁”这一追问性的代词,构成一个更有深度的对话语境:“是谁把一座古老的森林埋入水下。是谁,在水边低低吟唱?”(《风轻叩桥面》)“是谁俯身看这一切?是谁,从未离去?”(《古旃檀》)“谁能听到水声?一个冬天,是谁穿过荒林,穿过了冷冽的风,取回那火的冰?是谁,赶在一盏灯点亮前,斟上这干净之水?是谁怀抱谦卑,结伴那远古振翅的大鸟,御风而来,在江畔听涛?”(《彼岸的水声》)这些诗句在对水的沉思、冥想与追问之中,引出一个水后面的更大的存在者“是谁”。
事实上,我们无须一一去对应追索。这些人称代词意象,发挥了强大的诗学修辞功能,它的指向是一条精神的探索路径。诗中的“我”“你”“是谁”等人称,可以看作是一个人的思考、探索从自我到世界,再到神性的不断上升过程。这个“谁”仿佛造物主,仿佛源初的真理。而诗人所表达的,也是类似于张若虚“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类似于屈原的“天问”似的终极追问,这样就把诗歌的存在之思提升到了哲学层面。
在一个物欲横流的时代,诗人如何跳出现实的物质主义逻辑,如何祛除技术意象和消费性思维对人的心灵的遮蔽,而保持纯粹的心灵之思?这恐怕是诗歌自身无力承担的问题,但“思”可以,那么谁是那个进入“思”的人?这是超越文学之上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这组诗不仅仅是诗,而是一个被打开的存在场域,是一个被萦绕、包裹在水中的纯美的世界,是一个供我们的精神栖息的乌托邦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