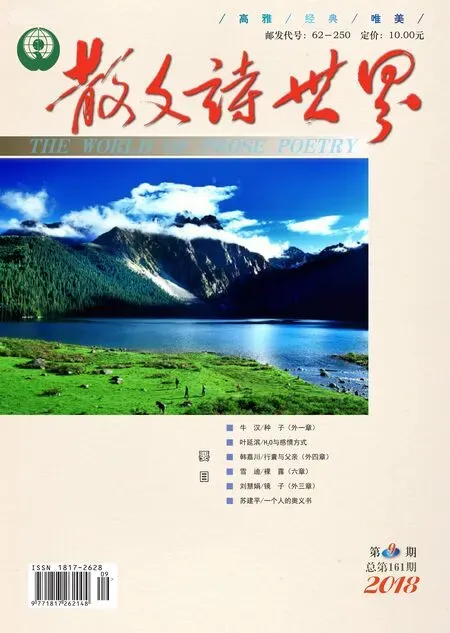雨中走故乡(七章)
北京 张玉泉
月夜之思
月亮沦落为远房亲戚。在我背后照耀着,我却很少抬头。
一切影子都那样模糊,在爬山虎绯红的脸颊上,一阵迷茫的月光,在影子中跳跃。
不是白色的,不是清澈的,不是旅者的保护神。我只能手捧月光,祭奠我走失的童年。
一切烟消云散去。没有过去的历史,怎会有不可阻挡之未来。也许闹钟,就是乡街上曾经喊醒村庄黎明的公鸡之魂。
我不再犹豫,我甘愿做一个沉沦者,在无边的城市死海中泅渡。
那是一个无边而遥远的彼岸,需要一颗从不放弃的内心。我坚守每一次黄昏来临的时刻,坚守自己的身体与命运,也许未来如同这缕淡雅的月光,在黑夜中独自前行。
麦场上的成人礼
是风,吹走了麦子的衣胞和麦芒,风在一阵平息的麦场上,落下的是炊烟的重量。
我坐在牛耙上,一只牛,甩着粗壮的尾巴,为麦子脱粒。
扬起我高昂的头颅,看见了父亲,看见了天空的丰腴和饥饿的粮仓。
那就是我,一个懵懂的少年,懂得了父亲扬鞭的含义。
在村庄的场上,一场硕大的黄昏成人礼,以艰苦的劳作作为序幕。
我扛起粮袋,像扛起了父辈的期望。走吧,朝前走!慈爱与丰收、汗水,都是种植在一块贫瘠土地上的同义词。
麦场与河流
我的心像麦垛一样的高耸。
坐在扫把上被牛拉着,顺着麦场转圈,蓝天白云都愉快地飘浮在头顶。
村口的水井已经搬迁多次,至今还未从记忆的地点中删除。
我牢记着浪花的形状,在石头的碰撞中发出了白色的闪光,照亮了河床。在激流中,我渴望看到游鱼溯流而上的转身。
我常常路过河流,而许多茂盛的草丛,藏着一种孤独的灵魂。
只有在亲手种植的土地上,才感觉到了生命的秩序、善良和亲近。
我手捧刚刚脱离了襁褓的麦子,细细地品尝。她的清香,弥漫过童年的嘴角。
菜地上的风景
不会只有无名的坟墓。
我常常听到风雨的叹息,就在不成器的桐树下,我寻找金铃一般的蝉声。
我寻找斑驳的天空,那一缕白云的光线。
黄昏顺着河流轻轻地歌唱,金不换也愈加青翠。
那是奶奶的金不换,用来洗脚消肿的金不换。
我听见了一棵野豆芽的张狂,顺着篱笆偷偷地直起腰杆。
我听见了内心的风雨,就在黄色的桐叶上,一只蚂蚁啜饮着迷离的哑泉。
我从来不会说话,浑厚的土地上,虽然那些简朴的花朵都已经开放,我不去打扰她们,她们的约会是那样的隆重,面对一座村庄,你可以听见叶落的回声。
如禅。用我最初来世的耳朵,聆听你无声的语言。那些结实的词语,就在松软的泥土上,随意翻阅,都是一卷卷可以净化的经句。
或许,你不知道,一切都有花开的内心。当你慈悲的目光,投过密林,看到桃花的骨朵,就在红色的皮肤下面,我甚至想提前摘取她诱人的果实,在我老了以后,仍旧把属于她的甘甜,还给我的幻想。
故乡橡子
在一棵苍老的树下,多少熟悉的月光被年轮铭刻。悉数光阴,都挂在了蛛网颤抖的内心。
雨珠零碎,急雨未曾修剪,藤蔓四处飘摇。
该倦了的院落,放不下一颗归乡的心,等候着一场雨的叩问。
一场雨的洗白,从哺育到厌倦,从熟悉到陌生。如此加速的变故,让你我两鬓斑白。
少年已经走过风雨人生,像极了一颗滚圆的橡子。被遗落在如此深奥的山谷,独自面对一汪深雨。
远去的荒芜
再也无法看到逝去的流水,光阴早已被水纹以流动的方式埋葬进大海。
河边生长的野草早已荒芜成经年的陌生。只有山川起伏的形状可以辨认,只有道路的弯曲可以辨认,而河边的呼喊早已老去。
只有踉跄的雨,漫步在村口。所有的斑白挂在雨的梢头,苍茫的颜色被风吹落。
辛夷树独自飘香,菜园废弃。我是来自记忆中的泥泞,是谁拱手让出心灵的巢穴。
雨中的故人
所有的瞭望都带着热度,都带着厚重的雾,带着化不开的愁绪。我需要这一浓烈的雨,让我的内心重新归于沼泽。
我愿意与村庄一起变得模糊,从蛛丝马迹中发现云朵的粮仓。
让干涸的荒草苏醒,从母亲的坟头苏醒,望穿崇山峻岭,灵魂在城市安家。
让结实的雨丝竖立成一座墓碑,在泥土的额头刻出未曾发芽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