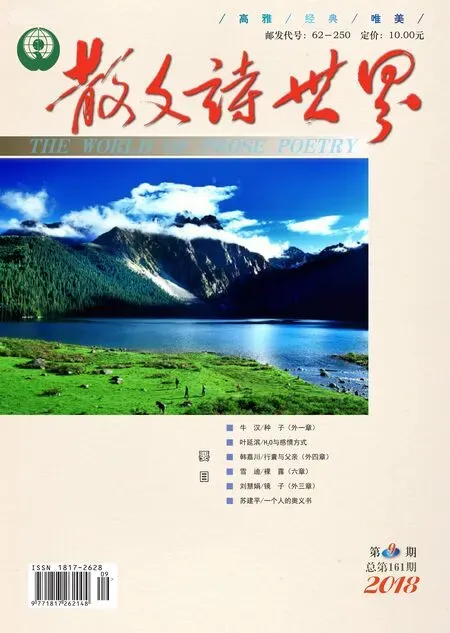一座村庄的流水汤汤(六章)
甘肃 朱旭东
抛沙河
该有一条河流允许我追本溯源。
一滴水也拥有,一条河的五脏六腑,流淌的血液和不弯曲的骨头。
从河流的身体里出走,你把一代人的足迹种植在了随身携带的泥沙里。
你看得见由小变大的全过程。
颓废,沮丧,挣扎,笑和泪,构成了一个年代的落花和流水。
像一座桥,只待你路过。
我伸出的手不再是折弯的钓钩,我只是试图为你剥去一层层波纹,还原清澈和恣意奔腾,以及梦中怀揣着的大海。
事实上,我想把一切还给你,包括生活留下来的磨不掉的锈迹。
我看见河水里的一面镜子,碎了,没有来得及捞回。
我选择从源头再一次匍匐潜行,去凭吊你与生俱来的悲悯。
一条河流的失踪
从挺拔的鸡峰山面前流过去,平铺在地的抛沙河怎么说,也是一条河。
当初,足够有胆的人跳进河里游泳,生活残留的疲惫与污渍,颗粒饱满的汗珠,燥热不堪全部被抛沙河擦洗干净。一上岸,又像重生了一次——身体、心情全是新的。
也有自以为是的人,跳下去就再也没有上岸——后半生沉入河底,永远。
那时,去河对岸必须架桥。木桥、石桥、吊桥、水泥桥,如抛沙河伸出的臂膀,扶住粗粗细细的日子,扶住婚丧嫁娶,扶住出门远行,扶住衣锦还乡……
河在桥下流,人在河上走,是日常生活的常态。
现在的抛沙河,仍从鸡峰山面前流过。人们想要的生活,她再也力不从心。
凡是下河的都可以上岸,只是再也没有下去的必要了。
那些桥——木桥、石桥、吊桥、水泥桥,更像裸露在外的骨头,有的残损不堪,有的被堤岸抬在手里,不知道何去何从。
唯有堤岸,仆人一样站在原地,河水却已不知去向。空空荡荡的河床里,流淌一条解剖开来的河流、一条等待祭奠的传说。
抛沙河怎么说也是一条河,纵然河水失踪,河床荒芜,也对得起自己的称谓。
翻开县志,每页都流淌河面上绽放的浪花,晨钟暮鼓式的涛声。
只是现在,她离家出走了,从鸡峰山面前,从我们亲手调配的生活里。
周末,和赵老师爬山
需要这样一种高度,提升逐渐下滑的生活。
正如需要一顷湖水,填补二十多年欲望的沟壑。
为了能抵达高处,来此之前,我放下了本该属于低处的重量——
一大块黑板,一大截粉笔,一大堆滔滔不绝的词汇。
分割成一百份的心,现在重新完整,完全归还自己。
五月的树上,那么多樱桃。七嘴八舌,讨论火红的夏天——
这一季,它们将遇见一个怎样的胃,咀嚼甜美的一生?
那些核又会在哪里生根发芽,会在谁必经的路旁开花结果。
山中生活的细枝末节上,结满了更多细致入微的幸福。
它们象征着什么,暗示出什么,我无法将它们一一描述。
年长的赵老师笑着说:在这里置一座小院该有多好!房前栽花,院边种庄稼。
一抬头看见西红柿提着灯笼,照亮了昨晚所解的方程式,结果都和萝卜青菜有关。
一转身便与满径的花香相遇,和亲手种植的生活说一声早安。
太阳懒洋洋地晒在天上,让赵老师的笑意无处藏身。
一只狗突然丢失了悲喜
只剩下木板钉做的狗窝,空空的,装得下一整个春天。
再也牵不出摇晃的尾巴,抖动一身灰白相间的绒毛;再也跑不出一连串狗吠,再来盘问下一位来者的身份。
只剩下一个不锈钢空碗,不需要喂食,倒水。
不需要用一家人的残羹剩水,喂养一个不挑不拣的胃。
一只狗突然丢失了悲喜。
残缺的一生,除了生过泪水和汗水,这一对永远养不大的双胞胎,它至今还没有一儿一女。
一根沉甸甸的铁链子,竟不能牢牢地拴住一只狗从幼到老的一生。
它没有走完的部分空空荡荡。
春天在这个时间段破了一个洞,无论春雨针线手艺再怎样纯熟,也缝合不出生命的迹象。
一只狗的愿望
一只一文不值的土狗,它价值连城的愿望肯定是,去我家后院以外的世界,看一看。
跑上一座真正的大山,哪怕张大嘴巴喘息。抖一抖全身淋漓的大汗,去摸一摸河流,没有风吹,也摸得到自由的流动。
世界那么大,它至少会在某座高山之上,流水之畔,结交一个知己,促膝长谈。
最好能逢着一段爱情,即使懵懂,一朝一夕的相守,也足以捏碎将铁链数成念珠的孤独。
它叫得出每一位来访者的名字,却没有人知道它姓甚名谁,包括它的主人——我们家的任何一个人。
它该有一个狗模狗样的名字,该有块墓碑,刻得下名字就行。
该有多大一片土地,才埋得下忠诚、逆来顺受的命运以及被束缚住的一生。
站着睡觉的树
从破土而出到这把年纪,一棵树在半山腰站了多少年?
对面一贫如洗的荒山上,一棵树兀自孤立,它站成了一棵风景——
隔着无法逾越的空旷,我看见那棵树似乎睡着了。
挺直腰身,闭着眼睛,不随风左摇右晃。
该是怎样一个灵魂,囤积过往的风雨和未知的静谧,抵挡来自外部的诱惑?
这是深秋。枯萎,使劲敲叩每一棵树的木门。
落叶纷纷,时光碎了一地。
面对季节的横征暴敛,除了脚下扎根的大地,除了向上生长的执着,那棵树别无长物。
夜幕徐徐降落下来,它已然身陷一个高远的梦境。
将一件事坚持了那么多年,醒和睡,只不过是向前迈进的左脚和右脚。
秋风吹动梦外的事物。它站着睡着了。
以一种倔强的姿势,聚敛起整座山的富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