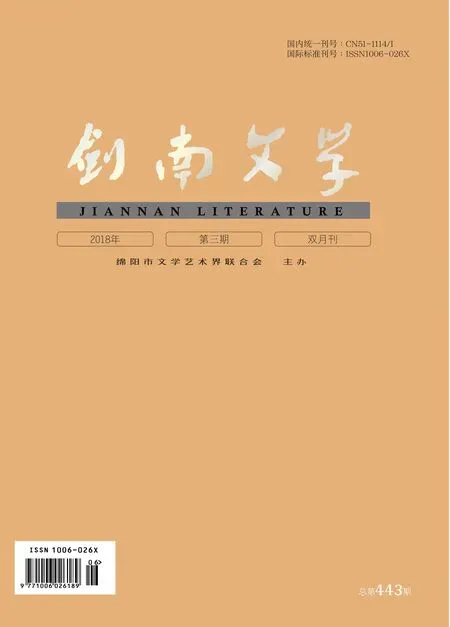“绘事后素”,大地情深
——评侯志明散文集《行走的达兰喀喇》
张叹凤
《行走的达兰喀喇》据作者“后记”说原题《无家可归》(取自集中一篇名),可能是考虑书名的影响缘故,改为现名。“‘达兰喀喇’是蒙古语,意思为‘70个黑山头’的阴山。”作者自述是“走西口”的后代,“家乡就在达兰喀喇中部大青山北麓的草原”,如此“行走的”意思自然不言而喻,也还比较贴切。《无家可归》虽然能够纪念作者长年南北迁徙工作调动的生活,以及在“5·12”汶川大地震性命攸关亲身经历并率先领队抢险记录,终究还是没有现定书名更有诗意,更能寄托作者的一腔乡情牵挂。但披阅全书,极少有涉及蒙古族生活、语言之处,于是阅毕就想同作者商量或许径直题名“剑南漠北”以及“家山北望”之类更加简洁明了?不用多加解释。
不论如何,这是一部“志深而笔长”的散文集,作者长于抒情、叙事、致理,处处能绘出塞北江南的苦寒与温暖,字里行间纯孝之情,不假雕饰,均出于生命最本真的流露,这不约而同见诸书扉三名推荐者,也算是共识。作者的文字不由令人联想到孔子“绘事后素”的说法,即善绘者返璞归真。单纯,文风简洁;含蓄,大巧如拙;腼腆,谨慎于引用,用则画龙点睛。通篇看得出他长期文字工作积累沉淀与其对文学写作审美憧憬的充分体悟把握。虽然书封题联:“行走江河大地,感恩世间万物”,统观之后,绝非泛泛之论,深感其用心独到,凝聚于亲情乡里,那一片“敕勒川,阴山下”作者生命的摇篮,以及剑南(川北)四百里作者的第二故乡,绵绵不绝,合声雅奏,突出其文质肌理——真实、朴素、简劲、诙谐,也许还时有淡淡的忧伤,但自始至终,总是一颗赤子之心、娓娓不倦之情,诚如西哲赫尔德所谓:“乡愁是所有痛苦中最高尚的一种痛苦。”行文有如斯“高尚”的气息贯穿始终,即便多写琐事、身边事、平常事乃至“鄙事”(子曰:“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按指如今打工、苦力活件),及至尴尬事、伤心事(如其儿时打破了父亲要命的酒壶——《父亲》;成婚后想申请一张闲置于巷道的公家破桌子而被拒——《写在第十八个纪念日》;大地震灾难中恨不能三头六臂多施救而掩面哭泣——《痛定还痛》),总能文情溢出,细节精微毕现,如《文心雕龙》所谓“真宰”存焉、“英华乃赡。”(《情采篇》)作者自己撰文也这样认为:“生活中有许多小事,本来是没什么意义的,但由于融入了一个人当时的心境,融入了某种特殊的情调,也便有了特殊意义。”(《想吃一碗馄饨》)这种“情调”感,即作者行文的面貌魅力。“高天厚土,父母恩深”,能让刘庆邦先生阅读间“双眼一次又一次湿润”,主动致电作者表示:“写得挺感人的。”(刘庆邦《序·常怀感恩之心》)内蒙古电视台资深记者、散文家张阿泉在笔者向他推荐这部散文集读后也发图文写到:“质朴可读,尤其是作者回忆故乡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的篇什更为亲切醇厚……仔细回味,行走的并不是这些乡土风物,而是融入血液、梦绕魂牵的一脉乡思、一枕乡愁。”(见张阿泉公众群)都能言中肯綮。
作者能写出别一种诗意,得自他人少有或不能深入的高原边疆生命体验观察,如家乡生活、农人的艰难与爱惜,集中《母亲》《父亲》以及共分为“感恩”“感情”“感物”“感言”“感事” 五个专辑,一切与父母、妻儿、手足同胞、师长同窗、亲情乡情紧密关联的篇什,莫不精神流动,指向“游子悲故乡”。生于高寒“草莽”间的苦孩子,他的生命历程与“因为懂得”的回望,发诸内心世界,感触深至,写出来自然不同凡响。如以下这些行文段落为证:
烙月饼虽然是大人的事,但我们孩子总是围在跟前,看母亲如何把月饼包好,如何用一个刻好的五角星或六角星蘸了红色印上去。然后,看母亲把月饼拿去,到一个平底锅里去烙。就是做这么简单的事,我似乎也很少帮助母亲做到底,往往是干过了新鲜劲,吃饱了肚皮,或悄悄溜走,或倒头便睡。剩下的事只好由母亲一个人来做。
这天所烙的月饼我记得分三种:一种是普通月饼,一种是小月饼,一种是大月饼。所谓的小月饼,并不是个头小,而是烙一些各种各样的图案,比如猪头、兔子、鸡等,为什么要烙这些动物,当时我没有问过母亲,现在只好作为一个谜暂时存疑了。所谓的大月饼确实很大,我所见过的母亲烙过的大约直径有一尺二三。这个大月饼很需要一番苦心制作。首先得在里面包糖、擀平后,边上须得切出些花来,然后再在中间画出个圆圆的月亮。
——《月照相思》
是啊,父母亲是经历过饥饿的一代,是饥饿的恐惧,使他们如此看重每一粒粮食。而所有的苦,又有哪一个比得了挨饿的恐惧呢!有一次,我跟在他身后,他对我说:“有这些粮食,即便有个灾年,至少两年不怕挨饿了,节省点也够三年。明年如果年景好,还可以卖一部分,给你们买点新衣服。”在那个年代,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的父亲,要养活一个七口之家,除了吃穿还能考虑什么呢?
遇有丰年,粮仓会装不下,父亲就会在院子边,挖一个直径1.5米左右很深的直窖,把粮食倒进去,然后在上面铺了麦秸,然后再用土埋上。埋的时候要尽量看不出任何痕迹,还要放上一些农具等东西,仿佛这里什么也不曾埋过。
——《怀念家的粮仓》
一幕幕快乐的镜头从眼前掠过。人尽管还是这些人,但每个人似乎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可爱。唱着,欢笑着,追逐着,不知不觉我笑出了眼泪。我掉眼泪了!我吃惊自己。为什么?我问自己。我忽然想起了清代文豪李渔说过的一句话:“人能以孩提之乐境为乐境则去圣人不远矣。”啊,在这个静谧的晚上,哈仙(引者按:指地名)你究竟是怎样把我们带回天真烂漫的童年的?你又为什么要带我们向圣人靠近,去体味圣人的乐趣呢?
——《爱你,哈仙》
限于篇幅,我想,摘录以上三节原文,未读过集子的读者已可感受作者的文风眉目。他写及父母师长恩者的行文,明白如话,行状自然,娓娓道来,不无苦中的欢趣。没有多少模仿雕琢痕迹,但体会得出,显然是受到“五四”朱自清、废名等一路白描作风的影响,包括集中多封写给儿子的家书体散文,细大不捐,苦口婆心,又多少有些家长傅雷的影子。却都能融入化出,左采右撷,行文熨帖。最精彩还莫过于他对塞北高原农事生活的细微描写,最能令人念及:“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采荼薪樗,食我农夫。”笔者感觉这方面也是作者散文集中上乘之作。除前引之外,还如《感谢母亲》《父亲有句至理名言》《熬糖饧》《老屋》《老树》《老井》《母校杂忆》《煤矿,那些抹不去的记忆》等,皆有可圈可点处,令人掩卷而神思。也许作者未必认同这观点,也有名家被他“行走”主题“打眼”“瞒过”,未及深究即题写“花重锦官城”或“处处为家处处家”的荐文。实际上这个集子除了汶川大地震一篇亲历长记感人至深外,其余写及他乡他国包括“剑南”风俗的行文,都不及他生命本真与精神家园的塞北题材内容更加沉着有力、摇曳多姿。有些哲思类的、观光型的泛泛小文显然初为报端所撰,选入集中,并不都称身,有的甚至会稀薄原题的内容分量。作者的心思才华,集中所谓的“干货”,显然还在书写那一方塞北草原黄土的行文中。起于艰难,沉吟既多,更多的会心,更能体现推陈出新之意。
林庚先生评《诗经·七月》有道:“乃是一个日历的歌诀,而这些日子上便都带来和悦的生命。”又形容旅人之思:“乃是劳人行役之时,却于叹怨之中,还给我们以林野的景色看,所以生活的美趣,乃无往而不存在。”(《中国文学史·女性的歌唱》)我想中国文学科班出身并曾经长期任职业记者的作者——侯志明先生,致力诗文,他的审美认知必会赞同这样的评判。而我们对于他的散文集《行走的达兰喀喇》其精华部分,亦正有着这样感觉上的借喻与形容——“生活的美趣,乃无往而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