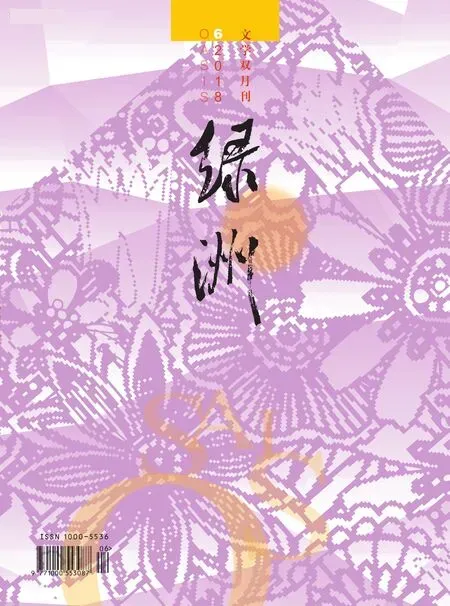日常的诗意
——黄毅散文品读
黄毅是一个被低估了的作家。尽管他已得过很多奖。任何一个时代,一方地域,总有一些真正的实力派被文学的流行所忽略。这种忽略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对新疆作家来说,如果你不能鲜明地提供一副主流文坛对你的地域期待的典型或符合他们想象的面貌,偏远、偏僻不占人脉优势的地域背景,就将你置于某种竞争的不利位势了。而新疆书写的样貌无疑应该是多样的,是多姿多彩的,它必不是为了迎合某种流行期盼而硬将自己塞进模子的产物,它的由众多个性作家撑起的样态,也必将增加新疆书写的整体厚度与高度。
“我出生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石河子下野地。和一些兵团作家谈起这个时,我说,我是兵团下野地人呀!但和南疆的人在一起时,我又可以说自己是南疆的;和石油系统的人在一起时,我也可以说自己是石油人。从民族属性上讲,我是壮族。”黄毅的出身,仿佛就是大部分新疆人的来历。整整一代人,我们要把根扎在这里了。一想到自己是新疆人,对新疆,怎么抒情都不过分了。所以,黄毅曾经写下过那么多新疆的篇章。归纳黄毅的散文写作,似乎不应该用写了什么,而应该问,什么是他没写过的?《新疆时间》《新疆四季》《不可确定的羊》《和田叙事》《秋之喀纳斯湖断章》,这些早年为他获得赞誉和声名的美篇,都浸润着黄毅对新疆的情感与认知。
近读黄毅的《疼痛史》,可看出他乃至新疆文学整体的某种走向变迁。新疆书写,正在填补和充实自己风情地域书写之外的日常,或内心与灵魂。黄毅开始写病痛了。看到这个题目不免心中赞叹。中国人是个偏爱喜庆、吉祥的民族,一般对自己的倒霉事儿讳莫如深。西方人则不然,对悲剧欣赏的文艺细胞格外发达。苏珊·桑塔格就不放过自己得病的经历,像是对袭击了她的癌症的报复,她写了《疾病的隐喻》。当然作为学者和作家的一体双面人,她这本书更高的目标似乎意在揭示、批判社会的病症。黄毅则更多的是用诗人的感受和笔触,将目光凝胶在被一再贬弃的“身体”之上,再现着自己对生活、对人生的体悟。一个一直被疼痛放逐的人,是一种怎样的精神或心灵状态?黄毅从纯粹的身体创痛,写到了人的精神之痛。疾病,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名词。它的隐喻和象征意义,像一条隐形的绳索,或远或近地威胁着人的脆弱的存在。纯粹的身体之痛与精神之痛有明晰的分界线吗?相伴生或一前一后的人生之痛,其实早已不知不觉、浑然一体地主宰了我们。
“上帝造人时也在其血液中添加了疼痛的因子,并用它来控制人。”“疼痛是肉体的哗变,灵魂的背叛,也是外部力量作用于精神而产生的不同梯次的震颤,是温暖的熄灭,甜蜜的稀释,美好的飘逝,健康的病变,阳光的黯淡,清风的污浊……”“每一根铮铮白发,无不是被疼痛之霜打白的,而每一根白发也是疼痛的觇标,是疼痛敏感的触须,只不过经历了无数大大小小的疼痛,对疼痛的忍耐力有了空前的提高,表面上的无所谓,恰恰反映出了内心承受的巨大疼痛。疼痛是长期潜伏下来的卧底和线人,你的所有秘密它都熟记于心,在你毫无防备、得意忘形的时候,一击之下让你毙命。”
黄毅可能没有意识到,他从诗歌转到散文,留下了诸多的“后遗症”。这使得他的散文大多数时候近似赋,铺张扬厉、铺采摛文。诗人的炼句本能、想象的奇瑰、抒情主人公的主场意识、对具象的迷恋……黄毅是散文的古典派。能坚持古典写法的,必是才华很高的作家。旁的作家,不东拉西扯、左右敷演,或者依附于叙事,怎么完成一篇文章。而黄毅硬是凭着他的诗心诗眼,不偏不离围绕某个主题,挥洒的全是才华。其中充斥着华丽的比喻、奢侈的想象、缤纷的色彩、繁丰的细节……黄毅的散文是写给同行看的。他的古典体现在他还是那么迷恋辞章。他的心里一定睥睨时下很多的散文。对比他的富丽繁华,很多人的文字显得太没修辞难度了,更遑论想象力。
一个人届中年的作家,最关心的是什么。一切都没有了早年的对世界的顾盼流连,争强好胜;一切峻急的、夸饰的、浪漫的、外向的激情与冲动开始向内收敛;连注视也变得平静、变得节奏放缓、调门调低;惟一不变的,可能还是放不下的对世界的一颗诗心。一个真正的作家,怎么会随便放下自己的笔呢,正如一个活人不会放下手中的食物。所以,有了这些漂亮的句子:“我在狂奔的时候眼睛好像看不清东西,居然在短短的十几秒内不偏不离跑出了一条直线,”“那疼痛犹如晨钟,在我的体内铿然訇响,余音袅袅,经久不散…….从此,我开始害怕早晨。”“我口瞪目呆,就像革命干部接受被双规的决定宣告一样,再牛皮哄哄的人一下子就蔫了,所有的心性和胆气都给灭了。”“当一个人的行为有所顾忌的时候,说明这个人被上天用了某种方式点化过,腰痛肯定是其中的一种方式。”
我尤其欣赏黄毅对疼痛采取的纪实主义态度。一般印象里,英雄是不应该轻言疼痛的,似乎那样的表现仅仅是妇女和儿童的专利。然而,谁能说身体不是一种政治?一种形而上学,一种意识形态?笛卡尔式身体、精神二分法早就受到后现代思想家们的质疑。身体似乎是罪恶的渊薮,是非理性的;在真理领域,身体也几乎完全没有发言权,在哲学上,更是不堪入目的笑话。必须有效压抑其做乱的能量与力量。将身体变为有用又驯服的生产工具,就是我们一直追求的意识形态。然而,从尼采开始,身体开始了反叛,走出了历史的阴影和屈辱。难道世间的一切不是以身体为准绳?正是身体操纵了历史,左右了哲学。福轲甚至认为,道德就是从身体内部的生物学冲动出发,是身体灵机一动的结果。身体是来源的住所。身体与主体如何区分?也许一直被贬弃的身体,才是真正的主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黄毅的《疼痛史》有着非同一般的价值。
一方地域是需要一批实力雄厚的作家的。出那么一两个拔尖的不算什么,有了高度更应具备厚度。这种积累才是真正的财富,才会惠及后人,惠及一方水土。从小就喜欢文学,可是在我最敏感最有可能成为一个作家的时候,举目四望,没有看到写作的同类。孤独和自卑吓退了我。用了很多年修正一颗向往文学的心。等我可以正大光明地从事文学的时候,又已经过去了很多年。那时候我要是知道,在新疆,还有这么多像黄毅这样的作家同行,我是会有勇气在十几岁的时候发表作品的。实际上,黄毅和刘亮程、北野和周军成,曾经以四小龙的诨号在新疆文坛彰显着松散的流派特征,也许这种文学的团体就会影响后来者呢。四兄弟的文学品位都很高,对书法、绘画、棋类有着不俗的鉴赏和实践能力。是古代文人传统在新疆的自然接续。黄毅尤其涉猎面广,交游着一批新疆画家,他们钦服于黄毅的画评。美术评论不是那么好写的,既要懂得世界绘画史,又要有灵心慧眼,有鉴别力;黄毅还创作歌词、写电影剧本……除了聪明、天赋,还能怎么解释黄毅之才呢。
而有时黄毅也吃亏在他的复杂暧昧,他不能提供简洁、鲜明的新疆符号,或新疆款式,用来抓住读者。他似乎更热衷于写他眼里的日常的新疆,拒绝被轻松地消费,流行的轻文学显然于他不宜。他不讨好读者,也不当读者是蠢的,他用了全力,写每一篇文章,认真但也许并不被贴心地回报。实际上,精明的读者并不多。
“大师的意志愈坚定,众人的感觉就愈强烈。”“忽然变得无所谓了,不愿意多想也不愿意深想,疼痛把我悬浮在半空,晃晃悠悠的,任凭什么风都可以把我吹到任何地方。”“而我的这个时代,已经强力干了多少件力所不能的事,这个时代是否也患有椎间盘突出症?它的脊柱是否也在变形?疼痛从此根深蒂固?”“人生无论清白与否,骨殖都会是白色的,这些白色,让我们懂得宽宥,原谅自己,也原谅别人。”他在散文中贯注了许多的智性思考,但对这个浅薄又没有品位的时代来说,这些思考让读者觉得是多余的负累。他们宁愿你在文中让他们轻松搞笑地度过一段闲暇时光,愿意不假思索地由你带领进入别人的故事。一切要轻松、猎奇、有趣,显得情商很高的样子。而不愿深入地去体味复杂、痛苦、不安以及孤独的韵味。这使得时下的散文,很多几乎沦为中产阶级消闲的时尚装点。黄毅却一以贯之地不愿提供这种简明读本,他更愿意将自己对生活的复杂况味、他的精神发现,以诗意的语句与世界对话。
他的两篇写人物的,巴登和老那,令人叹服。不用认识这两位,我以为黄毅把这两个人从外形到内心,从物质到精神都写透了。当然,我们刚刚还质疑了笛卡尔对身体与精神的二分法。在这里提到的物质是指酒,精神是指酒与人浑然一体后的状态。巴登和老那,就是我们身边的“熟悉的陌生人”。这种描形状物,抓细节,抓关键,抓意象,抓瞬间的本领,得益于他在报界从业过多年。形象的比喻,机智的观察,细腻的描写、精微的发现,这些叠加在一起,使黄毅的人物散文格外生动、引人入胜。
我们如何评价别人的一生?正如尼尔·波兹曼所说,也许我们将毁于我们所热爱的东西。看罢惟有感叹生活远比纸上的丰富复杂,而生活到了纸上还能保有那种丰润和鲜活吗。黄毅以他观察家的敏锐和诗人的穿透力,外加时间终于馈赠他的淡然的幽默,让我们看到他人的一生里可能蕴藏的自己的一生。“酒原本就是用来燃烧生命的。”“自己欢乐了,天空就欢乐了,自己在云端行走,还在乎谁在地上爬行?”生活在苦寒又辽阔、寂寥又混血的新疆,还有谁比我们对酒更理解更依赖?在这两个人物身上,寄寓着黄毅对他们的深深的懂得与喜爱,以及在这之下的对世间的温柔和怜悯。
这种理解是哪来的,黄毅对此绝对是有准备的。正如胡康华对他的评价,“我认为黄毅是最早进入西域历史文化精神腹地的探求者之一。”“不了解新疆文化,不了解新疆各族人民的文化心理,怎么能够写好新疆散文呢?我看有些新疆散文纯属文字游戏!”黄毅是有资格批评那些浅薄的散文的。这资格就建立在黄毅书写新疆的视野、格局、知识和情怀之上。
我在文中一再提到新疆,并不是把黄毅定义为一个新疆作家,恰恰相反,我的比较系统背后有一个模糊而又清晰的全国图景。我也从来不认为新疆最优秀的作家有必要自我卑贱化,我们缺的就是像黄毅这样水准作家的数量。黄毅也许不知道,他的文章已经或正在影响着新疆文学的整体风土,一批这样水准的作家正在垫高我们的文学积淀。新疆文学,将会是有传统、有来历、有大量代表作家的一支劲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