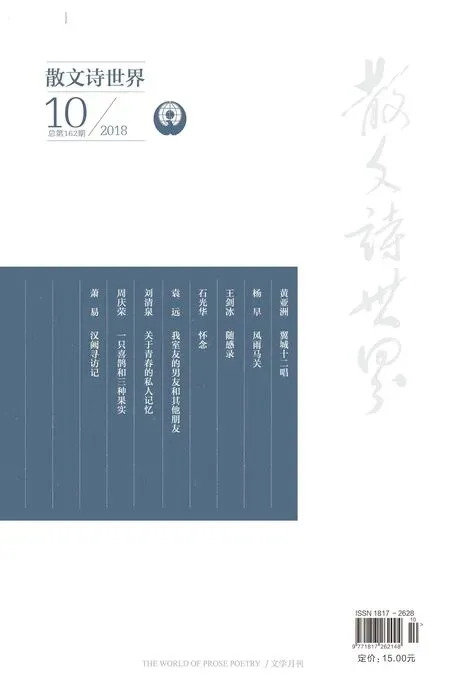汉阙寻访记
萧 易
“佻兮达兮,在城阙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阙”至迟出现于西周,定形并盛于汉代,汉代是“阙”的极盛时代,“汉阙”一词由此得名。中国现存汉阙45处,其中24处在四川省,它们被称为“中国最古老的地表建筑”,如同一些峨冠博带的老者,讲述着汉人的城市、建筑、生活、传说,甚至梦想的天国。
大约一百年前的一个初春,法国探险家色伽兰与同伴法占行进在四川渠县县城到城外土溪乡的古驿道上,调皮的中国儿童骑在路边残破的石兽上,对这些高鼻深目的外国人指指点点,路边黄色的建筑物下,坐着不少身着长衫的中国人。色伽兰翻身下马,走到建筑面前,他2月初从京师出发,经过2个多月的跋涉,终于见到了朝思暮想的汉代遗物——汉阙。
此前,这位精通汉学的法国人曾在《金石录》与地方志中寻得汉阙的点滴资料,当2000多年前的汉代建筑出现在眼前时,色伽兰还是大为惊叹:沈府君阙的顶盖如同一座年久失修的屋檐,高挺的阙身上,一条张牙舞爪的青龙口衔玉璧下的绶带,直冲云霄,朱雀翩翩起舞,下面有一行古朴的隶书:“汉新丰令交趾都尉沈府君神道”。府君是汉代对郡相、太守的尊称,这位姓沈的府君曾在遥远的交趾郡(今越南北部)出任都尉,这是汉代郡县之中的最高军事长官。
1923年,色伽兰在法国出版《中国西部考古记》一书,将汉阙照片对外公布,引起了世界普遍的关注,没想到在古老的东方居然保存着两千多年前的建筑。1939年,中国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刘敦桢、陈明达等学者专程到四川考察汉阙,踏遍中国寻访古建的梁思成,终于在这里发现了中国最古老的地表建筑,在《中国雕塑史》中,他赞叹道:“在雕塑史上,直可称两汉为享堂碑阙时代,亦无不当也。”
中国汉阙大半在四川
什么是“阙”?回答这个问题前,不妨先读读古代与阙有关的诗词:《诗经·郑风·子衿》:“佻兮达兮,在城阙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唐代诗人李白《忆秦娥》:“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宋代词人苏轼的《水调歌头》:“不知天上宫阙,今昔是何年?”单是《全唐诗》中写到“阙”的古诗,就超过了1100首。为何中国历代诗人一直把阙当做吟咏对象?
“阙”,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释为“门观”,晋人崔豹的《古今注》说得更为具体:“阙,观也。古者每门树两观于其前,所以标宫门也。其上可居,登之则可远观。”阙是中国古代竖立在城市、宫殿、祠堂、庙宇、陵墓两旁前的标志性建筑,用途不同,自然也就分为了城阙、宫阙、祠庙阙、陵墓阙等等。
早在先秦时期,阙便已出现,当时的阙大多是城市的象征。除了《诗经》,《毂梁传·恒公三年》也有“礼,送女……诸母兄弟不出阙门”的记载。秦国统一六国后,秦始皇也立了不少阙,最著名的便是矗立在东海之滨的东门阙,这是继长城、阿房宫、骊山陵墓之后秦帝国的又一地标建筑,是秦帝国面向东方海洋的国门。
汉代是阙的极盛时代,“汉阙”一词由此得名。汉代创立之初,丞相萧何在长安营建未央宫,除了前殿、武库、太仓,还修筑了东阙、北阙。汉高祖认为天下未定,就修建如此壮丽的宫阙,实在太过奢侈。萧何答道:“夫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换句话说,巍峨壮丽的东阙、北阙,就是大汉帝国威仪的象征。此后,汉武帝也在建章宫前立凤阙、圆阙,其中凤阙“高二十余丈”,汉代1丈约合今2.3米,凤阙高约46米,该是何其壮丽巍峨!凤阙遗址位于西安市未央区双凤村,分为东西两阙,东阙残高5米,西阙残高11米。
汉阙不仅是帝国的象征,还是汉代许多著名政治事情的发生之地。未央宫的北阙一度是汉人上书、请愿、请罪、行刑的场所,汉宣帝时,名臣赵广汉入狱,“吏民守阙嚎泣者数万人”;酷吏田广明讨伐匈奴不力,回到长安后也在阙下自杀。汉代每每擒获夷狄之王,常将首级悬于阙下,汉武帝时郭吉出使匈奴,就以“南越王头已悬于汉北阙”之语恐吓对方。巍峨的汉阙,传达出的不仅是至尊权威的建筑语言,还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王朝气魄。
长安城有宫阙,汉代的城市,从都城到边塞,大多筑有城阙,这是城市入口的标志,也兼有瞭望警戒与颁布法令的功能。两汉时期,伴随着一个个汉朝郡县的建立,恢弘的城阙遍布大汉王朝的各个角落,却鲜能保存至今。从考古发掘来看,汉代城阙大多以夯土高台为台基,其上有木构建筑,比如长安城宣平门阙址、洛阳城阙址以及四川芦山姜城阙址。姜城遗址位于芦山县县城南门外,百姓在这里常能拾到残破的汉砖、瓦当,上书“寿千万岁”“长乐”铭文。
汉代的宫阙、城阙大多已在漫漫岁月中崩塌损毁,后人看到的石阙,绝大部分是陵墓阙,这也是中国存世最多的汉阙。与城阙、宫阙相比,陵墓阙的体量要小得多,它们是一些礼仪性建筑,立在帝王将相、文武百官陵墓墓道两旁,是墓主身份与地位的象征。陵墓阙有着严格的等级限制,最高规格的三出阙(即一主阙两耳阙)只能为天子独享,诸侯、文武百官可用二出阙(即一主阙一耳阙)或单出阙,平民与商贾是不能立阙的。魏晋之后,礼仪性的陵墓阙、祠庙阙走向衰落,城阙与宫阙则一直延续至唐宋,明清仍有余绪。
了解了阙的历史,你或许可以理解,为何历代诗人热衷于将阙作为吟咏对象。阙位于建筑物的最前端,以挺拔、巍峨的姿态改变了中国古代建筑此前平面铺成的布局,具有“纪念碑”性的意义,常常用来借指城市、宫殿,《全唐诗》中频频出现的“城阙”“丹阙”“河阙”“朱阙”便是此意;再者,不少阙作为前朝遗物,孤零零地耸立在荒野田畴,那些残砖断瓦、败土颓垣往往引发诗人对往昔的追忆,这恰恰是中国诗歌永恒的主题;一些阙还作为当地的地理标志被载入史料,郦道元的《水经注》中便记载了诸多古阙。
本文在环境话语概念界定的基础上,从生态语言学、环境传播学、环境社会学、环境政治学、环境地理学、环境史学等多种学科视角回顾了环境话语的研究成果,重点阐述了环境话语分析的多种研究路径和基本观点。研究发现:基于环境话语跨学科研究的内在需求,环境话语研究具有超越传统学科框架的视野和开放性,需要研究者突破单一学科视角的固有认知与思维模式的局限。随着现代环境学科群的枝繁叶茂以及环境话语概念在不同学科的动态建构,环境话语将迎来更为广阔的研究前景。环境话语研究势必将语言学和环境科学的诸多分支学科聚合起来形成多学科交融、合作共赢的发展趋势,并最终构建出一个以研究系统化、多种学科结合为特色的环境话语研究框架。
诗词中的阙汗牛充栋,留存至今的阙却是凤毛麟角。中国存世的阙绝大多数修筑于汉代,现存汉阙45座,其中四川省24座,山东省11座,河南省3座,江苏省1座,重庆市6座,北京市1座,又以四川省最为集中,独占中国汉阙的半壁江山。四川的汉阙,广泛分布在绵阳、雅安、梓潼、芦山、德阳、夹江、渠县等地,其中,建于东汉建武十二年(36)的梓潼李业阙,是中国迄今年代最早的汉阙。
一个村庄,三座汉阙
2017年4月,我追寻色伽兰的脚步来到渠县,这里如今被誉为“汉阙之乡”,在渠县县城到土溪镇的路上,不足10公里的道路旁密集地分布着冯焕阙、沈府君阙、王家坪无名阙、蒲家湾无名阙、赵家村东无名阙、西无名阙六处七座汉阙,是四川汉阙最集中的区域。当年色伽兰探访过的赵家村,如今已改名为汉阙村,著名的冯焕阙就在村口,加上东、西无名阙,一个村里就有三座汉阙,在中国恐怕也无出其右了。
冯焕阙高4.6米,由顶盖、楼部、阙身、台基四部分构成,层层相叠,顶盖为重檐庑殿顶,其上雕有椽子、连檐、瓦当、瓦陇图案;楼部刻出栌斗、斗拱、方胜图案,正面两斗拱间刻青龙,背面刻玄武;阙身由整石雕成,正中书有两排飘逸的汉隶:“故尚书侍郎河南京令/豫州幽州刺史冯使君神道”。
四川诸多汉阙中,冯焕阙形体较小,却朴素归真,简单飘逸,色伽兰称赞它为“绝优美之物”,梁思成也赞誉“曼约寡俦,为汉阙中唯一逸品”。阙身的八分书隶书笔道细瘦,自由灵动,呈现出开张纵横、不拘小节的特点,是四川隶书碑刻的代表作。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评价为:“布白疏,磔笔长,隶书之草也”。
冯焕阙对面有个茶馆,今天是雨天,茶馆里挤了不少喝茶的乡民。留着八字胡须的冯光成一大早就挑了个敞亮的地方坐下来,叫了杯两块钱的“三花”。他跟我攀谈起来,“上小学那会,放了学我们就拿粉笔在冯焕阙上写字,老汉看到了就喊,‘这是祖宗留下来的,你乱画祖上会怪罪的’,村里都说冯焕是大官,他是冯家的先祖。”说到这里,他多少有点洋洋得意,旁边的乡民说他吹牛,他嘬了口茶,音调顿时高了八度:“冯焕是大官,不是大官能建石阙么?”
冯焕的事迹,《后汉书·冯绲传》略有记载。冯绲汉桓帝时曾任车骑将军,其父冯焕的传记附在《冯绲传》后。冯焕是巴郡宕渠人(治今渠县土溪镇一带),汉安帝时官至幽州太守,在任秉公执法,疾恶如仇,得罪了不少地方豪强。一天,皇帝突然下旨将冯焕收入监中,冯焕忧愤交加,意欲自尽谢罪,年幼的冯绲觉得事有蹊跷,他让父亲上书朝廷,结果是豪强伪造圣旨,意欲置冯焕于死地。真相大白,冯焕却已病死在狱中。公元121年,冯焕归葬宕渠,部属在墓前为他建立石阙,祭奠这位屈死的汉代忠臣。
蒲家湾无名阙则恍若“动物世界”,翼马、朱雀、三足乌、九尾狐、双头鸟、玉兔,这些天国中的神兽预示着墓主死后会进入一个光怪陆离的神话世界。如果没有雕刻,汉代无疑是一个遗憾的时代,汉朝人将宴乐、出行、狩猎场景雕刻在汉阙之上,给后人展示着他们的生活甚至梦想中的天国。
中国汉阙的扛鼎之作
渠县阙多,雅安阙精。雅安有高颐、樊敏两座汉阙,又以高颐阙最富盛名。高颐阙位于雅安市北郊的姚桥镇汉碑村,一座座拔地而起的楼盘中间,围了个仿古的院子。左阙仅存阙身,顶盖是后来加上去的;右阙高590厘米,就连附属的耳阙也保存至今,是中国现存汉阙中结构最完整,保存最完好的一座,在《金石略》《金石录》《舆地碑目》以及日本的《寰宇贞石图》《书道全集》,法国的《汉人陵墓艺术》中都有收录和介绍,被誉为中国汉阙的扛鼎之作。
高颐阙右阙为重檐庑殿顶,四隅有憨态可掬的角神,其下露出24只枋子头,每只上书隶书铭文,从正面左起,四面依次为“汉故益州太守阴”“平都尉武阳”“令北府丞举孝廉”高君字□□”。楼部、阙身以高浮雕、浅浮雕、线刻、圆雕等多种技法,雕刻车马出行图、鸟兽率舞图、季札挂剑图、夷人献宝图,以及三足乌、翼马、九尾狐等神兽。车马出行图再现了墓主生前出行的场景:墓主安坐在轺车之中,前有八名伍伯开道,身后还有骑马的小吏跟随。轺车是汉代官吏乘坐的车舆,按照汉朝定制,文武官吏出行皆有仪仗队随行,车马之前鸣声开道的步卒叫“伍伯”,《续汉书》记载,“车前伍伯,公八人,中二千石、二千石、六百石皆四人”,高颐官至益州太守,按制应有四名伍伯,阙上却是八名,无疑已是僭越了,这也是东汉末期王室衰微,朝廷礼仪荡然无存的见证。
阙主高颐不见于史料记载,汉碑村以前叫孝廉村,联系坊子头“举孝廉”的铭文来看,他是“举孝廉”走上仕途的。“举孝廉”是汉朝自下向上推选人才为官的制度,汉武帝元光元年初(公元前134年)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此后一直延续到东汉,两汉不少名公巨卿都是孝廉出身。高颐曾任益州太守,其地域大部分在云南省境内,夷人献宝图中那些赤裸上身、光头大眼的夷人,恐怕也是高颐为官一任的再现。
傍晚,村民牟岳恒领着小外孙到院子串门,他告诉我,小的时候,高颐阙在一个破败的八角亭里,周围是水田。牟岳恒望着眼前的高颐阙,点了支烟,围墙外,一座座高楼大厦正拔地而起,将院落层层包围,“楼房越修越多,地都被征走了,村里不少人都搬到城里去了,只有老人和高颐阙还在。”
楼盘多了,村里的建筑工人也多了,天快黑的时候,门口来了个年轻人,他叫董源,是附近楼盘的木工。董源是云南省鹤庆县人,鹤庆自古出木匠,他念过几年书,去年辍学跟着几个叔伯做木工,一个多月前才来到雅安。叔伯们下了班喜欢喝点小酒,董源则爱四处溜达,他偶然转到高颐阙,就被凝重朴实的斗拱迷住了。
斗拱是中国建筑特有的构件,“斗”是斗形的木垫块,“拱”是弓形的短木,拱架在斗上,向外挑出,拱端之上再安斗,形成上大下小的托架,环环相扣,如蟒蛇缠绕。斗拱通常位于大型建筑物柱与梁之间,它的出现,解决了剪应力对梁的破坏问题,不过它又堪称艺术品,象征和代表着古典建筑的精神与气质。
高颐阙斗拱粗壮笃实,与汉代建筑雄浑大气的特点一脉相承。汉代是一个稳定、富庶的时代,也是一个大兴土木的时代,是中国古代建筑第一个全面发展与融汇的时期。昔日宏伟壮丽的汉代木构建筑早已在漫漫尘世中化为废墟,高颐阙以准确比例刻出斗拱、铺作、仿子头,令后人得以管窥汉人的建筑样式、比例,如同一部刻在石头上的中国建筑史。
汉朝人的梦中天门
当年,从渠县离开后,色伽兰沿途拜访了梓潼贾氏阙、李业阙,绵阳杨氏阙,并留下了这些汉阙的存照。在梓潼县郊外一处树林边,贾氏阙被孤独地遗忘在旷野中,看起来如同一堆乱石,令色伽兰唏嘘不已。
贾公阙如今位于梓潼郊外的太平村,当地人称“书箱石”。传说三国时诸葛亮派马谡守街亭,走时匆忙忘带兵书,诸葛亮急派张苞送去,张苞在梓潼迷了路,心急如焚,气得蹬脚,两箱兵书堕地化为“书箱石”。《金石苑》作者刘燕庭曾得到贾公阙拓片,上书“蜀中书贾公”字样,不过眼前的贾公阙已斑驳得看不出字迹了。“张苞送兵书”是当地人口中津津乐道的民间故事,贾公阙的真实身份反而被淡忘了。
绵阳杨氏阙在老川陕公路旁边,双阙俱存,左阙高514厘米,右阙高521厘米,枋子头“汉”“平”“杨”“府”隶书铭文还隐约可见。南北朝时,佛教在中国兴盛一时,高挺的阙身便成了绝佳的开窟场所。工匠费力地铲掉阙身的“车马出行图”,开凿了密密麻麻的佛龛,那些穿着褒衣博带长袍的供养人也把自己以及族人、奴婢的形象刻在阙身上,不大的汉阙顿时变得熙熙攘攘,这也让古老的汉代建筑多了几分梵音。
此外,四川尚有德阳司马孟台阙、芦山樊敏阙、夹江杨氏阙、西昌杨佑阙等等。就阙主而言,冯焕曾任尚书侍郎、幽州刺史,沈府君为交趾都尉,高颐为益州太守,樊敏做过巴郡太守,德阳司马孟台阙主曾是“汉故上庸长”,哪一个都是响当当的人物,这也验证了史书中只有帝王将相、文武百官才能立阙的记载。汉代的长安,天子脚下的官吏熙熙攘攘,可以想象,这些冠冕一时的官吏死后皆会立阙,长安一带的陵墓阙的数目可能并不比四川少,只不过已在漫漫长河中崩塌损毁。“西风残照,汉家陵阙”,萧瑟的西风残阳下,汉家陵阙残寂寞无主,李白看到的,不仅是一幅绝美的意象,也代表着汉阙的某种境遇吧。
恢弘的陵阙注定只能属于达官贵人,汉人却在石棺、画像砖上刻下了无数汉阙的图形,这让学者们颇为疑惑,为何汉人会在生命的终点频频描绘汉阙的形象?四川简阳市鬼头山崖墓出土的画像棺上,双阙间刻有“天门”铭文,学者们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双阙是天门的象征。在汉人看来,死亡并不是生命的终点,而是另一种形式的开始,汉人无不希望穿越天门,到昆仑山拜会西王母,求得不死药,尔后自由地遨游在宇宙天地之间。
两千多年前,巍峨的城阙几乎出现在每一个汉朝郡县中,它们是汉代城市的象征,寓意着安宁、繁华,那些达官贵人死后也会竖立石阙,这是或许已是当时最体面的葬礼;而在汉人心目中,还有一座隐形的阙,它寓意轮回,象征不朽,它是人间与天国的分界线——跨过双阙,便成为天国的一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