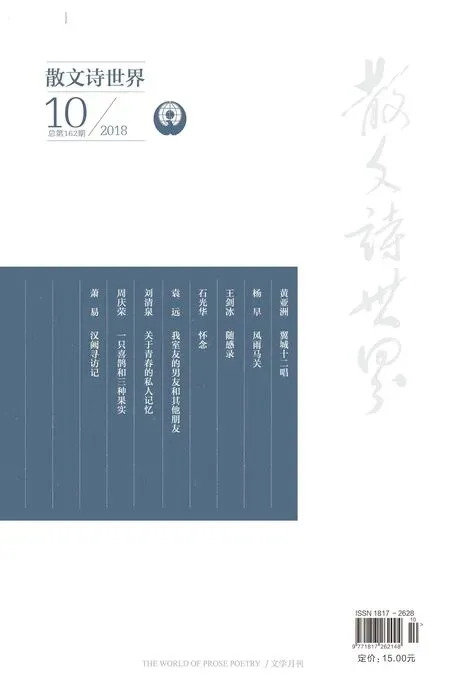我室友的男友和其他朋友
袁 远
1
我和布伦达是同一天搬入学生村6号院10号房的。
伊丽莎白港大学学生村是6座四合院似的院子,院里的房子皆为红屋顶的单层别墅公寓,房间分单人、双人和三人间三个型号。
10号房为双人公寓,我和布伦达各有自己的卧室,共用厨房、洗手间、浴室和客厅。布伦达是约翰内斯堡人,祖鲁族,学医药学。她个子高挑苗条,头发扎成一绺一绺的短棒槌。
那个时候我对黑人的头发已有所了解。从外貌特征上,黑人跟白种人和黄种人的最大区别,不仅在于肤色,还在于头发。
黑人头发极细极绒,犹如化纤和羊毛,比玉米穗更为轻和软,因此不易养长,也没有垂坠感。有的人头发稍长就自动一团一团纠结起来,成簇地立于头顶。也有女人将自己头发养到齐耳长,仔细梳得平整顺滑,但发梢却是向上翘起而垂不下去。黑人们在头发上用的工夫相当多,发式也花样百出,假发是最常用的美发用品,方法是把假发一绺一绺固定在自己真发的发根上,编成细长辫子,或短棒槌。编辫子的式样有多种,露出头皮和不露头皮的。露出头皮的又分竖杠、斜杠,看去就像田埂明晰的水田,发辫开始紧贴头皮编,到后颈处才撒开,整个头颅的形状因而也浑圆地昭显。编短棒槌也分为随意型和条理型,此类发型让头顶看上去茂密旺盛。另外是不用假发的发型,将细绒头发抓成小块扎紧,呈西瓜状,井田状,显出泾渭分明的头皮。头发被那样紧密地抓或编,看着总让我觉得揪心。不过问他们,没人说疼。还有人将半长头发直立梳在头顶,好像一团燃烧的褐色或黑色火焰。
所以我的朋友,另一个住学生村的中国留学生彭有次感叹,“哎,他们的头发真的是叫人叹为观止呀。”
当天布伦达的男朋友也来了。一个肤色较浅的黑人,斯文细瘦,一笑露出一口白牙。他的发型是最简单的那种,理得短短的只剩覆盖在头上的一层绒毛。后来我发觉这个简洁的发式倒很配他懒散、率真同时顽固的性格。
他对我说,“嗨,我叫如果(Zuko)。”
我一阵笑。如果。这名字的发音让我觉得好玩。不过我也知道,我名字的发音对他们也一样,肯定属于稀奇古怪的一类。
一直没取英文名。每次回答了叫什么的提问后,我总要做一番解释:Yuan Yuan在中文里是不同的字,不同的意思。有次一个黑人女孩,因为听到好些中国人的名字是叠音的,便问我,假如塞西莉(一个中国留学生)回中国后,是不是要被叫做塞西莉.塞西莉呢?
Zuko住在学生宿舍。那边的条件偏于简陋,房金也便宜。他当然喜欢往我们这边跑。进门只要见到我,必然笑眯眯郑重喊一声:“Yuan Yuan!”
我想Zuko内心里是得意的,因为他能把我的名字念得接近准确。而这两个字对很多人来说,属于高难度发音。
布伦达只喊一个字:Yuan。
布伦达性情安静,喜好睡觉。她的安静使我对这种同一屋檐下的合居没感太多不适应。Zuko话也不多。他和布伦达在一起时几乎没有打打闹闹的事,也很少展示亲密举动。两个都是有点羞怯的人。
2
搬入学生村三个月后,每套公寓都配上了电视机。安装电视机那天,布伦达简直抑制不住脸上的笑。布伦达对电视有着绝对的痴情,Zuko可以不必随时在身边,电视却是她时刻依赖的。早上起床后,布伦达的第一件事,是打开电视。中午一定要看完一场每日播放的脱口秀节目,才去赶下午的课。没课的时候,她会一心一意把时间全用来看电视,一副长相厮守永不厌倦的劲头。
有了电视后,Zuko天天过来。他们的夜晚全在电视机前度过。电视机使他们把沙发在功能上变为了床,两个人半躺在沙发上,盖上毛毯,对着电视一直看到头晕眼花非睡觉不可。
电视使学生村的生活走向有声有色,令多数人心满意足。同院的小伙盖来自苏丹,做过记者,总是一边看书一边看电视,并且也爱好盖条毛毯卧在沙发上看。布伦达极少在公寓里看书,公寓就是休息处,除非考试前,但只要看书她肯定是把电视也开着。就好像吃西餐的人喜欢用饮料将食物冲下喉咙,我的这些黑人朋友看书则必然用电视节目将书本内容送进大脑,一个道理。彭的同屋是肯尼亚人,据彭说也是不折不扣的电视迷,热衷过屏幕生活,并也以同样躺在沙发上的姿势和形式看电视。有的夜晚,肯尼亚小伙身上盖条毯子半躺在沙发上,可以对着那台声音开得极细微的电视,边看边睡地打发整个夜晚。
电视连续剧是布伦达的最爱。那些剧都是拉拉杂杂的都市剧,布伦达看得非常投入,诚心诚意地为人物命运担忧。傍晚我在与客厅相连的厨房做饭时,总听到她啧舌叹气,“哟,多丽丝,他是骗你的!”“唉,约瑟芬,别做傻事。”若听到某句有道理的话她便自己点头,道,是的,对的,唔。
Zuko天天过来吃晚饭,但他既不做饭,也从不洗碗。总是布伦达做好,把盘子端到电视机前的Zuko手上。我说Zuko,“你干吗不劳动啊,光吃不做心安理得吗?”
布伦达高兴地在一边点头赞同。Zuko一点没料到我竟然提出这种问题,他问,“中国男人做家务?”
我说当然,不做饭也要洗碗。谁让你要吃呢。
Zuko不吱声了。过一会儿,他想到了一个理由,对我说,“你看,将来我娶布伦达的时候,我要支付给她父亲20头牛。”
我说那有什么,就是付100头牛,该你做的你也要做。
Zuko分辩说,他也做饭的。布伦达也替Zuko说话,背后对我说,她到Zuko那去,就是Zuko做饭给她的。
不过因为那次谈话,Zuko认定我不理解非洲文化民俗,以后有机会他就歌颂南非,对我进行南非的爱国主义教育。我们俩唇枪舌剑,布伦达只在一旁笑。
某日布伦达的一个女友来了,滞留到晚饭时间。布伦达依然做的是两份饭,Zuko自己一盘,布伦达和她的女友合吃一盘。两个盘内的食物一样多。自始至终,Zuko也不问一句,你们够吗?
3
那些朋友来时,我们的客厅常常充满科莎语、祖鲁语、英语、别的什么语言或这些语言的混合语。南非有十多种语言,而他们每个人都是操几种语言的天才。Zuko说句科莎语,问我知道什么意思吗?我说不知。Zuko又说句祖鲁话,问我明白意思?我依然不知。Zuko就十分得意。我承认,跟他们相比,在语言学习上我是自愧弗如的。布伦达和我用各自的语言互教对方数数,我先用汉语念了一道从一到十的数字,布伦达说,怎么听起来像一个单词啊。我放慢语速再念一道后,布伦达就可重复到六。而布伦达用科莎语一个数一个数教我,等她教到十,一的发音我又忘了。如此教了两遍,都是学到十,忘了一。
我自己找的理由是,科莎语的数字都是多音节发音,而且发得古怪,也怪不得我学不会。
至今我能说的科莎语也只是一个“摩罗(你好)”。而在伊丽莎白港,自从中国留学生一拨一拨来了后,随处我们都能听到迎面而来的黑人用汉语打招呼,说“你好”,“早上好”,“下午好,”“你很漂亮”,以及“谢谢”,“别客气”。这几句汉语几乎成了某种范围里的一种普及的公共用语。惊人的是一次我在电脑设计室做海报设计的作业,等我弄完要离开时,旁边一个戴耳环的黑人男生突然用标准的汉语完整地问了一句:“你要回家了吗?”
到我们公寓来找布伦达或Zuko玩的人,最爱问我的问题是,你会找个黑人男朋友吗。我不知道。这个回答不让他们满意,但我无能为力。一个叫久久(Jojo)的小伙子跟我们同一个院,他的房间在我们的斜对面,中间隔着草坪。那晚他待在我们的客厅聊天,又有人跟我提到黑人男友的问题。久久说,“我还没有女朋友。”见我没有反应久久又说,“我想找个中国姑娘做女朋友。”
Zuko在一旁帮腔说:“这里就是一个。”
我故意不懂他什么意思。
Zuko的中介不成功,但久久毫不介意。久久是个热情开朗的人,那次熟起来之后,只要看见我站在房间门外抽烟,他必然隔着老远大喊一声,“又在抽烟!”然后穿过草坪走过来,和我聊会儿天。久久苦口婆心地劝我把烟戒掉,他喜欢跟我谈什么是幸福生活。
有段时间我没看见久久。一个周六的中午,我搬了张椅子到门外,坐在阳光下吃午饭。久久那边的房门打开了,久久走出来,见我大声问候,“你好吗?”他跑过来,我们天南海北说了一阵话,突然久久告诉我,“我妻子现在和我住一起。”
我忍不住大笑。尽管知道这里好些人喜欢把关系确定的女朋友叫做妻子,但久久这关系也来得太快了。我说,“你一个多月前还在找女朋友呢,现在就有妻子啦?”
久久说是啊。理所当然的神情。结束谈话时久久说:“享受你的午餐。”
我说:“享受你的妻子。”
久久本来已经转过身去,闻言又转过来,大张着嘴,问:“怎么享受?”
我又一阵笑,久久也笑。我说:“那是你妻子,你问我怎么享受?”
4
不知从何时开始,每到周六的夜晚,布伦达和Zuko就玩起了一种奇怪的游戏。半夜Zuko不停地打电话进来找布伦达,而布伦达又偏不去接他的电话。电话铃在客厅里响,布伦达的卧室门却紧紧关闭。电话铃一直响,挂断后又响,挂断后又响,我只好去接,然后叫布伦达听电话。两次后,布伦达说,不要去管那个电话。
我并不想去管,但那铃声完全是不到黄河心不死的架势,吵得我无法入睡。他们之间估计是闹了情人间的小矛盾,可为什么总在周六?Zuko身上看不出的固执在打电话这个事情上表现得十分显著。如果电话不被接起来,他会让电话一直响,甚至响一刻钟。再不被接听,他就让电话歇半秒钟又响,歇半秒钟又响,反正是不断地打。一次我实在忍无可忍,拿起电话第一句话就是,“你疯了吗?”第二天Zuko见了我,马上对我道,“你疯了吗?”
接下来的一个周末,凌晨不到1点,Zuko的电话又来了。我告诉他布伦达不在,可能在她哪个女友那儿。等我刚回到床上,电话又响了。Zuko再次表示找布伦达,我说我已经告诉你了啊,她不在。再次回到床上,还没躺到两分钟,电话跟那死不了的妖怪一样,嘟嘟嘟地又叫了。
我坐在床上。电话铃一声一声,不紧不慢地叫。我跟那声音对峙着,看谁抗得住。大约10分钟左右,它总算断气了。我下床走出卧室,到客厅电话机那正准备拔掉电话线,门上突然响起辟辟剥剥的敲门声。Zuko在外面说,“是我,Yuan Yuan。”
我无可奈何,再说什么也是无用的。Zuko直接走到布伦达卧室,他开始敲门。他轻轻地,耐心地,持之以恒地敲。他停了下来,不一会儿他又在敲布伦达的窗户了。他敲会儿窗户,又过来敲门;再去敲会儿窗户。我心里怀着气恼佩服这个家伙,他怎么做得到完全不顾屋里没人的事实,好像只要不停地敲,布伦达就会突然变出来,为他把门打开。
那一次 ,Zuko孜孜不倦折腾了一夜。以这种方式打发周末之夜,对谁都不是个美妙的事。比较起来,布伦达在两个人的相处上则显得从容自在一些。假如Zuko几天不现身,或者周末也不过来,她从来没有非要找到他,并因此声讨他的举动。还是那么雷打不动地自己看电视,一副安安稳稳自娱自乐的样子。
不管怎么说,布伦达和Zuko都是恩爱的一对。他们希望尽早结婚,建立一个孩子成群的大家庭。Zuko希望有12个孩子,考虑到生活的压力,又把数字减到6。布伦达对家庭主妇的角色满心盼望。药剂学专业?那算什么呀。
5
只有一种情况Zuko对呆在我们的客厅毫无兴趣,那就是布伦达做头发的时候。几个女孩前来为布伦达编满头细辫子,那会是从下午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凌晨的工作,她们边吃东西边弄头发边聊天。这个时间是一点都不夸张的,我问过另一女孩,她的满头辫子是在美发馆做的,4个美发师用了7个小时时间来完成那个工作。
我服气的是她们的耐心。做一次头发的时间简直比做一次大手术的时间长出一倍。这样的头发怎么洗呢,女孩们说,通常的洗法呀。花那么大力气编出的辫子,布伦达也就保持两个月左右,然后也不拆,直接用剪刀嚓嚓剪掉。反正都是假发编的。下一次想换发式了,再买假头发,再花个十几小时做就是了。
到11月下旬放长假,大家都得搬出学生村,那些小别墅都要作为临时的假日公寓出租给旅游者。我和布伦达的合居也就结束。来年我不再住学生村,不过好几次在学校电脑室碰到Zuko,他依然那么笑眯眯喊一声我的名字。
很少见到布伦达。想必她还是那样,整天坐在电视机前,津津有味享受她那由一张荧光屏传递出来的有声有色的室内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