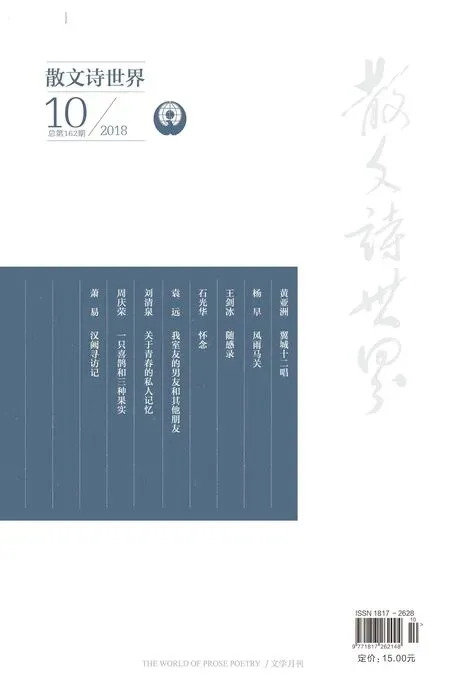弄溪桥 外四章
郭 辉
弄溪桥
那一尾无名野溪, 若一管玉笛, 在野草野花的清香深处, 在野雀子一忽儿高一忽儿低的自恋症里, 尽日横吹。
而你呵, 小小的青石板桥, 多像是按在绿水之上的一根指头。
桥面上过尽人寰, 有太多的风尘。
唢呐声中, 你把玩过许多新嫁娘的大红花轿。
每一次都喜在眉梢, 又不无担忧, 总会悄悄地告诫一句: 娘子, 从这里过去,就是一生的悲欢。
有去无归的黑漆棺木, 也时常由此经过。
你非奈何挢, 却有着更多的悲悯, 不落泪,不念佛, 打一个拱手相送——来生山高路远,请兀自珍重!
装着猪崽崽的独轮车经过, 你硬起筋骨,让它走得又平又稳。
挑了两篮竹笋的村妇, 蹒跚而至, 你目带期许, 唯愿闹市有众多的手,尽早剥出笋衣里,嫩白嫩白的春光。
最盼望的是那些色彩纷呈的书包。
蹦蹦跳跳来到桥上时, 你就会情不自禁,露出一脸无声的笑, 仿佛是被一双双小脚丫子,搔着了痒痒。
——踩重些, 踩踏实些, 前头的路, 还远着呢……
弄溪桥, 这乡土的昵称呵, 野性缠绵, 野味悠长。
其实, 你从不戏弄人间, 只是把所有来来去去的生活, 悉数倒入绿得发蓝的波心, 荡开来千朵万朵纯朴的意象。
远离了清水和浊水
堤堰越筑越高了, 河有了肩膀,水有了锁骨。
却见一条烂尾船, 横躺在河坡之上, 了无生气, 就像是一具苍老的干尸。
裸露着是羞耻的。
可是它呵, 无法不向天, 向地, 向人世,摊开自己一辈子的辛酸。
惊涛拍岸,落木萧萧。
它像一扇张开的耳朵, 悉数听到了。
可是, 谁能听到它无声的歌哭呢?
——那么多酸甜苦辣五味杂陈的感慨, 全都被晾在身下一块块冰凉的石头之上, 打着寒颤, 起了霉斑。
嗅觉灵敏的河风, 还一定闻到了, 它从头至尾, 那一枚枚被岁月锈透了的扒钉, 发出的冷冷铁腥味, 那么枯涩, 那么刺鼻!
是在回味自己的痛感, 还是在追思曾经的荣光?
我走近前去, 站在这一只船的前世今生和宿命里。
默然, 怅然, 惶惶然。
从上往下看, 它活似一只巨大的敞口鞋,所有的承载和抱负, 都已然随着逝水东流了,而今, 只剩得行迹沓沓, 岁月空空。
从下往上看, 它分明是粘贴在长堤上的一块小补丁, 从此远离了清水和浊水, 却无法缝合世事沧桑。
鱼形山
头在那里拱着,尾在那里摇着,身子却被一堆白云拦腰截断,仿佛游历了天下的沧桑,犹未脱离苦海。
嘴与腮似乎仍在开合,吐无形的水泡,吐日月星辰和逃不过的命理。
山体背负着青天,两翼是次第排开的坟场。
全村先人们的墓,都镶嵌在显眼处,像一溜一溜的鳞片。
又像一枚枚偌大的图钉,强行按着了若有若无的风水,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哪一枚也不曾松开。
我从未谋面的叔外公,也栖居其间。
祖辈传下话说,人的三十六岁,是一道大坎。
无妻室儿女的叔外公,果真就栽在这一道坎上。
那一天他过生日,家徒四壁,已然没有一粒隔夜粮了。又饥又饿,莫可奈何,只得去找人家借。
出得家门,走到河边,竟看到了一条翻着白肚皮的鱼。
想也没想,他就跳下去了。谁知道那是一条前来催命的鱼,收魂的鱼!鱼未捡到,口福没享到,他却溺水而亡。
多少年过去了,叔外公的那座坟,依旧爬伏在鱼形山上,只是越来越小了,越来越矮了,就像是标记着那些不堪岁月的一个句号,正在日渐淡化,没入虚无。
鱼形山呵,鱼形犹在,山殇在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