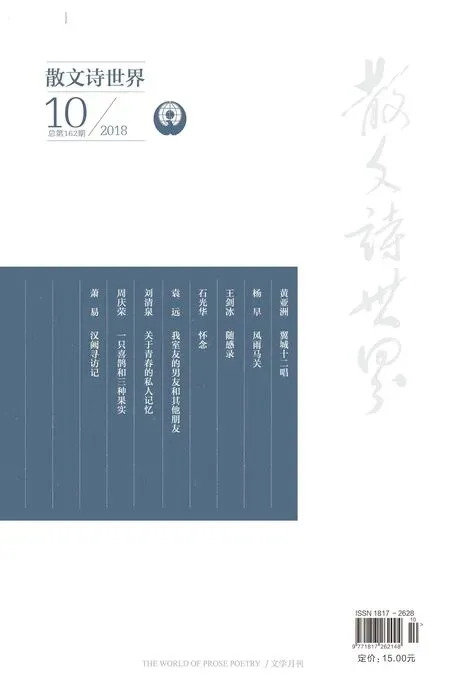都江堰·外河的石头
金指尖
1
内河灌溉,外河泄洪。
作为人类对自然的干预,更多时候,都江堰外河,石头多于水。
石头,在河床睡觉。
洪水留下的狮子在睡觉,铁在睡觉,钙在睡觉,河堤在睡觉……
内河灌溉,外河泄洪。
自从修建紫坪铺水库,更多时候,都江堰外河,干净而安详。
石头,像一枚勇士的骨骼。
这些远古诞生的婴儿,时间的遗产,面对诗人,展露微笑。
这是2014年5月一个下午,一场小雨来了又走了。
我们在变轻,携带的山色和雨量,也在变轻。
当阳光小心翼翼,经过外河时,我正在河床翻捡。
我发现:石头的脸,比我干净。
2
茶,续了一遍又一遍。
整个下午,我都在沉吟:这些偃伏的石头,隐藏了怎样的野心?
这些洪水擦亮的战士,
怎样把哭泣还原为荡漾的笑声,怎样把落水的光阴还原为春天?
石头们一声不吭。
它们,在干涸的河床继续偃伏,那么安分,安分如立地成佛之心;
那么干净,干净似没有一丝杂念的眼睛。
它们以慈悲立世,存大爱于天地间,两千年不归不隐。
但更多时候,我在幻想,在审视洪水的阴谋。
也许当洪水再次咆哮,我刚好学会偃伏,学会石头们的睿智。
3
已经习惯了外河的石头,习惯了冷;
习惯了站在它们中间,眺望秦王郡坚韧的
斧铖和铿锵,眺望先贤们留下的智慧和汗水。
已经习惯了外河干涸,习惯了紫坪铺水库;
——干涸是外河的大道。
习惯了坐在堤岸上,欣赏一河精致的石头。
像成群结队的女人,裸露干净的肌肤。
我跟石头们点头,跟石头们攀谈,向石头们学习赞美……
但我拒绝愚蠢的举动。
4
谁不希望温柔地靠岸?
止步天堂门前的石头,存放于众多石头中间。
所有锋芒,都隐藏于体内,这似乎,来自于更久远的人间。
每次翻捡,都让我想起逝水,那些向前翻开的日历,那些翻涌后的白云。
我不能简单地,把石头概括成花儿。
我敢肯定,在都江堰外河之外,在生长芦苇的地方,石头听得见水中,一场又一场葬礼。
独善其身,不是河水带走的花朵
也许二十年、三十年后,我们也将住进石头中间,与它们一起怀念,那些逝去的水。
但我更愿意,流萤三千,比翼一只蝴蝶止于水的飞翔
5
美人和石头,是外河最精致的风景。
当诗人抛开幻想,试图变成一堆精致的石头;
当手捧石头的人爱上干净,手捧茶杯的人爱上蓝天、白云;
我终于找回了丰饶的肉体,找回了美人和荡漾。
我希望,被闪光灯安置的,不是一张过客的脸,被石头们射中的,不是最后的靶场。
我相信,这些偃伏二千余年的水的骨头,每一枚都有一个动人的故事。
我温暖地想到了炊烟。
但我不敢确认,保持最后的尊严,是人间向善的途径,或有着天穹私募的背景。
飞花和水袖,或大于沧海;
或小于一粟。
但我确信皮肤上的盐,有恒定的光明向恶,向善?
如果天空继续空着,请学会辽阔。
不爱江山就爱美人吧!
你看,那一枚外河的石头上,美人在座;
一朵闲云与两只野鹤,成了绝配。
6
火中的石头叫钢;水中的石头还叫石头。
这些隐藏在洪水中,一次可以,撕裂一万头大象的,狮子、老虎、猎豹,野牛或者狼……
当我们津津乐道一条干涸的河床时,岁月正在掉漆。
暴雨锁不住我们的脸
湿淋淋的天空漏掉了多少人的灵魂?
不得不承认,软体的浊浪就是一个虚拟的骑士。
伤口只是洪水留下的一部分。
不得不承认,每个瞬间的疼痛都在证明,刮骨疗伤的真理 。
在石头里寻找江山。
在岁月里保持深度。
翻捡石头的人,相信水里有道;翻捡弱水三千,找到了石头隐藏的绝技。
7
心地大善,方可入药。
这是二○一四年五月一个雨后的下午,一群诗人站在外河堤岸上口吐莲花:
让我们以一纸春色为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