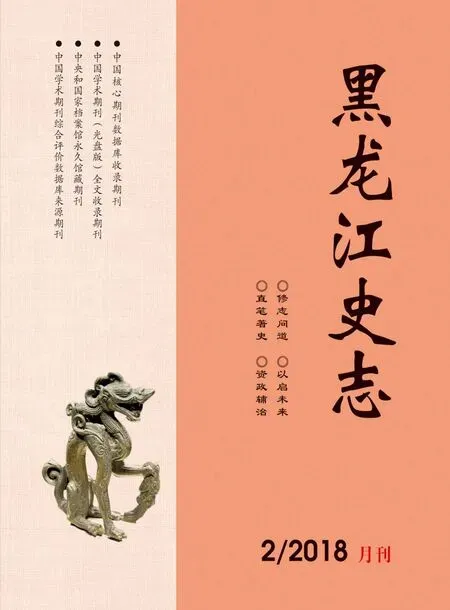论王阳明的天理史观
杨 灿 韩金晶
(贵州大学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 贵州 贵阳 550025)
“天理史观”所探讨的内容主要有心、性、理、气等概念的社会政治化和理学家经邦济世的价值导向。前者是从太极到男女到万物的空间维度,后者是依道统而展开的具体历史中的时间维度。缺少任何一种维度,其天理思想体系都将崩陷。目前,学术界对“天理史观”略有涉及,如任继愈《中国哲学史》(人民出版社,2014版)一书中专门谈及宋明时代的“唯心主义的天理史观”,张岱年《中国哲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中也出现了“天理史观”一词,萧父、许苏民《王夫之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版)一书中也提到了“天理史观”。对王阳明“天理史观”的研究而言,除王勇《论王阳明的社会历史观》(湖北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一篇论文之外,尚称阙如。这与王阳明在明代思想史上的重要性不太相称,所以本文试图以王阳明的良知说为基础,来分析其历史观念。
一、良知说:宇宙万物运动法则
理学家都以“理”为宇宙万物运动法则,对此王阳明也是承认的。他认为自然界万物的运动法则和成圣修养都有法则可循,因此他认为天地万物的产生皆是因为有理的存在。朱熹所谓“理”,既是物理又是性理,把自然规律和道德原则合而为一,变成一个无所不包的“太极“之理。而王阳明主要是讲性理,并认为理在心中,因此不必向事事物物上求理。正是心中有理,才能视、听、言、动。“心”不仅是人身体的主宰,也是天地万物的主宰;而心的虚灵明觉也就是它的本然良知。这就是王阳明的良知说。
王阳明以“良知”为天理,而“良知”人人具有,故人人心中都有天理境界。“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1)心的本体是“天理“。”心之本体即是天理,天理只是一个,更有何可思虑得?天理原自寂然不动,原自感而遂通。”(2)所以”天理“就是”良知“。王阳明认为“良知”存在于人的心中,“良知”就是是非之心,是不用学就会的东西,是天生固有的。“是非之心,不虑而知,不学而能,所谓良知也。”(3)
王阳明认为良知产生了天地、万物,世人只要一心一意的致其良知,自然就可以把天地万物视为一体。因此他把“良知“看成宇宙本体。“良知是造化的精灵。这些精灵,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从此出,真是与物无对。”(4)“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天地无人的良知,亦不可为天地矣。盖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其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5)天地万物都离不开人的良知,天地万物和人原本是一体的,所以五谷禽兽可以养活人,药石之类可以治人的病,这就是因为万物的气是相同的,所以能够相通。
王阳明认为良知具有伦理道德的观念,是人立身行事的法则。在不同的层面和状况下,其内涵可作不同的规定。良知的内涵,主要是忠、孝、信、仁等伦理道德规范、原则、原理。王阳明认为事父、事君的忠孝之理都是从自己的本心即良知上去求。心的本体是知,这里的知,就是指良知。“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侧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6)认为孝、忠、信、仁之理都在吾心,是不用向外界去学习就知道的良知之学。他将朱熹道德形上学的理从心外移植到心内。他异常鲜明地强调,仁、义、礼、智、纲常伦理的“天理”不是某种外在的东西,而是统统来之于人的本心。而且,由于道德主体是用“良知”去事君事亲、仁民爱物的,因此,社会秩序、天地秩序所遵循的“理”,均是“良知”的产物。
王阳明认为良知是社会政治的根本。王阳明认为朱熹向外界学习的“格物致知”导致“心”“理”为二的弊端产生,从而也使一些士大夫言行不一,霸道横行,因此,提出他的“良知说”。在他看来,朱熹把理排斥在心外,王阳明企图使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合而为一,回归到其本然的良知之学,抨击“外心以求物理”。“夫物理不外于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无物理矣。遗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邪?心之体,性也,性即理也”。(7)“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8)同时他的良知说也是针对自己的处境与当时的社会状况提出的。当时,在学术方面,明中叶的士大夫和官吏均尊奉程朱理学,他们满口仁义道德,私底下却贪赃枉法,见利忘义。口中讲的和做的完全相反。王阳明认为,脱离良知,分心与理为二,则是造成上述现象的根源。同时,王阳明以良知为出发点,认为“如五伯攘夷狄,尊周室,都是一个私心,便不当理。”(9)世人对他们的评价高,是因为只注重表面,没有从良知出发,分心与理为二的缘故。因此,他认为要在心上做功夫。把良知作为其宇宙规律变化发展的出发点。他以为这样便能消除冲突和王霸。
二、道统论:社会发展的人文动力
从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来看,理学家认为不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等政治人物、不是二十四姓之家谱,也不是普通民众,而是社会中作为道德人文力量的圣贤君子,正如孔子被尊为“万世师表”,是国人从庶民到帝王皆应取法的师长。这种道德人文力量在理学中逐渐形成一种谱系。王阳明所谓的道统不明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学术上来看,到了孔、孟之后,不管是教育者还是学者,都不在重视发明本心的良知,而是转向外在的浮华之学,导致学派繁多,无所适从。“孔、孟既没,圣学晦而邪说横,教者不复以此为教,而学者不复以此为学。……于是乎有训诂之学,而传之以为名;有记诵之学,而言之以为博;有词章之学,而侈之以为丽。”(10)这里的“此”指”本心”。因此,王阳明认为华而不实的文风是导致天下混乱的原因,人们只求在世上出名而没人懂得敦厚自己本性之善,躬行实践。“天下之大乱,由虚文胜而实行衰也。”(11)王阳明把政治上沽名钓誉,相互攻讦,自私自利的行为,归结为当时的良知之学不明。
王阳明的道统说,至始至终都贯穿着其“良知”之学,以其为出发点,阐述了三代所教化和学习的,就是这些人性本来所固有的本心,不需要求助外界东西。“孝其亲,弟其长,信其朋友,以复其心体之同然。是盖性分之所固有,而非有假于外者,则人亦孰不能之乎?”(12)王阳明认为圣人教化的主要内容是:“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而其中的细节明目主要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13)这都是他的“良知”之学的内容。
道统通过儒学人物的序列,将儒学学理与现实政治紧密地联系起来,是儒学在教化层面的具体展开。(14)在《原道》一文中韩愈认为这个人物序列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以及孔子、孟子。孟子之后,道统中断。宋代理学家尤其是朱熹举周敦颐和二程等人继孟子之后,进一步完善了这样一个道统谱系。关于王阳明的道统序列,孟子之前和宋明时期朱学派理学家基本相同,但王阳明把贯穿道统的十六字心传理解为他的良知学说,王阳明的道统人物序列如下:
首先,王阳明解释了孔、孟发明本心的道统内涵。在《答顾东桥书》中,王阳明引用了孔子对子贡说的一句话。“赐也,汝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欤?非也,予一以贯之。”他认为这里的“一以贯之”就是“致良知”。同时他也认为“孔子气魄极大,凡帝王事业,无不一一理会,也只从那心上来。”(15)他也对孟子的“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从良知方面作出解释。在孟子所处的时代杨、墨之道盛行,孟子为阐明其以本心为出发的道统做出了很大的努力。
其次,王阳明认为“洙、泗之传,至孟氏而息。千五百余年,濂溪、明道始复追寻其绪。”(16)周敦颐的太极图说所谓圣人与天地合德。那么什么是圣人呢?他认为是完全保持固有的“诚”的人是圣人,时时通过思虑来恢复“诚”的人是贤。所以学人求达圣贤的“圣功”就在于“身端心诚”。(17)可见周敦颐也重视在心上下功夫。关于明道的所谓“天理“完全是自家体贴出来的,更是强调在本心上下功夫。
再次,陆九渊接续了程明道的道统。王阳明在调和朱陆的同时,也把陆九渊放入道统体系中,因为陆九渊的“宇宙即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和王阳明的“心外无理,心外无物”非常相似,把陆九渊放入道统,也是为自己寻找儒家道统合法地位做铺垫。针对陈九川对陆九渊的评价“看他论学,篇篇说出骨髓,句句似针膏肓,却不见他粗。”王阳明认为“然。他心上用过功夫,与揣摹依仿、求之吻义自不同。但细看有粗处,用功久当见之。”(18)可见王阳明认为陆九渊也是注重在本心上做功夫的。
最后,理学各派提倡道统,均号称接续孔孟,实际上是直指当下,将自身作为道统的直接承担者。(19)王阳明指出孔、孟道统核心是发明本心,他又把程灏、陆九渊放入其道统体系,实际上就是为承认自己是儒家道统继承人做铺垫。在《答聂文蔚(一)》王阳明说道“每念斯民之陷溺,则为之戚然痛心,忘其身之不肖。而思以此救之,亦不自知其量者。”可见他希望用良知拯救天下人的这种社会责任感。同时他把自己的处境和当时孔子的处境比较,承担起发扬光大良知学问,他希望天下人都能懂自己的良知,并希望聂文蔚能够帮助他一起实现他的良知学说,去掉自私自利,互相帮助,以实现天下大同的理想。
三、社会历史合法性探讨:王、霸、义、利之辨
王阳明同朱熹一样,认为三代之后王道衰落,霸道兴起,施行霸道的人,窃取与先王相似的东西,借助外在的学问来满足他们自私自利的欲望。人们只关注与利益、权谋有关的东西,一些儒者力图挽回先王之道,但由于“圣学既远,霸术之传积渍已深。”即使是聪明贤能的人也难免会不受影响。他们所做的“仅足以增霸者之藩篱,而圣学之门墙,遂不复可睹。”(20)徒劳无功,与先王之道越行越远。
他认为三代以前,“其治不同,其道则一”(21)。所遵循的天道准则是一样的。他和朱熹一样认为今不如古,历史是退化的,赞颂三代以及之前,认为“羲、黄之世,其事阔疏,传之者鲜矣,此亦可以想见。其时金是淳庞朴素,略无文采的气象。此便是太古之治,非后世可及。”(22)三代以前是远古圣人治理天下的太平盛世,不是以后的时代所能比的。一切以良知为出发点,是昌盛的时代,三代以后“因时致治,不能如三王之一本于道,而以功利之心行之,即是伯者以下事业。后世儒者许多讲来讲去,只是讲得个伯术。”(23)按功利之心去治理,是霸者的事业。人欲横行,良知流失,到春秋时已成为“礼崩乐坏”、“天下无道”的时代。他用一日来比喻三代之前和之后。“人一日之间,古今世界都经过一番,只是人不见耳。夜气清明时,无视无听,无思无作,淡然平怀,就是羲皇世界。平旦时,神清气朗,雍雍穆穆,就是尧舜世界。日中以前,礼仪交会,气象秩然,就是三代世界。日中以后,神气渐昏,往来杂扰,就是春秋战国世界。”(24)王阳明和朱熹出现类似的看法,是因为朱熹以天理为出发点,而王阳明以良知为出发点,在王阳明看来,天理实际上就等于良知。
王阳明的圣人史观。朱熹的“帝王“心术决定论”。朱熹在《朱子语类》中说到“盖天下之大根本者,陛下之心也……天下之事,千变万化,其端无穷,而无一不本于人主之心者,此向然之理也。”认为天下之事本于人主之心。而王阳明与其非常相似,在《传习录》中认为“人君之心,天地万物之主也,礼乐刑政教化之所自出也”。尧、舜三王能够推致自己的良知,所以老百姓对他们没有不相信的,因此实现了他们的圣人之治。“尧、舜、三王之圣,言而民莫不信者,致其良知而言之也。”(25)王阳明认为时势造英雄,圣人的作用十分巨大,但也受社会环境的制约。“周公制礼作乐以文天下,皆圣人所能为,尧、舜何不尽为之而待于周公?孔子删述六经以诏万世,亦圣人所能为,周公何不先为之而有待于孔子?是知圣人遇此时,方有此事。”(26)同时,王阳明也对三代以后的君主提出批判,认为他们被华而不实的文风所迷惑,即使有人想要奋起反抗有所作为,但所能做的也只不过是争夺霸主的功名利禄而已。“时君世主亦皆昏迷颠倒于其说,而终身从事于无用之虚文,奠自知其所谓。间有觉其空疏谬妄,支离牵滞,而卓然自奋,欲以见诸行事之实者,及其所抵,亦不过为富强功利,五霸之事业而止。”(27)
除了强调君主的重要性,对上古圣人作出肯定之外,同时批判三代以后的一些君主之外,王阳明也对历史上的一些人物作出评价。例如。他认为张良、黄宪、诸葛亮等人资质天生就清明,很少受到物欲的引诱,所以良知得到很好的发挥,自然离天道不远了。尤其是对王通给予较高的肯定。“张、黄、诸葛及韩、范诸公,皆天质之美,自多暗合道妙。……若文中子则又不可谓之不知学者,……如数公者,天质既自清明,自少物欲为之牵蔽,则其良知之发用流行处,自然是多,自然违道不远。”(28)而认为苏秦和张仪具有圣人的资质,他们的智谋窥见了良知的妙用,只是没有把它用在正道上。“苏秦、张仪之智,也是圣人之资。……仪、秦亦是窥见得良知妙用处,但用之于不善尔。”(29)司马相如因违背良知,迎合汉武帝的心意,作文鼓吹封禅之说,王阳明认为他是“盖欺天罔人,无耻之大者,君子之所不道,司马相如之所以见讥于天下后世也。”(30)这也是他被后世批评的原因。
除此之外,王阳明也用他的良知说,对一些历史事件作出评价。关于舜的不告而娶、武王的不葬而兴师,王阳明认为他们是“抑亦求诸其心一念之良知,权轻重之宜,不得已而为此”(31)。根据自己心中的良知,在权衡利弊轻重之后才这样做的。从良知出发,对相似的事进行了分析,认为杨、墨施行的是假仁假义,而且反对乡愿。认为尧舜施行禅让制天下大治,子之施行禅让制,导致燕国大乱,汤、武放伐夏桀、纣王是对的,而项羽杀害义帝失去人心。周公辅佐成王平定叛乱是对的,而王莽、曹操的摄政与辅佐实际上是篡位。王阳明认为统治者不能只注重外在的东西比如修建明堂等,要注重从内心教化民众。以”以不忍人之心而行不忍人之政,则虽茅茨土阶,固亦明堂也。(32)”反之,即使拥有明堂也是实行暴政的场所。
注释:
(1)(明)王阳明:《王阳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45页。
(2)(明)王阳明:《王阳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58页。
(3)(明)王阳明:《王阳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79页。
(4)(明)王阳明:《王阳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04页。
(5)(明)王阳明:《王阳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07页。
(6)(明)王阳明:《王阳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6页。
(7)(明)王阳明:《王阳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42页。
(8)(明)王阳明:《王阳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页。
(9)(明)王阳明:《王阳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21页。
(10)(明)王阳明:《王阳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55页。
(11)(明)王阳明:《王阳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7页。
(12)(明)王阳明:《王阳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54页。
(13)(明)王阳明:《王阳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54页。
(14)王胜军:《清初庙堂理学研究》,长沙:岳麓书社,2015年出版,第9页。
(15)(明)王阳明:《王阳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14页。
(16)(明)王阳明:《王阳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27页。
(17)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43页。
(18)(明)王阳明:《王阳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92页。
(19)王胜军:《清初庙堂理学研究》,长沙:岳麓书社,2015年出版,第91页。
(20)(明)王阳明:《王阳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55页。
(21)(明)王阳明:《王阳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9页。
(22)(明)王阳明:《王阳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9页。
(23)(明)王阳明:《王阳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9—10页。
(24)(明)王阳明:《王阳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15—116页。
(25)(明)王阳明:《王阳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79页。
(26)(明)王阳明:《王阳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2页。
(27)(明)王阳明:《王阳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56页。
(28)(明)王阳明:《王阳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68—69页。
(29)(明)王阳明:《王阳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14—115页。
(30)(明)王阳明:《王阳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53页。
(31)(明)王阳明:《王阳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50页。
(32)(明)王阳明:《王阳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