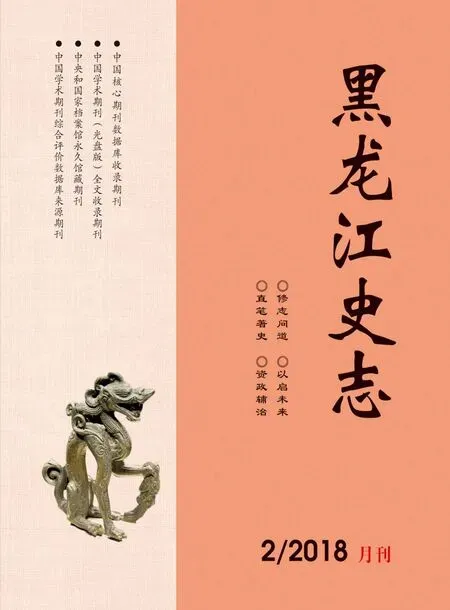《容美纪游》的“美政”向往情怀
黄映梅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美政”理想是“中国古代士人普遍追求的文化模式”(1),先秦诸子中,儒、道、墨等家纷纷著书立说,或托于上古,或寄于预言,描摹本派主张的理想政治情景。到战国后期,“美政”追求的贵族代表屈原,更明确提出:“既莫足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自汉代儒学确立官方正统哲学以来,儒家“美政”思想即成为士大夫的主要政治追求,想要“通过审美化了的道德教化,最后达到一种美善相乐之境”(2)。在这一政治哲学的指导之下,士大夫对于平民百姓负有自然的“教化”责任,是士人从政追求的最高成就,也是评判他人政治成果的重要准绳。
一、顾彩与《容美纪游》的写作背景
(一)容美土司概况
容美土司是今湖北恩施境内历经千年的古老土司之一,“容美古有柘溪、容米、容阳诸称,辖地甚广,今鹤峰、五峰、长阳三县之大部,及建始、石门、巴东、恩施等县与之接壤的边缘地区均属之。其地崇山峻岭,危关险隘,为古巴人后裔土家族聚居地。”(3)在明末清初之际,容美土司实力达于极盛,周边地区的桑植土司、高罗土司等无不与容美土司修好联姻,或者被打败。容美土司统治的中心区为今恩施州鹤峰县县治容美镇,鹤峰县境内尚有许多土司时期的建筑遗址,鹤峰人民的记忆中仍有许多关于土司的传说。
《容美纪游》成书之际,正值容美土司史上最强盛的统治者田舜年的统治时期,据《容美纪游》的记载:“宣慰使田舜年,字眉生,号九峰……爱礼客贤,招徕商贾,治军严肃,御下以简,境内道不拾遗,夜户不闭。”(4)表明了顾彩进入容美土司地区之时,正是司内政局稳定,实力较强的时期。
田舜年在清朝初年以土司的身份统治容美地区,而他本人在年幼时候长期寓居荆州,受到良好的汉学教育,曾经立志通过科举考试跻身帝国政治之流,但是屡遭失败。他一生嗜好著述,既写诗文,又修家史,一生著述包括《容阳世述录》《廿一史篡要》《六经撮旨》等数种,且将田氏家族中以往历代诗人及自己的诗作汇编成《田氏一家言》,现有部分留存。因此,田舜年是当时帝国西南土司之中汉文化程度较高的代表(其子田炳如似乎就不善于诗文)。
(二)顾彩与《容美纪游》的写作背景
本书的作者顾彩出身于江南名镇无锡。随着整个江南地区在帝国统治中占据的经济、文化中心地位,无锡甚至一度在帝国的学术地位与政治抗争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明末时期的东林党,就是顾宪成、高攀龙等人士以家乡东林书院为讲学中心的所形成的一个士人议政集团。这一以政治追求为目标的文人党社实际上直接开创了以地域为特征的地方文人势力集团之间的斗争,到后来演变为轰轰烈烈的以与宦官斗争为主的明末清初江南党社运动。(5)
顾彩的父亲酷爱书籍与收藏,据称“江南藏书之富,莫过于常熟钱宗伯家,次则锡山顾氏……其先人遗者,仅二百卷,而后所收乃逾万卷,其著述则自辟疆园选应制文行于天下,而日本、朝鲜、交趾、辰韩之属无不购传之,其盛如此。”(6)由此可见,清初无锡顾氏正如后来康熙年间的江南曹氏一样,是名副其实的书香之家。
但明清易代之际,书香之家尤其难以支撑,随着满清政府在整个中国的统治的逐步稳定,江南士人受到严重打击,顾彩的家族在这一时代背景之下急速衰落,等到他成年之时,家族已经近于凋零了。
年轻的顾彩为家计四处奔波,虽则才华满腹,但似乎并无意于科举功名。最终在好友孔尚任的引荐下,顾彩受聘为山东孔府西宾,获得中原士人艳羡的崇耀学术地位。顾彩生性淡泊名利,孔氏后人评价他说:“天石以南国衣冠之后,声名满尘寰,足迹遍海宇……人有讥其负盛气,矜名节,蹈狂,白眼傲世而不乐为世用者。而余之重天石者正在此也”(7),足见其高洁之心。
1703年,顾彩因事前往与容美土司辖境东部接壤的枝江县,其时,枝江县令孔振兹正是山东孔府后裔。此时的顾彩固然受到容美土司“桃花源地”传说的吸引,且一方面得到容美土司田舜年的邀请,更加上枝江县令孔振兹的鼓励,因而决定“涉奇险”游历容美,并留下十分珍贵的地方史文献《容美纪游》。
二、《容美纪游》所体现的美政向往情怀
(一)对于土司主田舜年的想象性记录
在《容美纪游》的开篇,顾彩即以极赞誉的言辞描述了一代贤主田舜年,称其“爱礼客贤,招徕商贾,治军严肃,御下以简,境内道不拾遗,夜户不闭”(8),但事实上,在田舜年治理之时的容美土司政局,至少有如下三个问题是不符合顾彩的政治理想的:一为父子不睦;二为刑杀太重;三为“独立思想”浓厚。
首先,在土司府乐舞问题上,田舜年与其子田炳如发生了很大分歧,据《纪游》记载:
“女尤皆十七八好女郎,声色皆佳,初学吴腔,终带楚词。男尤皆秦腔,反可听。所谓梆子腔是也。丙如自教一部为苏腔,装饰华美,胜于父优,即在全楚亦称上,然秘之不使父知,恐被夺去也。其二女皆剃发如男装,侍立如小校,丙如之行眷也。丙如欲觞余,必嗣君移于别署之夕,乃出以侑酒,戒下人勿得泄。仍布人侦探,恐父至,则匿之。君喜人誉其女尤,客之谀者必盛言丙如女尤之劣,以为万不及父。君则曰:‘彼字且不识,安责知音!’及观丙如戏,又言太都爷行头潦倒,关目生疏,不如主爷教法之善。丙如辄曰:‘老父固强为知音者’,有识已知其父子之不和矣。”(9)
此一事中,司主田舜年对自己继承人的评价“彼字且不识,安责知音”,失去慈父风度;而田丙如作为司府长子,背父藏匿戏班,且在家臣甚至是顾彩这样的远客面前评价自己的王父“老父固强为知音者”,父子二人言行均违背了儒家思想中对家庭理想的追求。但顾彩没有就此事作出更多评价,仅仅指出“有识已知其父子之不和矣”。仅仅在顾彩离开容美土司3年以后,田氏父子即因王权之争,引起严重内斗,田舜年亲赴武昌省府申诉丙如罪过,反遭拘禁,困死狱中。顾彩在1706年以后的文章诗词都没有反应他对此事的看法,但聪慧如他,其实早已预料父子反目。
其次,在田舜年的治理境内,刑杀过重,顾彩对此十分重视,并一直极力劝阻,顾曾在游记中详细记述容美土司的刑罚:
“其刑法,重者径斩。当斩者,列五旗于公座后,君先告天,反背以手擎之,擎得他色者皆可保救,唯黑色则无救。次宫刑,刑者即为阉官,入内供役使。次断一指,次割耳。盖奸者宫,盗者斩,慢客及失期会者割耳,窃物者断指,皆亲决余罪则发管事人杖责,亦有死杖下者,是以境内凛凛,无敢犯法,过客遗剑于道,拾者千里追还之。”(10)
儒家政治自先秦以来便主张以教化为主,刑杀应尽量轻简。容美土司的这些刑罚在顾彩看来无疑是十分严重的,在土司府内时,顾彩也一直尽力劝解。但顾彩亦没有就此问题发表过多的看法。
另一有关误医和偷盗罪的记载:
“在中府日,有袁和尚者,百斯庵僧也,少时为君伴读,后为僧行医,偿误方杀人,君命收其药具,戒子弟勿得延之。三月,丙如子病私用其药而愈,君怒切责丙如,必欲以违令杀袁,袁窘求救于余,余从容为言违令虽当斩然昔杀人而今救人,是其奉教进益处亦可赎也。君乃以余居停,故免死,逐出郡城,令住小昆仑,仍命读书三年,方许行医。不数日,又有九寿儿者,阉人也,盗君猞猁狲裘,割去裹,鬻其皮于梅相公。梅相公者亦浙人也,君之客,梅初不知而贱值买之,后九寿儿事破,梅渐俱,自缢死。君初无意杀九寿儿,怒其致客于死,始欲杀之,余往救已无及,至今怅怅然,终余在司,仅杀此一人。”(11)
这种刑罚与《大清律例》相比较是太重了,自然也不符合顾彩的政治愿景。
第三,顾彩心怀“天下一统”的政治理想,而实际上,容美土司田舜年更加关心的是压制邻近强大的桑植土司,稳固甚至扩充自己的辖地,并且对自身的功绩感到骄傲,这种罔顾中央政权,近于“独立思想”的心态也不得顾彩的认可。
根据顾彩对游“得胜桥”的记载:
“二十日,邀余游下坡,观得胜桥,请余作记刻石。(桥在紫草山下坡,跨龙溪江以通往来。落成后君未尝一观。是日,管事旗长康姓者置酒张幔设乐,邀君携宾客宴于桥畔,仍储舟以便泛江。君顾余曰:‘吾砻石以待名人作记久矣,盍捉笔焉。’余问所以名桥。君曰:‘十年桑植寇至,余以四十八人破其数千之众,故以得胜志之。’余曰:‘小矣!且桑植婚姻也,胜之不可为功。夷考是年适值皇上征噶尔丹得胜,普天同庆,以是名之,见不忘君父之义,不亦大乎?’君喜曰:‘吾固想不至此,先生教我多矣,此义是也。’余遂走笔而成,即付石工。)”(12)
由此上几个事例看来,顾彩对于田舜年的个人评价是不符史实的,而仅仅是反映了其个人理想中“美政”追求的“贤君”因素。
(二)对于容美地区自然人文风物的美化
容美地区因为地处偏远,被中原士人一度视为“桃源胜地”,孔尚任指出:楚地之容美,在万山中,阻绝入境,即古桃源也,其洞主田舜年,颇嗜好诗书。(13)毛子霞更是有诗文颂赞:“从今欲鼓渔郎棹,莫遣桃花隔风情。”(14)这些历史文献都体现了在清朝初期中原士人对容美土司所辖地的印象——一个与世隔绝的美好地方,与几千年中国士人们的隐士情怀——桃花源紧密联系在一起。
顾彩在前往容美地区的途中遇到一件事情,很有可能增加了他对于容美“桃花源地”的政治性想象,据《纪游》记载:
“晚至南山坡,有荒庙,颓败不可居。幸已得平地,山明月朗,沙土干燥。东行数里得民房,门道甚整,屋宇亦宽,鸡、豕、牛、驴成队,而阒无主人。余令从者入探之,其东厢有竹床布被,架上有衣儒,不扃锁而误认焉,疑,不敢辄入也。有邻姥过篱外,问之,姥云:‘只管住,无妨。’使解鞍,厝行李西侧房,夹竹为墙,中有磨床,农具与薪。俄而主人归,姓李,见投宿人众,亦了不嗔怪,意邻姥先告知矣。余问:‘何故委牲畜而久不归,设为人攫去奈何?’李笑曰:‘深山中鬼亦无一个,谁攫者?且年成幸好,岂有贼乎?’噫,此太古风也!仍舁竹榻至,燃松做饭,又馈青蒜一把,供夜膳。”(15)
山深林阔,人迹稀少,邻里和睦,尤其是当地居民李老人对于财产单薄的态度,使得顾彩由衷感叹“此太古风也”,无疑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但随后顾彩遇到的事情就没有那么顺利了,不仅因为路途崎岖,人烟稀少,补给困难,更加之深山中虎豹成群,时有危险。在他的《和玩月》一诗中记载了遇到老虎的情景:
“霁景澄澄暮景鲜,万山擎月上中天。巢空近觉乌雏堕,谷静遥知鹿子眠。猿泪下时成碧石,鬼诗吟罢没苍烟。厨人夜语无他事,唯恐于菟到屋边。(时有虎食一驴于屋后圃)”(16)
这一景象对于常年往返与江南与山东等东部平原地区的汉族儒士而言,理应充满惊异和危险,但是顾彩没有在惊诧、危险等等情感因素上发挥,而是以“时有虎食一驴于屋后圃”带轻轻过了。
甚至在其后他的诗作中就出现“岩居幽事颇无穷,葛粉为粮腹易充。虎不伤人堪作友,猿能解语代呼童”(17)、“牛羊各自下,月出大如斗。扫叶闭柴扉,扶藜送邻叟。山中虽有虎,不致伤鸡狗。岁稔俗既淳,盗贼亦稀有”(18)等动人的诗句。不久之前还在土司境内亲历老虎吃驴的事情,转眼就写出“虎不伤人堪作友”这样人与自然和谐并存的诗句,顾彩的意图非常明显,即正是要寄托他那如同陶氏桃花源地般儒家士子的“美政”向往情怀。
三、结语
顾彩作为江南钟鸣鼎食之家培养起来的儒生,饱读诗书,笃信儒家道统。然其一生适值明清鼎革之际,明末江南士大夫实力大为衰减。顾彩作为遗臣后代,对于新王朝并不从内心认可,因而不热衷科举考试与朝局,而是选择教书和四处奔走。
容美土司因为地势险要,早有“桃花源地”的美誉。其时,土司主田舜年也与顾彩旧友孔尚任交好,多种因素促成了顾彩的容美之行。这次出行,是顾彩一生中难得离开中央王权控制之地,到达士人备受礼遇的地方,田舜年对他的尊重无疑也换来顾彩的友谊,终《容美纪游》,顾彩均以“君”称之;对于险要的容美山势,顾彩也以士人欣赏的情怀全心去描绘。
总之,顾彩此行,实际上寄托了明末清初儒家士人的美政向往情怀。
注释:
(1)田耕滋:《屈原“美政”理想的学术渊源》,《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
(2)陆庆祥:《儒家政治美学论》,《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
(3)吴伯森:《容美纪游校注》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260页。
(4)吴伯森:《容美纪游校注》,268页。
(5)钱杭、承载:《十七世纪江南社会生活》,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2——11页。
(6)(清)侯方域:“顾修远辟疆园集序”,见侯方域:《壮悔堂文集》卷二·《续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1405,642页。
(7)(清)孔毓圻:“序”,见顾彩撰:《往深斋诗集》,清康熙辟疆园刻本。
(8)吴伯森:《容美纪游校注》,268页。
(9)吴伯森:《容美纪游校注》,305页。
(10)吴伯森:《容美纪游校注》,314页。
(11)吴伯森:《容美纪游校注》,314页。
(12)吴伯森:《容美纪游校注》,313页。
(13)(清)孔尚任:“桃花扇本末”,徐振贵主编:《孔尚任全集》第一册,“戏剧”,20页,济南:齐鲁出版社,2004年。
(14)毛会建:“寄容美田韶初”,中共鹤峰(五峰)县委统战部县史志办编撰委员办公室:《容美土司史料汇编》,287页。
(15)吴伯森:《容美纪游校注》,278页。
(16)(清)顾彩:“和玩月”,见吴伯森:《容美纪游校注》,283页。
(17)(清)顾彩:“峡内人家”,见吴伯森:《容美纪游校注》,293页。
(18)(清)顾彩:“山家乐”,见吴伯森:《容美纪游校注》,293页。
——李良品《中国土司学导论》读书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