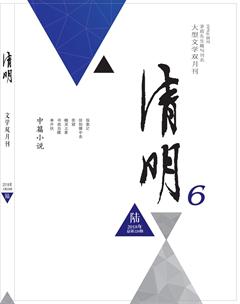一种认知装置:年轻的谜或雨的途中
霍俊明
近两年来,90后诗歌群体引发越来越多的关注,已然成为文坛新的持续增长点。他们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崭新的认知装置,像一场雨正在途中。这既与其整体性的写作面貌有关,又离不开各种平台的大力推介。此次《清明》杂志推出的“安徽90后诗人专辑”让我们继续感受这一代人正处于进行时的写作状态。
对于正在生成、分蘖的“90后”诗歌,我们能做到的也许就是群体性“展示”。与此同时,我们又应该持有审慎和开放并存的阅读期待。文学并不存在什么可供评论家和文学史家们谈资的进化论。对于前景和问题,对于优劣短长,对于及时性的赞扬或者否定,都需要我们耐下心来先读读他们已经写出的或者将要写出的作品有没有不同以往之处。阅读司晓飞、彭杰、闫今、星芽、韩子、许无咎、向晚的诗作,我强烈感受到他们之间的差异性,无论生活方式、精神态度还是诗歌技巧和修辞上,这种差异都体现得非常突出。显而易见,即使是在90后这一群体内部来谈论和考量个体写作也是非常困难的事情,这不仅在于90后写作人口的庞大和可观,也在于很多写作者的个性和面目还尚未完全建立起来。质言之,无论是个体风格还是整体景观,我们对90后诗歌并没有获得足够完备的认识。在整体写作水平提升的年代评价所谓的“好诗”并不难,关键是缺乏具有修辞难度和精神深度的重要性诗作。在滚烫的中国诗歌新浪潮中,我越来越倾心于那些真正用“生命体验”所淬炼出来的诗句。他们类似于某种语言“结石”,在夏日的黑夜中硌疼了我们。这是燃烧的诗,也是冰冷的诗。应该找到一个标志性的文本,它更像是一个神经元,能够让围绕一个个刺激点来谈谈诗人的个人经验、语言能力、诗歌的结构和层次、空间的离乱以及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
个体、碎片、偶发、实感、即时、生长,这是包括90后在内的中国当代诗歌写作的一些特征。每个人都是偶然性的碎片,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区别于其他人,但是当你和其他人一同出现在地铁、公交和电子屏幕前的时候就成了集体复制品。这在一个技术化的时代更为显豁。也许诗歌能够在真正意义上维护一个人的特殊性和完整性。对于这一代刚刚开始成长的写作者来说,更为可靠的还是个案解读。一定程度上,验证年轻诗人写作成熟度的一个重要指标是自觉度,闫今的《长山路桥》和许无咎的《麋鹿记》都体现了较为自觉的形式感和诗歌构造方式,二者也都接近一种融合的诗歌样式,文本的形式感都非常突出,这对于年轻作者来说,是一种有效的训练方式和提升手段,存在的问题则是繁密的叙述在一定程度上压制了“诗性”,形式感也限制了一首诗的生成度。星芽体现在组诗《喜鹊词令》中的自觉意识则让人欣喜。很多写作者对“组诗”尤其是“主题性组诗”存在着非常大的误解,往往就是几首完全不相关的诗堆在一起了事,真正意义上的组诗一定是每一首诗之间存在着密切关联,它们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结构的各个侧面。《喜鹊词令》就是严格意义上的“组诗”,每一首诗都紧密围绕着核心意象“喜鹊”展开、深化、拓殖和围聚,实有的、虚化的、现实的、精神的、经验的、超验的都共生在一起,这就使得“喜鹊”得以最大化的深度揭示。这种写作方式非常有效,经典如史蒂文斯的《观察乌鸫的十三种方式》,再如于坚的《对一只乌鸦的命名》,我希望年轻的诗人们能够多多注意这一点。
当年24岁的青年诗人穆旦给我们呈现和打开的年轻世界是“如果你是醒了,推开窗子,/ 看这满园的欲望多么美丽”。这是年轻人与外界、与时间、与自我的对话。诗歌往往是一个我与另一个我之间的协商、盘诘甚至龃龉,这样必然会产生“困惑的诗”“无解的诗”。在他们的文本中,困惑、否定、犹疑、无解的白日梦状态显然又一次得到了印证:“但别处是否仅是此地的幻象?”(司晓飞《在候车室》)“这一切让我想到万物的困境”(司晓飞《困境》)“在多重楼层的寄居中,疏散困顿的宽度”(彭杰《交谈》)“很难相信有这么多的东西跟随着我”(韩子《旧物》)“你感到这雨像九十年代的人流 / 让你浑身是刺”(向晚《雨的途中》)。正是这种困惑、紧张产生了“真实的诗”。
一个诗人总会怀有写作“纯诗”的冲动,或者抱有介入现实的巨大热情,在诗学的层面,二者的危险性几乎是均等的。诗人有必要通过甄别、判断、调节、校正、指明和见证来完成涵括了生命经验、时间经验以及社会经验的“诗性正义”。由此需要强调诗人处理的公共生活和焦点现实的前提只能是语言、修辞、技艺和想象力的。语言需要刷新,诗歌中的现实感也需要刷新。司晓飞的《在候车室》的开端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最为重要而又日常化的空间——小镇上老旧的候车室。候车室,已经成为这个时代最为日常的景观和流动性的个体生活缩影,而新旧两种时间的摩擦力并并没有随着新时代的到来而消解,诗中体现的正是快速流动的现代性时间给个体带来的普遍感受。彭杰的組诗《风景》则体现了写作者对“纯诗”的追附,他的超现实的幻象、细微的感受力和略显神经质的精敏都使得他具备了诗歌写作能力。当然,语言和诗义上的晦涩与“夹生感”可以看到他对某类诗人的学习经验。一个诗人最终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话语方式和发声装置并不是一个短暂的过程,这正是当下的90后诗人群体所要面对的一个写作难题或巨大瓶颈。
最后我想提醒90后乃至更为年轻的写作者的是,诗歌是一种精神生活,但是精神生活的获得显然并不容易, “诗人”是诗与人的高度结合体,是诗品和人格的相互见证,也就是说“诗人”完全不等同于“写诗的人”。一起来听听三十多年前诗人骆一禾的严正提醒吧——“现在的诗人在精神生活上极不严肃,有如一些风云人物,花花绿绿的猴子,拼命地发诗,争取参加这个那个协会,及早地盼望豢养起声名,邀呼嬉戏,出卖风度,听说译诗就两眼放光,完全倾覆于一个物质与作伪并存的文人世界。”
责任编辑 木 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