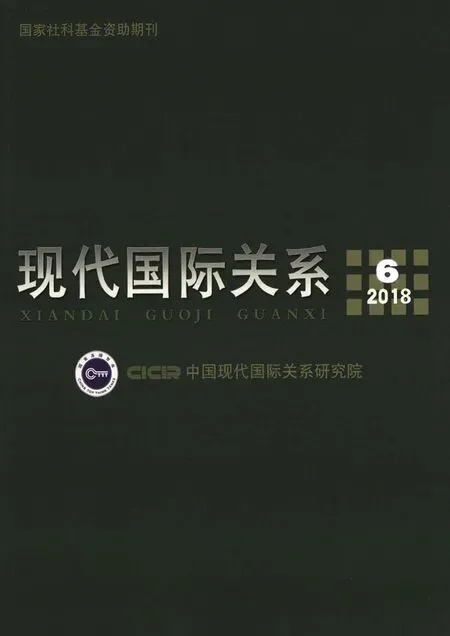“一带一路”倡议推进与中外双边投资协定重构
柯 静
[内容提要]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顺应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变化、破解大国崛起与发展困境所做出的重大战略调整。推进过程中,地区安全风险、秩序主导权争夺、大国竞争和沿线国制度环境等因素,对投融资造成重要障碍,严重制约了“一带一路”顺利推进。双边投资协定(BIT)作为当前国际社会保护投资者利益最重要的工具,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应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但中外双边投资协定体系久未更新,严重滞后于现实需求。为更好地服务于“一带一路”倡议,须认真梳理中国与沿线国间的BIT,仔细分析各国政治、经济、社会、民族、宗教等特点,根据中国在世界投资格局中的身份变化和“一带一路”倡议的现实需求,重构中国和沿线国之间的中外双边投资协定。
2013年,中国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 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统称“一带一路”)倡议,旨在构建中亚到欧洲的合作经济区,推进海上通道开放与合作,进而推动中国与整个欧亚大陆共同发展。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一方面是为了因应美国亚太政策调整,缓解周边战略压力;另一方面则是中国积极提升自身经济资源运作效用,主动拓展与周边国家外交新局面的创新之举。然而“一带一路”地区投融资尚面临多重挑战,制约“一带一路”倡议顺利推进。本文拟对当前中外双边投资协定(BIT)在“一带一路”倡议中保障投融资效力不足予以重点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几点重构建议。
一、 “一带一路”倡议面临的投融资挑战
“一带一路”倡议超越以往纯粹经济思维,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周边外交方针,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http://www.gov.cn/ldhd/2013-10/25/content_2515764.htm .(上网时间:2018年1月12日)倡议提出以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将本国发展战略与之对接,说明该倡议的原则和理念逐渐为更多国家接受,并在一定范围内形成共识,逐步进入实施阶段。2017年3月,李克强总理访问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之际,将“一带一路”覆盖范围向南进一步拓展。*“李克强澳新之行扩大‘一带一路’朋友圈”,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7-03/31/c_1120731985.htm. (上网时间:2018年3月6日)2017年5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阿根廷总统马克里举行会谈时强调,拉美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自然延伸。*“从‘中国船’到‘新海丝’——拉美国家拥抱‘一带一路’倡议”,http://news.xinhuanet.com/2017-05/24/c_1121030198.htm .(上网时间:2018年2月12日)同月,美国总统特朗普特派马修·波廷格率领美国代表团,出席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倡议高峰论坛,表态美国企业愿意参与该倡议。尽管美国迄今对“一带一路”倡议十分疑虑,但并不否认其商品、服务供应商和投资商参与“一带一路”存在商机。*CSIS,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Five Years Later,” https://www.csis.org/analysis/chinas-belt-and-road-initiative-five-years-later-0. (上网时间:2018年3月8日)2018年2月,英国明确表示希望参与“一带一路”项目合作。*“Britain Embraces China’s ‘One Belt’ Initiative; Washington Offers Warning,” https://www.voanews.com/a/britain-china-one-belt-one-road-washington-warning/4236436.html. (上网时间:2018年2月23日)由此,“一带一路”蓝图,向西辐射整个亚欧非大陆,向南与澳大利亚、新西兰实现对接,并与北美、南美基础设施相连,从而以点带面,将整个世界都联通起来。
“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实施,需要大量资金投入。据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估算,未来五年,沿线国家仅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就达10.6万亿美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带一路’设施联通研究”课题组:“‘一带一路’基础设施投融资需求及中国角色”,2017年第17号。而据中国商务部统计,继2015年中企对“一带一路”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8.2%之后,2016年同比下降2%,其占同期对外直接投资总额比重也从12.6%下降至8.5%;*“2016年我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合作情况”, http://hzs.mofcom.gov.cn/article/date/201701/20170102504429.shtml.(上网时间:2018年1月19日)2017年,占同期对外直接投资总额比重为12%,较2016年上升3.5%,但投资金额同比下降1.2%。*“2017年我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合作情况”, http://hzs.mofcom.gov.cn/article/date/201801/20180102699459.shtml.(上网时间:2018年1月16日)可见,“一带一路”倡议在获得沿线国政府热烈欢迎的同时,中企投资热情并未明显高涨。对比20世纪末,中国推行“走出去”国家发展战略,以及对外直接投资额迅速攀升的情形,以上数据真实反映了资本对进入“一带一路”沿线国的犹豫,凸显出倡议推进难度。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投融资尚面临诸挑战因素。
第一,地区安全风险高居不下。“一带一路”沿线中的中东、中亚、南亚和东南亚地区自“9·11”事件之后,就形成了一条所谓的“恐怖主义弧形带”。中东地区,因其敏感的地缘战略位置和极其复杂的历史、宗教、民族、资源等因素,长期以来深受恐怖主义影响;*宫玉涛:“‘一带一路’沿线的恐怖主义活动新态势解析”,《党政研究》,2016年第2期,第19页。中亚地区,阿富汗、巴基斯坦北部恐怖势力活跃,连同我国新疆地区“东突”分子,连连制造恐怖事件。俄罗斯的车臣和高加索地区,素来是恐怖势力盘踞之地;东南亚的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同样深受恐怖主义威胁。甚至欧洲近年来也沦为重灾区,法国、德国、西班牙接连发生恐怖主义袭击,不仅造成民心惶惶,甚至产生高昂的政治成本。据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对沿线35个国家的投资风险评级结果显示,低风险国家仅有新加坡,中等风险国家有27个,高风险国家有7个。*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中国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级(2018)》,2018年第20~21页。
第二,地区秩序主导权争夺激烈。东亚地区,日本对“一带一路”心态复杂,既恐失去市场机遇,担心地缘政治发生变化,又因美国牵制,自主性受到影响。总体而言,日本持竞争者立场,常以在技术、质量、信誉、资本和市场运作经验等方面更胜中国一筹为由,采取尾随破坏做法,谋求通过“丝绸之路外交”,遏制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这不仅使中国在新能源开发和利用、核电技术、资源加工及管理等领域直接面临日本竞争,且造成一些国家对中国意图产生疑虑,削弱对中国的政治信任。*黄凤志、刘瑞:“日本对‘一带一路’的认知与应对”,《现代国际关系》,2015年第11期,第41页。迄今,日本在东南亚很多国家的投资都超过中国;南亚地区,印度洋对中国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但印度作为南亚传统强国,担心中国加大在印度洋的存在会威胁到印度作为印度洋安全提供者的地位。*张立、李坪:“印度对‘一带一路’的认知与中国的应对”,《南亚研究季刊》,2016年第1期,第19页。此外,中印之间存在领土纠纷,近年来中国经济崛起给印度带来颇大压力,国内战略界普遍视中国为竞争对手。中国与巴基斯坦的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与斯里兰卡、孟加拉国和尼泊尔关系的进展,都被印度视为威胁。*张蕴岭:“中国的周边区域观回归与新秩序构建”,《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1期,第19页。因此印度对“一带一路”十分警惕,发起“季风计划”以作应对。东北亚地区,2014年俄罗斯与中国建立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并就欧亚经济联盟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对接形成共识。双方在能源和金融合作、经贸便利化、互联互通、人文交流等领域都取得重要进展,但俄罗斯内部仍保持高度的警惕,担心中国主导“大欧亚”,损害俄罗斯在该地区的战略利益。周边大国地区秩序主导权竞争激烈,直接影响这些国家对待“一带一路”倡议的立场,并可能导致地区其他国家态度发生转变。例如此前曾被叫停的科伦坡港口城项目,斯里兰卡政府公开承认是由于来自印度方面的压力所致。
第三,大国竞争因素干扰明显。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具有鲜明的经济民族主义特征,其贸易团队对华鹰派人士居多。自其上任以来,中美经贸摩擦一路升温。与此同时,美国的中美关系定位出现实质性变化迹象。2017年年底,特朗普任内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界定为“修正主义国家”和“战略竞争对手”,如何遏制中国崛起成为华盛顿的战略焦点。2017年10月,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其《下个世纪的美印关系》的演讲中,用“印太地区”替代“亚太地区”。特朗普在其亚洲之行中提出要“保障印太地区的安全、稳定和繁荣”。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区域战略中,也将印太地区置于首位。*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c. 2017.这些措辞变化表明,美国亚洲战略将出现重大调整,其意在通过美、印、日、澳联手,重塑印太地区新秩序,矛头直指中国“一带一路”。美国作为当今实力最强的霸权国,其政策调整不仅关乎中美关系,还会产生强大的外溢效应,影响他国和中国的互动模式,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威胁认知上升,促发对抗性加剧。
第四,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缺口庞大。基础设施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向效应。它作为一种投资既可直接促进经济增长,又可通过溢出效应间接促进经济增长。*刘生龙、胡鞍钢:“基础设施的外部性在中国的检验:1988-2007”,《经济研究》,2010年第3期。“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实施,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是优先领域。*“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5-03/28/c_1114793986.htm. (上网时间:2018年1月17日)一方面,基础设施合作空间广大,另一方面,资金需求难以满足又会对经贸合作和经济增长形成制约。但基础设施投融资金额普遍巨大,回报周期长且回报率较低。作为典型的公共物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不可避免存在“搭便车”现象,对资本吸引力较低。据统计,目前政府资金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基础设施里的投资比重为70%左右,真正意义上的私人资本仅为20%。*“资金缺口大、投资主体单一 ‘一带一路’融资亟须引入市场机制 激励更多民间资本参与”, http://epaper.21jingji.com/html/2017-12/18/content_76633.htm. (上网时间:2018年3月18日)资金缺口巨大,投资主体单一,是当前“一带一路”建设中的突出问题。尽管中国政府大力倡议民间资本进入,但若没有完善的制度支撑,仅靠一般的政策指引,难以真正撬动民间资本。
五是沿线国制度发展水平迥异。当代全球经济中,一国对于外资的吸引力越来越受到制度性基础建设水平的影响。这种制度既包括实施法律规则、促进竞争、保护知识产权、鼓励创新和提升资本市场效率的正式制度,也包括构成社会化资本与鼓励成员间信任和合作的非正式制度。制度对交易成本起着决定性作用,远超要素禀赋的影响。*约翰·H.邓宁等:《跨国公司与全球经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605、673页。“一带一路”沿线国制度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新加坡和爱沙尼亚、捷克、波兰等东欧国家政治稳定,政府监管效率和质量、法律实施和腐败控制良好,但大多数国家是新兴经济体,经济基础薄弱,法律体系不够完善,政府监管水平有待提高,教育发展难以跟上人才需求,对投资回报率和经济增长形成掣肘,进而削弱该国对外资的吸引力。
二、 中外双边投资协定的保障效力存在不足
上述因素叠加,导致“一带一路”沿线国投融资风险成本过高,对外资吸引力有限。完善海外投资保险,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投资者顾虑,但并不能从根本上促使东道国营造良好营商环境,保护投资者利益。若发生可归咎于东道国的事件,却只能通过保险来弥补投资者损失,用国家公共财政承担风险,一来存在道德风险,容易引发财政危机,二来并未触及问题根源。因此,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实施,亟须投资者母国和东道国共商共建多层次的保障体系。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固然需要完善,但促使东道国真正致力于降低投融资风险,改善投融资环境并切实承担保护投资者责任的法律制度必不可少。就目前而言,BIT作为管理经济发展水平各异的国家间投资关系的主要工具,应在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中发挥更关键的作用。
第一,双边投资协定具有深厚的制度共识。作为两个国际法主体主要就保护、鼓励、促进和保证国际直接投资而缔结的以国际法为准的旨在确立其相互间权利义务关系之国际书面协议,*杨卫东:《BIT研究——中国的视角》,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第2页。BIT被广泛认为是保护外国投资者最重要且最有效的方式。截至2018年2月,全球共有各类国际投资条约3327个,其中BIT为2954个。*“UNCTAD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 Navigator,” http://investmentpolicyhub.unctad.org/IIA . (上网时间:2018年3月7日)在 “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中,我国已和57国签订BIT,*与我国之间无BIT的国家和地区有8个,分别为:阿富汗、伊拉克、黑山、尼泊尔、不丹、巴勒斯坦、马尔代夫、印度尼西亚。我国与印尼政府之间原本签署过BIT,但2014年印尼政府单方面宣布终止该国全部67项BIT,包括印尼—中国BIT。充分说明该机制在“一带一路”地区同样存在广泛共识,而共识是解决很多问题的前提和关键。
第二,双边投资协定签订方式更为灵活。“一带一路”覆盖众多国家,国情各异,民族、宗教、文化十分复杂,经济和制度发展水平不一,要素禀赋和区位优势存在差异,若要达成多边协定,可能性和可行性较低。即便最终形成共识,也会在规则标准和执行力度上做出不少妥协。效果如何,存在较大疑问。BIT签订主体仅为缔约双方,缔约过程一般只需关注彼此,相对来说干扰因素较少,可以充分考虑彼此关切,达成一致。
第三,双边投资协定保护投资者效力得到肯定。BIT中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ISDS)首次赋予投资者单方面提起针对主权国家的国际仲裁权利,为投资者提供超越国内法的国际法保护。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统计,自1987年以来,ISDS案件呈逐年上升趋势。截至2017年1月,已知案件达767起,全球共有109个国家成为被申诉方。*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7, p.114 ,2017.由于大部分国际投资仲裁允许保密,实际数量可能会更多。特别是执行此类案件裁决与WTO有所不同,东道国败诉须以金钱赔偿方式承担损害责任。近年来仲裁结果表明,仲裁庭偏重保护投资者利益,东道国常被裁决承担巨额赔偿责任。1987~2016年间,平均赔偿金额高达5.45亿美元。2016年投资者提起的申诉金额范围为1000万美元至165亿美元。*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7, pp.117-118 ,2017.以ISDS机制作为后盾,BIT保护外国投资者效力毋庸置疑,足以推动东道国审慎对待条约义务。
因此,相对于某些学者提出的在争端解决机制上另辟蹊径的建议,笔者更倾向于充分发挥BIT的保障效力。但问题在于,中国是BIT实践大国,迄今已签订129个BIT,仅次于德国;但最初开启BIT实践时,对外投资规模十分有限,并无保护本国海外投资利益的强烈需求,主要是为吸引外资,向国际社会释放中国开始融入世界经济的信号,表明愿意承担符合国际标准的保护投资者义务,更具有一种宣示效应。中外BIT体系运行至今,其最重要的保障投资者效力并未得到良好体现。
其一,中国并未充分利用BIT中的ISDS机制。此前述及,BIT之所以成为保护外国投资者最有效的工具,ISDS机制最为关键。截至2017年1月全球公开的767起ISDS案件中,最常见的申诉方母国为美国,共发起148起申诉,其次为荷兰92起、英国67起、德国55起、加拿大44起。*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7, p.116 ,2017.中国投资者提起的申诉仅为5起,不到总数1%,也即中国对外投资规模的迅猛增长并未同时带动中国投资者更多发起ISDS申诉。有学者试图对此现象做出解释,认为一方面“中国对国际仲裁缺乏亲和力”,更倾向于用友好协商方式解决争议;另一方面中国对仲裁范围做出严格限制,仅在为数不多的BIT中赋予投资者就所有投资争端提交ICSID仲裁的权利,且这些BIT相对方吸收中国投资流量不大。*Axel Berger, “China’s New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 Program,” Americ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Interest Group 2008 Conference in Washington DC, Nov., p.14,2008.无论是何缘由,中国对ISDS机制的利用状况差强人意。
其二,现有中外BIT尚未完全覆盖“一带一路”地区。在65个沿线国中,尚未与中国签订或已终止BIT效力的国家有8个,分别是阿富汗、伊拉克、黑山、尼泊尔、不丹、巴勒斯坦、马尔代夫、印度尼西亚。印尼是中国重要投资目的地之一,但该国反华情绪浓厚,时常发生排华事件,安全风险较大。另有些国家,中国对其投资存量不大,但增速惊人。例如阿富汗是全球风险系数最高的五个国家之一,在该国所有外国投资中,中国资本占79%。*“中国超越美国 成为全球最大海外投资国”, http://www.cankaoxiaoxi.com/finance/20160516/1160506.shtml. (上网时间:2018年1月16日)又如伊拉克战争后,伊欠下中国投资者债务,迄今少有归还。至于巴勒斯坦、黑山等地,由于复杂的民族冲突等因素,地区安全状况令人堪忧。中国与这些国家间尚无BIT,对保护投资者利益相当不利。
其三,部分已签订的中外BIT尚未生效。中国已签署的BIT中,仍有20个尚未生效,绝大多数相对方是非洲发展中国家,目前“一带一路”沿线国有2个,为约旦和塞浦路斯。随着“一带一路”辐射范围逐渐扩大,可能延伸至与中国BIT尚未生效的非洲国家。这些国家大多政治社会环境动荡,投资风险重大。例如2011年利比亚战乱导致当地基建项目被迫搁浅,中国企业损失合同金额约为188亿美元,而保险赔付不足4亿美元。由于中国——利比亚BIT(2010)尚未生效,不在国际投资规则保护框架内,投资者只能基于传统外交保护等途径寻求救济。可见,即便两国间签署了BIT,但只要还未生效,就无法真正发挥保护投资者作用。
其四,已生效中外BIT保护标准普遍低下。(甲)国民待遇尚未覆盖准入前阶段。迄今中外BIT中投资保护标准最高的中国——加拿大BIT(2012),也并未提供准入前国民待遇,且对投资扩张阶段的国民待遇附加限制性条件,仅限于投资扩张时根据相关国内法无须经过审批的行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加拿大政府关于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的协定》第6条第3款。(乙)早期准入后国民待遇普遍施加须符合东道国国内法的限制性条件。*如中国—摩洛哥BIT(1995)、中国—沙特BIT(1996)、中国—马其顿BIT(1997)等文本都是如此。2000年中国与伊朗签署的BIT中,也仍规定“依照东道国缔约一方的法律法规”的限制性条件。东道国可通过变更国内法的方式轻易规避协定义务,从而使国民待遇难以真正得到国际法层面的保护。直到21世纪,中国才开始接受更为普遍意义上的国民待遇,例如中国—塞浦路斯BIT(2001)、中国—荷兰BIT(2001)、中国—德国BIT(2003),国民待遇条款不再出现“在不损害其法律法规的前提下”的限制性用语,改为采用国际上较为通行的“祖父条款”,对不符措施做出例外规定。*此类“祖父条款”通常附随于议定书中,一般规定国民待遇不适用于:1.领土内任何现存不符措施;2.前款所述不符措施的延续;(丙)对第1款所述不符措施的修改,但修改不得增加修改前的不符程度,也即“静止”要求。此外,承诺将努力逐渐消除这些不符措施。(3)大部分BIT仲裁范围有严格限制。在中国—巴巴多斯BIT(1998)之前,仅同意与征收补偿额有关的争议提交国际仲裁,对东道国国家行为是否构成征收及其他投资争议,只能通过友好协商或寻求东道国国内法救济,对保护投资者相当不利。例如2015年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党(Syriza)在大选中获胜上台,取消该国9.5亿美元港口私有化项目。*“中国投资遭遇海外政治风险”,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60639?full=y?ccode=2G139005&archive.(上网时间:2018年5月8日)我国中远集团已进入最后竞标阶段,对该项目的前期支付血本无归。经笔者整理,此类BIT尚有73个处于生效状态。(丁)仅个别BIT包含业绩条款。目前仅中日韩BIT(2012)*中日韩BIT(2012),第7条。和中国—加拿大BIT(2012)*中国—加拿大BIT(2012),第9条。纳入WTO《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中的禁止性业绩要求。这对当初主要作为投资东道国的中国并无不妥,但目前已是资本输出大国的中国,则需对东道国一些不合理的业绩要求加以规范。(戊)未就便利劳务人员入境做出确有约束力的规定。目前也仅中日韩BIT(2012)*中日韩BIT(2012),第8条。和中国——加拿大BIT(2012)*中国—加拿大BIT(2012),第7条。设有单独条款规范人员入境问题,其他中外BIT基本都在正文中宽泛提到缔约方有为另一方国民获得签证和工作许可提供帮助和便利的义务,但皆为“软性”条款,且普遍施加“依据东道国国内法”的前提条件,并无实质性约束力。当前一些国家指责中国投资并未惠及当地,甚至损及就业,并以此为由阻挠中国劳务人员办理签证。例如中国公民申请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签证就很困难,后者2007年还通过一项限制外来劳务人员数量的法律,给中国企业至当地投资带来很大不便。对此,BIT中未能做出有效力的约束,是当前中外BIT的又一项重要缺陷。
三、 “一带一路”沿线国中外双边投资协定的重构建议
中外BIT体系严重滞后于中国已是资本输出大国的现状,难以为“一带一路”投融资保驾护航。为使BIT切实发挥保障作用,须对中国和沿线国间的BIT认真进行梳理,仔细分析各国政治、经济、社会、民族、宗教等特点,客观评估其对华关系,顺应中国在世界投资格局中身份变化,服务于推进“一带一路”现实需求,对沿线国中外BIT进行重构。
(一)“一带一路”沿线国中外BIT的重构定位。
第一,须平衡投资者保护与东道国外资管理权。目前中外BIT体系仍主要立足于中国作为投资东道国的身份,未注重保护本国投资者海外投资利益。重构与沿线国间的BIT,须根据沿线国国情和投融资环境,对保护投资者标准做出相应调整。但难点在于,提升保护水平对应着东道国保护投资者的义务,两者间存在张力。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输出大国,不断扩大国际投资条约中的“投资”和“投资者”定义,提升保护标准。美国2004年和2012年BIT范本,将投资者根据东道国行政许可而取得的公法权利纳入保护范围,*美国2004和2012年BIT范本,将许可、授权、允许和其他根据国内法所授予的类似权利纳入保护范围。在“代表缔约方为社会公众提供服务的权利”中,列举多项重要的公共服务形式,如能源的生产与分配、水处理或分配或电信;承担政府独占或主导使用和获利的基础设施建设权利。并主张权利一经授予,不得撤回。这会导致东道国失去未来因情势变更、行政许可有悖于公共利益时可进行调整的行政裁量权。TPP投资规则一定程度上对此加以纠偏,体现出美国认识到两者间需更好加以平衡。特别是ISDS机制起源于私人主体间的临时商事仲裁制度,仲裁庭偏重于保护投资者利益,近年来不时出现投资者挑战主权国家公共政策的案例,一些东道国为避免高昂的金钱赔偿不得不改变国内立法,严重危及经济主权和公共利益。*最具代表性的案例为2010年菲利普·莫里斯(瑞士)公司以违反公平公正待遇为由,挑战乌拉圭政府实施的烟草包装法案中为保护公众健康所作的规定;2011年菲利普·莫里斯亚洲有限公司基于同样事由,挑战澳大利亚政府《烟草平装法案》的类似规定。中国如今兼具资本输出和资本输入大国双重身份,更应特别注重两者平衡。
第二,要重视运用例外条款保障中国公共管理空间不被过多限制。为保障国家必要的外资管理权,BIT允许通过例外条款,排除协定义务的适用范围及履行。在特定损害发生时,可将成本从东道国转嫁至外国投资者身上,发挥风险重新分配的功能。*William W. Burke-White and Andreas Von Staden, “Investment Protection in Extraordinary Times: The Interpretation of Non-Precluded Measure Provisions in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 Virgin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48, Issue 2, 2008, p.314.但当前中外BIT体系对例外条款重视远远不足,此前未遭遇外国投资者大量申诉,得益于绝大多数中外BIT未完全提供相对方国民待遇并严格限制仲裁范围,外国投资者可提起的申诉事由十分有限。然而这一屏障很可能将被打破。2018年1月1日中国已正式实行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2018年4月习主席在博鳌论坛演讲中宣布今年上半年中国将完成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工作。*“习近平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http://www.xinhuanet.com/2018-04/10/c_1122660064.htm. (上网时间:2018年5月10日)随着中国即将进一步提升市场准入水平以及未来可能在BIT中提供相对方准入前国民待遇,若继续不重视运用例外条款,一旦大幅提升投资者保护标准,将会使得本国外资管理权受到很大限制。特别须注意的是,阿根廷公民诉Maffezini西班牙一案中,仲裁庭支持投资者适用最惠国待遇条款,获得另一条约中相对于基础条约更有利的ISDS待遇,*Emilio Agustín Maffezini v. The Kingdom of Spain, ICSID Case No. ARB/97/7, Decision of the Tribunal on the Objections of Jurisdiction, 25 Jan. 2000.此后还出现一系列类似裁决。如果仲裁庭对此逐渐放宽解释,将会使中国被诉至ISDS机制的风险大为提高。因此,中国首先应尽快清理中外BIT体系,通过更新协定或缔约方发布联合声明等方式,限制最惠国待遇条款适用范围。在提升投资者保护标准,为中国海外投资保驾护航的同时,重视运用例外条款,确保中国作为投资东道国的公共管理空间。
第三,要注重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经济全球化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因国际和国内政策未及时做出调整,加剧发展不平衡,并产生对环境、人权等方面的负外部效应。国际投资条约体系建立之初,国际社会并未充分重视可持续发展目标。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及诸如环境污染、侵犯人权、侵害少数民族、土著居民等群体权益的事件,使政策制定者开始反思,认识到促进和便利投资不能仅着眼于短期资本流动,而应纳入包容性和可持续发展目标,致力于长期稳定和均衡发展。重构与“一带一路”沿线国的中外BIT,亦应如此。文本应根据本国国情和经济发展水平,包含合适的保护环境、维护金融和经济稳定、消除贫困、减少发展不平衡、加强投资者责任等内容,在追求经济目标的同时适当兼顾非经济目标。
第四,应整合升级而不宜加重“碎片化”。“一带一路”沿线国差异大于共性,BIT文本须体现出针对性,考虑可行性。但重构应为整合升级,而非更加“碎片化”。当前国际投资条约体系中新旧条约并存,区域性条约与大量双边条约叠加,碎片化现象十分严重。如何整合,是国际投资条约体系改革的重点和难点。“一带一路”地区中外BIT重构,应顺应改革趋势,不应背道而驰。可借重构之际,制定既服务于“一带一路”现实需求,又符合中国在世界投资格局中身份变化的新一代中外BIT范本。与沿线国开展谈判应基于范本,各BIT重要条款和措辞尽量保持一致,根据国别国情适当加以调整,尽可能通过附件、双方议定书等形式,将特殊内容附随在文本后。既能避免削弱协定效力,又避免过于杂乱。
(二)可适度借鉴美国国际投资条约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投资规则。笔者认为,中国应尽快制定新一代中外BIT范本,基于范本重构和沿线国间的BIT,范本可适度借鉴美国国际投资条约和TPP投资规则。
第一,美国国际投资条约确有可借鉴之处。一是注重运用例外条款保障国家外资管理权。例如宽泛的根本安全例外条款,在促进投资便利和自由化同时,确保外资筛选权,不让外资进入关涉国家安全的敏感行业。这种方式可使美国在一贯坚持投资者保护高标准的同时,不会过于侵犯其国家公共政策空间。二是注重条约间措辞一致性。例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投资规则对美国国际投资条约体系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NAFTA达成后,美国大幅修改BIT范本,尽可能贴近NAFTA投资规则的框架和内容。此外,在起草条约文本时,尽量避免不必要的词汇创新,减少法律体系的内部冲突和适用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三是注重清晰表达缔约方意图。除了条约正文,美国在附件、双方议定书和提交国会批准的往来信件和资料中,都会对条约关键点进一步加以解释。信件和资料虽无条约相同效力,但在仲裁实践中有助于把握缔约方真实意图,减少仲裁庭自由裁量权。
第二,目前阶段中国尚无法回避美国规则的影响力。TPP规则蕴含美国继续引领国际经贸规则的战略意图,体现其主流精英阶层维持美国霸权的共识,其生命力不会随特朗普退出而消失,仍会继续出现在美国主导的国际经贸规则谈判中,如正重新谈判的NAFTA,据流出的谈判细节,部分规则甚至超越TPP标准。尽管中美经贸关系目前呈紧张态势,但特朗普政府并未表态终止中美BIT谈判。若双方继续谈判,文本也定会体现TPP规则外溢效应。当前中美经贸摩擦焦点问题如扩大市场准入、确保公平竞争、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减少国有企业补贴范围,也是中美BIT谈判博弈重点。而TPP规则对此早有安排,特别体现在TPP为国有企业单独设立章节,将其从传统的竞争政策中独立出来。通过对国有企业定义纳入“控制权”标准、约束国有企业商业运营须基于商业考虑、禁止政府对国有企业提供非商业性援助,*TPP (2015), Chapter 17.解决了WTO框架下认定国有企业提供补贴及采取救济措施的困难。另一方面,对中国而言,加快国企改革,提高市场竞争水平,于竞争中进一步提升生产力和竞争力,也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经之路。因此,与其被动为之,不如早做准备。审慎评估TPP规则适用效果,择其适用者,纳入范本。一来有利于尽早化解固有利益格局,打破体制改革僵局;二来也可起到宣示作用,或有助于缓解中美经贸摩擦。
第三,TPP投资规则在若干方面顺应国际投资条约改革方向。规则合理之处有几个方面。一是文义表达更加清晰。以“投资”“投资协议”等关键术语定义*TPP(2015), Chapter 9, Article 9.1 & footnote.和提起仲裁的资格范围*TPP (2015), Chapter 9, Article 9.1.为例,由于ICSID公约第25条并未明确定义仲裁庭管辖权范围内的“投资”,加上各国对此理解有所不同,因此仲裁实践中仲裁庭拥有很大的裁量权,屡屡出现不一致的裁决结果,严重削弱仲裁的确定性。TPP投资规则对此做出重要完善,*例如明确“投资协议”必须是TPP生效日之后缔结和生效的,排除在TPP生效日之前已缔结和生效的原始协议的续约或延长,协议条款无实质性变化的投资协议;明确将政府单方面的补贴和赠款行为排除在协定义务范围之外;明确行使政治分支机构授权的政府职权的国有企业,适用协定义务;通过具体列举方式,使协议覆盖的“涵盖投资”“投资者”权利范围非常清晰,并以“其他类似资源”“其他类似服务”“其他类似项目”等开放式措辞结尾,又可确保投资保护范围的开放性。可减少因文义不清导致仲裁庭做出不利于投资东道国的解释。二是进一步提升投资东道国公共管理权。TPP在为投资者提供高保护标准的同时,增补若干重要例外条款,比如将政府“补贴”和“赠款”排除于特定实体义务之外。*TPP(2015), Chapter 9, Article 9.1 & footnote, Article 9.6(1).5, Article 9.6(2).3, Article 9.7.6, Article 9.11.6.美国金融救助常以政府补贴和赠款方式进行,2008年金融危机使美国认识到确有必要排除这一行政行为,以免违反协定中的国民待遇和公平公正待遇义务;又如新增资本转移例外,允许国家因宏观经济稳定、金融审慎安全、国家收支平衡等存在严重困难或威胁为由,对相关经常账户交易、资金流动乃至实物支付和转移进行限制。美国改变其一贯严格的资本转移自由立场,也和2008年金融危机有重要关联;又如业绩条款中,新增缔约方在符合特定情形下为保护公共利益目标的例外。TPP投资规则中新增的上述例外条款,确保了本国海外投资获得高水平保护的同时,投资东道国自身的重大公共政策目标不会受到协定过多约束。三是提升ISDS机制合法性。TPP通过强化缔约方对条约解释权、程序参与权和裁决控制权,对此前ISDS机制程序设计过于偏重保护投资者利益、仲裁庭自由裁量权过大加以纠偏。例如,将投资者仲裁选择权从主观标准变为客观标准,提升国家协商前置程序地位;*TPP(2015), Chapter 9, Article 9.18.1.正面规定投资东道国行使反诉和抵消权;*TPP(2015), Chapter 9, Article 9.18.2.提高仲裁员专业知识和相关经验要求,强调仲裁员独立性和公正性;合理设计仲裁和律师费用以限制投资者滥用仲裁权利等。四是促进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TPP在美国2012年BIT范本基础上更进一步,序言中采用较大篇幅阐明可持续发展目标。*TPP (2015), Preamble.TPP投资规则在上述四方面的改进,与中国立场并不相悖。因此,TPP规则中虽有不少中国目前难以企及的高标准,但并非没有可借鉴之处。
综上所述,基于BIT在国际社会拥有较广泛的制度共识,制定方式灵活,且具有良好的保护投资者效力,可改善“一带一路”沿线国投融资环境,降低投资风险,应在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中发挥更关键作用。基于目前中外BIT体系严重滞后于现实需求,应尽快整合升级。建议中国尽早制定符合世界投资格局变化的新一代BIT范本,在此基础上重构与沿线国间的BIT。既要符合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现实需求,契合沿线国特点,也要避免加重条约体系“碎片化”,可适度借鉴美国国际投资条约和TPP投资规则中较为合理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