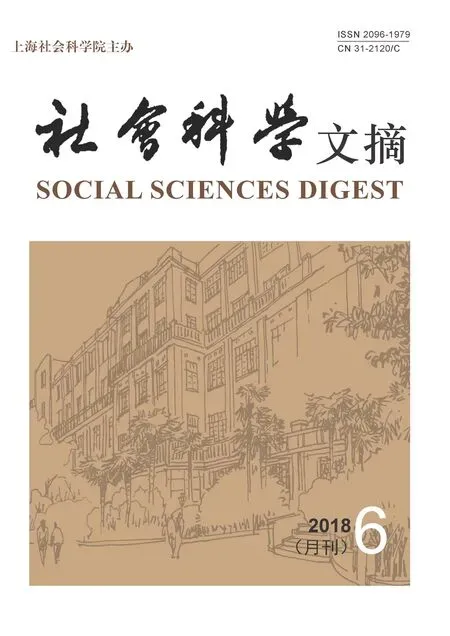华夏族、周族起源与石峁遗址的发现和探究
文/沈长云
华夏,是我国主体民族古老而又沿用至今的称呼,汉族则是华夏民族在汉以后的改称,这在今天已是基本的历史常识。然而“华夏”这个称呼的来历如何?华夏族的来历又是如何?许多人却不甚清楚。长期以来,笔者一直留意这个与我们民族早期历史有关的问题,经过研究,知道华夏族起源与历史上周族的兴起有着直接关系,华夏族对于祖先黄帝的崇拜亦牵涉到周族更早的历史。遗憾的是,学界对于周人的早期历史,尤其是对周族起源的认识一直处在比较混沌的状态。好在近年来,与这些问题相关的历史研究暨考古发掘取得不少进展,特别是不久前陕西省神木石峁遗址的考古发掘,提供了回答这些问题的新的契机,不仅揭示了作为华夏族与周族共同祖先的黄帝部族之所在,更提供了早期周族所从事职业的新的线索。
华夏族与周族:从华夏族名称来历谈起
众所周知,我国历史上的华夏族主要是由古代居住于中原地区的夏、商、周三族经过长期融合而后形成的。但是夏、商、周三族是在何种历史条件下怎样开展融合的,学者对此问题的认识却并不一致。实际上,夏、商、周三族以及部分所谓蛮夷戎狄的融合主要是在西周春秋时期,并且是在周人的主导下进行的,华夏族的产生与周族在历史舞台上的活动有着更多密不可分的联系。这一切,可以从华夏族在商周之际的起源谈起。
商周之际是我国古代政治制度与思想文化出现重大变革的时期。昔日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便曾指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其所指周之制度大异于商者,包罗甚广,不能在此一一论列,唯其中封建子弟一项,对华夏民族之形成影响巨大。可以说,正是周人的封建,才迈开华夏民族形成最关键的步伐。
在周人取代商人建立起自己的王朝以前,整个商人的天下还是一个万邦林立的局面。整个商代社会还没有出现不同氏族部落人们的混居杂处,这与一个统一的民族共同体的出现,应当说还有不小距离。
但是,西周封建却开启了打破古代部族间的血缘壁垒,促使他们混居和相互融合的新局面。所谓封建,是周人发明的一种新的统治方式,即将被征服地区的土地和人民分别授给周室的子弟亲戚,使其在各地建立一些兼具邦国规模和周朝地方政权双重身份的新的封国组织。封建的目的,当然是拱卫周的王室,但这样建立起来的封国已不同于过去那种自然生长的单一血缘组织性质的氏族邦方,而是人为建立起来的由不同血缘亲属关系的人们组成的政治组织。在所有这种性质的封国中,实际都包含了来自不同地方、具有不同血缘关系的人群:一部分是征服者,包括周室的子弟亲戚及他们的族属;另一部分是被征服者,包括当地的土著,或是周王赏赐给封君的其他被征服的族群。由于这些封国将不同血缘关系的人们组织在一个共同体内,使原本互不相干的族群有了共同的政治经济利益,这就有利于打破他们之间的血缘壁垒,促使他们在此基础上的混居和相互融合。这些,都为以后统一的华夏民族的形成打下了基础,说明周初的封建确实是华夏民族形成的先河,并且周人在华夏民族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主导作用。
能够对上述华夏族起源问题做出进一步说明的,还有华夏族族称的来历。因为我国华夏族的族称也产生在商周交替的时候,并且华夏这个称呼也出自周人的自称。从目前我国最早的传世文献《尚书》的《周书》诸篇中,可以考见周人自称为“有夏”的情形。如《康诰》:“惟乃丕显考文王……用肇造我区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君奭》:“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这些文献都出自周初统治者之手,由这些可靠的文字,可知“区夏”、“有夏”都是周人的自称。
现在要问,周人既非夏后氏的后裔,他为什么要自称为“夏”?过去人们对此有过许多猜测,其中最流行的一种解释是傅斯年在《夷夏东西说》中提出来的,他认为周人是出于政治需要,为冒攀亲缘而自称为夏的。
其实,周人之自称为“夏”并没有那么多的深意,他们大概只是使用了“夏”这个字的本义来表现自己,表现以周邦为首的反商部族联盟的浩大声势。“夏者,大也”,《尔雅·释诂》及经、传注疏并如此训。周人兴起于秦晋之间,人皆无异议,他们使用“夏”这个人皆爱伟之的称谓来张大自己的部族联盟,以壮大反商势力的声威。
商周之际,与商朝统治者集团的分崩离析形成鲜明对比,西方以周族为首的势力集团(即所谓“夏”)迅速发展壮大。随后,华夏部族联盟在周王室领导下展开对商王朝及东方部族的征服,随着征服的顺利进行,周王室又把“夏”的名称冠在自己分封出去的诸侯国的头上,这些诸侯被称作“诸夏”。作为周王室的“夏”与作为诸侯国的“夏”在宗法关系及姻亲关系下结成一个整体,成为当时中国的主宰。时间一长,凡称作“夏”的东西都带有正统的意味。《诗经》中的《大雅》或《小雅》被视作华夏正声,“雅”就是“夏”,“雅言”即“夏言”。于是,“夏”不仅带有政治联盟的色彩,而且带有共同文化的意味了。所谓“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的训释,当由此来历。在此文化心理的背景下,又产生“华夏”的称呼。华、夏二字本来音同通用,《左传》、《国语》等文献中或称“诸夏”为“诸华”。然而华、夏二字的重叠使用显然还具有更深的文化上的意蕴,因为“华”字还具有“华美”、“有文采”的意思。它出现在春秋以后,是表明华夏之人对自己的文化更多了一层自信。所谓“中国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当由此得来。
整个西周和春秋,以周人为首的华夏集团通过分封撒向黄河、长江流域的各个战略要地,在与各地夏、商旧族及部分蛮、夷、戎、狄的长期混居杂处中,他们开始是在政治上,继而在文化与语言习俗上,都广泛地起着主导作用。因而当日后他们与其他中原旧族融为一体以后,人们将这个新融铸成的民族共同体仍称为“夏”,或“华夏”,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总之,华夏族的起源与其形成,都是和周族的兴起密不可分的,这是周族为我国历史所做出的一大贡献。
黄帝:从周族祖先到华夏祖先的演变
有关华夏族起源的探讨,自然牵涉到华夏族何以称自己的祖先为黃帝这样一个问题。华夏族之所以奉黄帝为我们民族的共同祖先,也与周人有关。质言之,黄帝之作为华夏族共同祖先,乃是由周族的祖先演变过来的。这实际从另一个角度展示了华夏族与周族密不可分的关系。
黄帝之作为华夏族的共同祖先,并不是人们凭空想出来的。有关黄帝(及其他传说时代人物)的传说故事,应当说都有其真实的历史素地,需要认真加以探讨,不得以“其言不雅驯”为借口简单弃置不顾或置而不论。但如司马迁《史记》按照《大戴礼记·帝系》及《五帝德》的说法,将黄帝及其他几位古帝,包括帝颛顼、帝喾、帝尧和帝舜都比作后世一统国家那样前后相承的君主,并且将颛顼等其他几位古帝以及夏商周三代国家的君主都说成是黄帝一人的嫡系子孙,则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亦不符合历史发展的逻辑。彼时的中国,也就是文明开始前后那段时间,实居住着许多互不相统属的氏族、部落。今人或称之为族邦、邦国或“方国”。它们或因各种不同的利害关系,按地域和按亲属关系,结成为一些较大的部族集团。黄帝以及其他几位古帝,还有一些不包括在“五帝”系统内的著名传说中人物,如太昊、少昊、炎帝、共工、蚩尤等,应该就是夏以前各个部族集团的首领,或各部族集团的后人奉祀的祖先。
先秦时期较早且较可信的史学著作《左传》《国语》曾记载了上述古帝及其他一些著名部族集团首领的活动。其中《左传》昭公十七年说:“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太皞(昊)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其称黄帝等人为“某某氏”,可见黄帝等人的身份原本确实是上古各个氏族部落集团的首领。至于他们的“帝”的称谓,则是其后人在祭祀他们的时候冠在这些祖先头上的尊称。这些“帝”,与秦始皇以后“帝”的性质是不一样的。所谓“五帝”及其他一些传说时代的古帝,应当都是这样一种各氏族部落集团“祖先神”的性质,这比单纯将他们视作神化中人物显然要实在。
经过多方讨论,现在人们已大致达成对于“五帝”及其他部分传说中人物是何部族或部族集团祖先的认识了。如认为太昊是东夷风姓部族的祖先,少昊是东夷嬴姓部族的祖先,黄帝是西北姬姓部族的祖先,炎帝是西方姜姓部族或古代羌族人的祖先,颛顼是妫姓有虞氏部族的祖先,蚩尤是稍晚时期的东夷族的祖先(也有称他是南方苗蛮族的祖先者),尧是陶唐氏的祖先,舜则是颛顼之后的有虞氏的另一位祖先,等等。对于他们(及他们所代表的古代部族)的居住地域,也大致有一个基本判断,如认为黄帝居住在今陕西黄土高原;炎帝居住在今陕甘交界一带及渭水流域;太昊、少昊居住在今山东省境内及附近安徽江苏的北部;颛顼与共工居住在古河济地区,即今河南与山东交界的华北南部平原一带;舜作为颛顼的后人,也应活动在今鲁西黄河下游平原一带;至于帝喾,由于他的后人商族的起源尚无定说,因而他活动的地域暂时无法确定;尧生活在晋南或是在鲁西菏泽一带,也暂时没有定论。以上这些看法,都大致得到考古发掘资料的印证,并与考古学主流学者主张的中国古代文明多元起源理论相互印证。
那么,黄帝又是怎样由一位早先的西北姬姓部族的祖先演变为整个华夏民族的祖先,并且是排在第一位的祖先的呢?这需要从黄帝与建立周王朝的周族人的关系谈起。周人姬姓,在上古时期先后参与逐鹿中原的各个著名部族,包括夏、商、周、秦、楚各族中,只有周族属于姬姓,以此,古今人们一致认为周人是黄帝的直接后裔。黃帝姓姬是因为他的居住地在姬水,即《说文》所谓“黄帝居姬水,因水为姓”。这个说法又显然来自《国语·晋语四》“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的记载。我们无法判定姬水的准确位置,但大致可以认定它是在陕北某个地方。徐旭生先生就曾明确指出:“看古代关于姬姓传说流传的地方,可以推断黄帝氏族的发祥地大约在今陕西的北部。”早期的周人,即所谓先周族也一定是跟随着整个黄帝部族居住在他们的根据地陕北高原一带。周人后来迁居到关中渭水流域,乃是经过许多代人不断向南迁徙的结果。刚好,文献记载黄帝原本也是北方戎狄族的祖先,特别是姬姓的白狄族的祖先。白狄姬姓,白狄的别支犬戎、骊戎及以后建立古中山国的鲜虞族亦皆属于姬姓,他们都出自黄帝。
无论何说,作为黄帝后裔的周人至迟到晚商时期便在岐山下面的周原安顿下来。他们先是与这里的原住民姜姓族人结为婚姻,继而结成稳固的政治联盟,同时努力汲取姜人以及商人的文化,使自己很快获得长足发展。到公亶父之孙文王的时候,已积累起相当实力的周人窥测到东边商人统治内部出现的危机,又不失时机地打出反商的旗号。之后,周朝实行的封建统治为大规模的民族融合提供了新的契机,经过周人与夏商旧族及部分周边蛮、夷、戎、狄长时期的往来交汇,最后,当春秋战国之际,所有黄淮江汉地区的旧的氏族性质的群落终于融铸成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即华夏民族。
何以认定春秋战国之际黄淮江汉地区的人群才最终融铸成一个统一的华夏民族呢?因为只是到这个时候,各地区的人们才都去掉了对于自己原先氏族出身的记忆,有了对于统一的华夏民族的认同,即都一律认同自己是华夏之人。顾炎武《日知录》卷13“周末风俗”条曾谈到春秋时期与七国时期社会风俗之重大差异,其中一点是“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之矣”,即战国时大家都不再论自己的氏族出身了。顾炎武还谈到另一个战国时期与之前不同的社会现象:“春秋时犹严祭祀,而七国则无其事矣。”即战国之人不再严格区别各自奉祀的祖先。这当然不是说战国之人不再注重祭祀祖先,而是说战国之人认为大家既然都是同一个民族,就没必要将各自的祖先划分得那样清楚,只要是为华夏先民做出过贡献立有大功的祖先,不论他们出自何族,大家都可以祭祀。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将各氏族部落原来的祖先编在一个共同的谱系上,使他们成为华夏民族共同祖先的做法,也是很自然的事情。战国后期,《大戴礼·帝系》《五帝德》,即是在这种情况下成书的。这些书里面所列华夏族奉祀的所有祖先中,排在第一位的自非拥有最多后裔并主导这场民族融合的周人的祖先黄帝莫属。这样,黄帝就成为整个华夏民族的人文初祖。
石峁是古代黄帝部族的居邑
长期以来,学者对于黄帝及其所代表的部族的居处,只有一个大致的认识,即认为他们居住在陕北黄土高原一带。尽管这个认识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但毕竟只是一种推测。如果能够通过考古发现使这种推测得到某种程度的印证,将对于历史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令人兴奋的是,近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在陕西石峁进行的考古发掘,正使上述推测一步步得到印证,石峁应当就是古代黄帝部族的居邑。
石峁位于陕北神木县高家堡古镇附近。石峁遗址早就为人所知,因为那里自20世纪初就陆续出土了许多精美的古玉,其中许多玉器流散到欧、美。新中国成立后,有关方面曾对遗址做过多次调查。20世纪80年代初,考古工作者通过对石峁进行的小范围试掘,初步明确了石峁遗址的文化内涵及所处年代的范围,认为该遗址的上限应与陕西关中地区的客省庄二期文化亦即陕西龙山文化的晚期相当,下限已进入夏纪年的范围。对于遗址的规模与性质,人们的认识却较模糊,初以为遗址面积仅5万平方米左右,后定为约90万平方米,遗址的外城墙则被误认为是战国秦长城。近年,伴随着对中华文明探源的热潮,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遗址重新进行了仔细勘测,并对其部分地区进行了重点发掘,始确定该遗址是史前时期一座规模巨大的城址。整座古城建筑在镇东北面的山梁上,由“皇城台”、内城、外城三部分组成,墙体由石头砌筑而成,总面积达400万平方米以上,年代在龙山中晚期至夏代早期阶段,是目前所见我国史前时期最大的古城。
石峁遗址的发现迅即引起社会,特别是学术界的高度关注。不少考古学者得其先睹之便,纷纷对遗址性质发表见解,有称其是“当时北方一个很大的集团”,或一个“酋邦”势力控制的中心,有称其为“北方区域政体的中心”。这些看法基本上都是正确的,如此巨大的一座古城,确实应当是当时一个很大的地方势力集团或一支强势部族活动的中心。但遗憾的是,这些学者似乎都不愿意将石峁古城引入历史研究领域,尤其避免将其与文献所载我国传说时代的历史结合起来进行探究。大概是认为目前有关考古材料在时间与空间上尚未能取得与传说中某个族群或某个历史人物的完全契合,人们不愿意冒然作出将上述考古资料与历史挂钩的判语。
笔者因对西北地区古国古部族有过持续的关注,早就持有黄帝部族与其直系后裔先周族居住在我国西北,特别是陕北及其附近地区的观点。我曾设想黄帝部族生活的那个年代,这一地区一定有比现在更适宜于农业定居生活的条件,也应有比较大型的城址或居邑。及闻陕北神木石峁发现巨大古城及其他遗址的信息后,我便立即想到它应当就是古代黄帝部族的居邑。在我的认识领域,有关考古材料无论在空间上还是时间上,毫无疑问都与传说中黄帝部族的活动地域是相契合的。于是,就有了《光明日报》连续发表的两篇论石峁古城是黄帝部族居邑的文章。
为说明问题,有必要简单回顾一下这两篇文章的主要论点,同时对一些未及充分阐述的问题进行补充论证。首先,关于黄帝部族的活动地域,《史记》《汉书》都有关于黄帝陵墓在今陕北子长县的记载。《史记·五帝本纪》称:“黄帝崩,葬桥山。”《索隐》引《汉书·地理志》说:“桥山在上郡阳周县。”汉阳周县当今陕西子长县北。桥山今称高柏山,属子长县,正在汉阳周县南。《汉书·地理志》并于上郡肤施县下记其地“有黄帝祠四所”,肤施即今榆林。这两个地点都毗邻于石峁所在的神木高家堡。既然石峁附近的榆林、子长一带有古人认定的黄帝的冢墓,还有多处人们奉祀黄帝的祠堂,则黄帝生前和他的部族在此一带居住、活动是无可否认的。
其次,从先秦古部族的分布看,作为黄帝后裔的白狄族亦活动在这一地区。《山海经》及《潜夫论》都揭示了黄帝确实是此姬姓白狄族祖先的史实。至于白狄族分布在陕北一带,则有《左传》《国语》等一系列记载可为之证。由于气候变化等原因,白狄族的一些支系后来不断地东徙南移。
更重要的是,作为黄帝后裔的周族人亦是起源于陕北。我个人曾有过这方面的论文。须强调的一点是,该文除引用大量文献资料外,还引用不少考古发掘的资料,包括引用邹衡先生和田广金先生的有关论述来说明这个问题。尤其邹衡先生,他是明确主张先周族来源于今陕北一带,也就是黄帝族活动的地区的。
谈到石峁古城的年代与黄帝部族的关系,古城的发掘者不止一次声称,石峁古城建成的年代不晚于公元前2300年。黄帝作为我国进入文明前的一位部族领袖,其生活的年代自应在我国第一个早期国家夏朝建立前不久。夏建立在公元前21世纪,则说黄帝部族生活在石峁古城建成的公元前2300年前后,应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以上各点,无论在史实举证上还是逻辑结构上,应该说都是能够站得住脚的。需要对拙文做出进一步解释的,恐怕还主要是黄帝族生活的年代这个问题。大家习惯了“黄帝五千年”这句口号,对于黄帝族生活在距今4300年左右的说法有些接受不了。一些学者只接受石峁古城是黃帝族后裔居邑的说法,不愿直接说石峁是黄帝族的居邑。可是,只要我们冷静地、实事求是地对待历史文献,就完全可以体会到唯有上述说法才更接近于历史真实。
查先秦、两汉时期较早的文献,实无一处说到黄帝距今五千年的;前人,包括民国时期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学者,也没有说黄帝距今五千年的。另有学者从考古学文化角度将石峁与陶寺遗址相比较,认为陶寺文化作为尧的活动遗迹,其时代可早到公元前2500年,若以石峁为黄帝居邑,与史载黄帝远在尧舜之前岂不是颠倒了吗,由是判定“黄帝或其集团与考古学文化相对应的年代至少在距今五千年前”。此说看似有理,实亦经不起推敲。首先,陶寺遗址是否尧的都邑,向来就无定说。其次,说尧距今2500年亦是无据,此何以解释尧舜禹相互禅让而致禹在公元前21世纪建立了夏朝?岂尧至禹中间隔得有四五百年的光景?至于说与黄帝对应的考古学文化在今5000年前,则更属空想。因距今5000年前的我国中原地区尚停留在仰韶文化时代,其时虽有一些物质文明的进步和初步社会分化,恐怕与文献所载黄帝时期战争频仍,黄帝为此而制作礼乐,建立都邑,制定兵符,设置“左右大监”之类官署等社会进步现象不相吻合。倒是考古学家李伯谦对黄帝所在的时代说得比较客观,他虽然主张将黄帝的纪念地搬到中原去,却是说“黄帝生活的时代是距今4500年前后或者4300年前后”,此实与石峁城建成的年代相当接近了。
有关石峁与黄帝族的关系,还有一个方面的证据也必须提及,就是石峁出土的大量古玉器。按石峁自19世纪末或20世纪初以来就陆续有玉器出土,但多流失海外,据说其数达4000余件之多。20世纪70年代,曾有陕西省考古工作者到石峁农家进行文物征集,曾一次征集到玉器127件。之后,又有地方文物收藏者继续在石峁进行采集与收购,所得玉器亦有五六百余。其器类有牙璋、刀、钺、戈、斧、铲、璜、璧、牙璧、鹰首笄、虎头、人首、蚕形器等,但以牙璋、刀、钺等器类居多。由于上述玉器的出土皆未经过正式的考古发掘,对石峁玉器的年代众说纷纭。最近,经过科学的考古发掘,发现这些玉器多藏于石峁古城的墙体里面,从而证明石峁玉器的年代不晚于古城的建成年代,也就是前2300年。面对数量如此巨大的史前玉器,特别是各种款式的玉制兵器,人们不禁想到古文献提到的“黄帝之时,以玉为兵”的传说。
作为这个说法的旁证,我们还可以在《山海经》等反映我国传说时代的古地理书中找到距黄帝族活动区域不远的内蒙古阴山一带出产玉器的相关记载。今内蒙古阴山山脉中确实蕴含有大量玉石矿藏,特别是距包头市不远的大青山里面开采出的佘太玉,产量丰富,材质与玉色与石峁古玉亦相近似。其地距石峁不远,是否与远古石峁居民釆集的玉材有关,颇值得研究。
石峁与周族起源关系再探讨
石峁不仅是黄帝部族的居邑,而且也是古代周族更早的发祥地。关于周朝的建立者周族的起源,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东来说,即主张周人来源于东边的晋南;二是西来说,以为周人出自西边的羌族;三是本土说,主张周人出自关中土著。大家各自持己见,至今未有一致认识。
我于周人起源的看法与以上三种主张皆不相同。我主张周人来自北方,即来自陕北的黄土高原。十多年前我曾写过一篇《周人北来说》的文章,后来又写过一篇《周族起源诸说辩正——兼论周族起源于白狄》的论文。
我相信先周族以前的那个时代,陕北高原必定有比现在更好的自然环境,也有比一般人想象的那样更为繁庶的人群和聚落群。而今石峁古城的发现,连同周围不断挖掘出来的同时期的聚落和城址,不仅证实了我的设想,也更加有力地证明了周族祖先原本就是居住在这个地方的主人。
石峁古城不仅以其巨大的规模展示出它是那个时期当地某个族群(即黄帝部族)重要的政冶中心,它特殊的建筑方式及它蕴藏着的大量古代玉器,更显示出它与周人之间所具有的直接的关系。
谈到石峁城的建筑方式,一般人都会注意到的一个特征是,石峁及其附近所有同时期的城址都建筑在山上,并且往往是建筑在周围地形最髙的山梁上。对此,学者可以给出如下解释,说它是继承了石峁以前的老虎山文化或海生不浪文化的传统。这自然是不错的。但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到石峁以后,将它与岐山发现的先周时期周人建造的也是在山头上的多座城址联系起来,便会立即感到问题并不那么简单。我判断,将城邑建造在山上,正是早期周人一贯的传统。这样来看待黄帝部族将城邑修筑在石峁山梁上,也就很好理解了,因为黄帝是周人的祖先,后人维持祖先的传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至于黄帝族或早期周人为何要把城址建造在山梁上面,大概也不像许多人理解的那样,只是为了防御。我想更大的可能,乃是出于某种宗教或者信仰。周人信仰天,“天”和“天命”都是周人的发明,或许周人认为,城邑建在山上,有利于与天的交通。《左传》称“黄帝氏以云纪”,“以云纪”似乎也与黄帝——先周族对天的尊崇有关,因为云彩本来就是天上的东西
石峁遗址与早期周人的不解之缘的更有力的证据,是这里出土的大量的玉器。上举我所撰写的论周人出自白狄的文章为了辨驳周人并非是一个自来就居住在渭水流域从事农作的部族,曾经对周族的“周”的字义进行过分析,指出它作为象形字,所象并非是农田种植之形,而是雕琢治玉之形,说明周人原是一个善于治玉的民族。如今石峁发现的大批精美的玉器,正充分证明了我的这个判断。这么多的玉器决不会都出自外来的进贡或交流,而主要应出自本地人的制作。早期周人便是石峁玉器的主要制作者。
余论:有关华夏族祖先早期历史的更多思考
本文结合石峁遗址的重要考古发现,集中论述了华夏族起源、华夏族祖先黄帝的居邑就在陕北及其附近、华夏族缔造者姬周族人就是从这里走出的这一主题,但由此引出的有关华夏祖先早期历史的某些重要环节却足以启发人们作出更多思考。例如,黄帝既是古代白狄族人的祖先,白狄族不仅包含作为华夏先民的姬姓周族这一支,也包含其他姬姓之戎,如犬戎、骊戎、无终、鲜虞等各个支系。这就使人联想到,原来早期华夏与所谓戎狄其实也具有千丝万缕的血缘联系,华夏、戎狄其实就是一家。这些戎狄族有的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逐渐融进华夏,如骊戎、无终、鲜虞等,有的则再分蘖出新的族系,或衍变发展成为以后历史上的其他少数民族,如战国时期的林胡(儋林)、楼烦、匈奴等等,甚至今天北方的某些少数民族也和早期白狄族有着源远流长的关系。由此推而广之,今天的中华民族也应当是一个由古代华夏及众多蛮、夷、戎、狄等少数部族融汇而成的大家庭,黄帝不仅是华夏——汉族人的祖先,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由此看来,我们过去长期流行的夷夏观,是否应当做出一些调整呢?
先周族作为华夏先民,也作为白狄族的一支曾经居住在祖先黄帝所在的地域,他们和其他一些白狄族民必定和更北方、西北方乃至域外的一些部族有着物质文化上的往来。现石峁及周围地区的考古发掘已能提供不少这方面的线索。例如石峁发现的青铜器物,学者就指出它们或是从阿尔泰地区经由今蒙古国南部和我国内蒙地区直接传播到陕北高原的。其中一件若干年前发现的与数枚玉环、玉瑗套装在一起的砷青铜制作的齿轮状铜环,不仅其冶炼技术可能来自域外,其形制与其所蕴含的宗教义蕴,恐怕也与域外有着直接的联系。石峁玉器的材质有相当部分来自北方和西方,这大概是学者一致的认识。还有那为数众多的石雕人面像,其制作风格和表现形式,包括其背后隐含的原始宗教义蕴出自西方的人群,大概也不会有人提出异议。所有这些,都表明早期中西文化交流的存在,也显示了石峁在早期中西交通要道上处在一个重要的地理位置。这当然也是和石峁作为中国北方人群(白狄族群)政治中心的地位分不开的。故学者提出诸如早期丝绸之路、玉石之路、北方草原之路之类有关古代中西交通的命题,无疑都是值得研究的,也是华夏族早期对外关系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古代内地与西域乃至更远的西方的交通,绝不始自张骞。今石峁一带的考古发现,无疑为上述命题提供了新的依据。
——石峁遗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