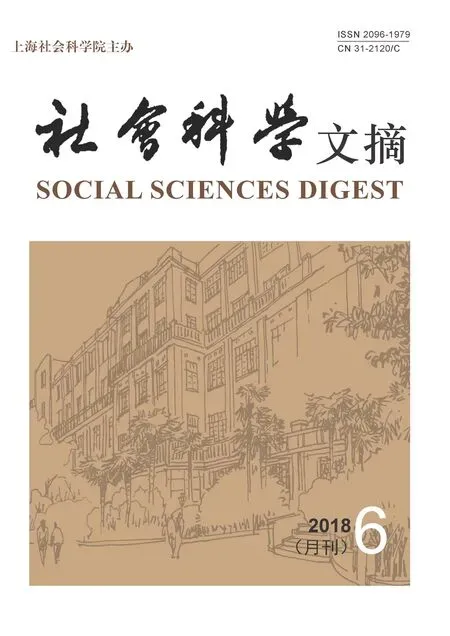国家理论:电影理论中的中国学派和中国话语
文/陈犀禾 翟莉滢
引子:“中国没有电影理论”
电影理论是一个长期被西方学派和话语把握的领域。记得20世纪80代中国开始编撰《中国大百科全书·电影卷》的时候,时任编委会委员的程季华1986年曾经找我谈过一次话。他告诉我,编委会在讨论拟设条目时,对是否应该设立“中国电影理论”的条目发生争议,时任编委会副主任、著名电影导演和理论家张骏祥认为:中国没有电影理论。张骏祥当时作为电影局的领导、且学贯中西(张早年留学耶鲁)、创作和理论成果累累,可以说是一言九鼎(当时《中国大百科全书·电影卷》的主任虽然是夏衍,但因年事已高,张骏祥是主要负责人)。程季华作为中国电影史的专家,对此难以认同,他会后找到我并征询我的看法。我当时刚刚从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系毕业,参加了钟惦棐领导的“电影美学小组”,1986年初发表了《中国电影美学的再认识》,提出并阐释了早期中国电影理论中的“影戏说”,主张它是可以和欧洲同时期先锋派理论和蒙太奇理论相提并论的中国电影理论。所以,我对程季华明确说中国有电影理论,并阐述了自己的观点。程季华立即确定让我负责撰写《中国大百科全书·电影卷》中的“中国电影理论”条目。我后来找到我的同学钟大丰合作(他曾对中国早期电影中“影戏电影”的形式和风格进行过深入研究),他负责撰写49年以前部分,我负责撰写49年以后部分。整个词条约六千余字,在1991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电影卷》第一版中正式发表。
从这一事例可以清楚看到,从文化大革命阴影中走出来的20世纪80年代,在文化思潮和理论上的一个重要倾向是向西方学习,西方的理论规范和话语深刻影响了那一代许多电影学者和艺术家。20世纪80年代这一开放过程在中国电影发展的道路上打下了它的烙印,推动了新时期中国电影的发展,但是它也常常遮蔽了我们自身的理论传统和学术话语。
中国经验和中国话语
事实上,中国电影人从上个世纪初拍摄电影开始,就有了关于电影的理论思考,如20世纪20年代的“影戏说”,20世纪30年代的“软性电影”理论。前者有浓厚的本土色彩,后者则可以明显看到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但是一些西方学者仍把它看作是一种中国的本土论述)。然而对当代中国电影产生了长期而持久影响、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在当代中国电影中最重要的理论话语则是“国家理论”。所谓“国家理论”,广义上可以指一切对电影和国家关系的理论思考。具体地说,是指主张把电影作为一种体现国家意志和维护国家利益的电影本体论思考。它可以体现在电影批评、历史研究和理论研究等各种形态中,但是其核心原则是把电影功能和国家利益紧密相连,发展和建构起一套从社会功能出发的电影本体论思考。
早在新中国建立之初,毛主席在亲自为《人民日报》社论撰文《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一文中,就为建立这样一种电影观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影片由从20世纪30年代就在上海从事进步电影运动的孙瑜导演,赵丹主演。影片一出来(1950年底),就受到当时报纸和媒体的一片好评。但是,毛主席显然对《武训传》和影片歌颂的以传播文化为己任的武训其人持有不同的观点,他质问道:(影片表现的)“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像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应当歌颂的吗?”显然,毛主席把对一部电影的批评放在千头万绪的国家大事的重要位置,绝不是偶然的。当时是在新中国建立之初,百废待兴。当时的文化界、电影界对于新中国的文化和电影将要走向何方显然并不清楚,许多人(包括《武训传》的创作人员)以为上海电影中的传统将会原封不动得到延续,事实证明他们错了。在毛主席看来,如果1949年以前的电影应该为打破一个旧中国服务的话,那么1949年以后的电影就应该为建设一个新中国服务。不认清这一点,就可能导致《武训转》所暴露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事实上,他当时对建设新中国的文化和电影已经有了一幅清晰的蓝图,并准备把它付诸实施。对《武训传》的批判可以看作这种改造和建设的第一步,也是1949年以后中国当代文化重大转向的一个明确标志。
在批判《武训传》的文章中,毛主席明确表达了一种新的关于电影的思想,即要求电影服务于新的国家和新的社会,并提出了电影中应该如何展示新的国家形象:即歌颂“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反对“压迫中国人民的敌人”和“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由此确立了以新的国家为核心价值的新中国电影的发展方向,也确立了以新的国家为核心价值的新中国电影批评和研究的典范。在随后的年代中,中国的电影批评和研究通过批判许多当时认为不健康的电影,鼓励在银幕上塑造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新人,同时对理论和批评战线以《电影的锣鼓》和《创新独白》为代表的一系列错误倾向进行了严厉的清算,为给新中国电影建立了一种以国家为核心价值的经典理论理清了思路。
中国电影思想中的国家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一度走向边缘。那是一个“和戏剧离婚”的年代,一个影像本体论的年代,一个崇尚心理分析和符号学年代。80年代中后期“主旋律”概念的提出,为中国电影中的国家理论续上了香火。20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社会和政治氛围的变化,西方的后殖民理论恰当其时地被引进中国。王一川、张颐武等中国学者运用后殖民理论对当时红极一时的第五代电影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一时颇为引人注目,可以看作是国家理论在电影研究界的重新抬头。随着全球化不断深化,民族国家意识的强化,国家理论终于在世纪之交全面激活,并在21世纪初的中国电影研究中重新走向中心,并形成以下几大主题,如:
1.当下中国电影理论和批评中关于“国家形象”的研究;
2.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电影民族性研究;
3.国家电影产业研究;
4.好莱坞电影在中国市场和对文化影响的研究;
5.中国电影“走出去”研究;
6.电影中的国家文化安全研究,等等。
和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理论的传统阐述相比较,新的国家理论也与时俱进,在关于电影的题材、电影的创作方法、电影的形式和电影的功能方面都有新的调整,如电影的功能,新的提法是“塑造国家形象”“传播主流价值观”和“增强软实力”。在以上种种发展和调整中,国家理论的核心原则:把电影功能和国家利益紧密相连,没有变。
国家理论和中国学派
相对于西方电影理论在早期注重于影像本体的研究(如关注于认知心理的影像美学、蒙太奇和长镜头理论等),1949年以后的中国当代电影研究在毛泽东电影思想的指导下发展起了一种不同于西方的电影理论:国家理论。国家理论是一个以国家为核心价值的电影理论和批评体系。在这一体系中,在西方电影理论史中被置于核心地位的电影艺术形式和特性的研究则被置于工具和应用(形而下)的层面,而对于电影如何表达国家身份和服务于国家利益(当时刚刚成立的新中国)成为核心议题。这一理论建构在十七年时期达到了相当成熟的地步,而在新世纪以来的发展中所达到的的完整性和系统性是史无前例的,并涌现了大量成果,对当代中国电影创作实践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巨大的影响。事实上,它比世界上在20世纪60年代世界电影思潮中提出的“第三电影”理论、民族电影理论和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发展起来的后殖民理论等思考电影和国族关系的理论要早得多。
第三电影理论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形成了美苏两国为主导的全球权力体系。一些殖民地也摆脱了殖民控制,独立成为现代民族国家,形成了一股新兴的政治力量。在此背景下,1950年法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人口学家与历史学家阿尔弗雷德·索维提出了“第三世界”的概念,这一概念是以法国大革命时期“第三等级”(即平民)提法为根据而衍生的。据此,“第三电影”就是指“第三世界国家即工业上欠发达的国家部分的电影生产”。这一概念首先出现在1969年3月的古巴电影期刊《Cine Cubano》的一篇对阿根廷电影团体“解放电影”的采访报道中,该团体认为“第三电影在陈述上和意识上都是革命的,它会发明一种新的电影语言,以便创造一个新的意识和新的社会现实”。随后弗尔南多·索伦纳斯和奥克泰维尔·杰提诺的重要文献《迈向第三种电影:发展第三世界解放电影的笔记和实验》(1969)将电影分为三类:“第一电影”为好莱坞电影;“第二电影”是欧洲艺术电影,是“第一电影”的另一条出路;而“第三电影”则是“在革命性开创中迈向一种立于体制之外,与体制对抗的电影”,是一种“解放电影与游击电影”,一种“去殖民化文化”,是一种革命电影。总而言之,第三电影理论从早先更多关注影像本体及创作者的心理分析,转向对民族国家话语建构的关注上来。
后殖民主义的学术思潮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关注被殖民国家在后殖民时期在文化与意识形态领域的“国族身份”。后殖民主义理论在学术界影响力巨大,爱德华·萨义德所著的《东方学》(1978)是这一领域的经典著作。萨义德将研究目标指向了被西方学术界边缘化的东方或第三世界,并且他“使用了福柯的话语概念和权力-知识连结的概念来考察西方帝国主义的权力和话语如何建构了一个程式化的‘东方’的方式”。他认为“西方和东方之间存在一种权力关系、支配关系、霸权关系”,并且东方“可以被制作成、被驯化成‘东方的’”,还时常扮演着相对于西方的“他者”的角色。可见,“东方”除了指涉其地理位置,还蕴藏了强烈的政治与文化内涵。总之,在萨义德的理论中,在意识形态上制造代表“理性”的欧洲和代表“非理性”的东方是同时进行的,东西方的表征被锁定在相互连接但并非对等的权力关系之中。后殖民理论也常常被借用成为电影批评范式之一。萨义德就曾集中以西方电影中的阿拉伯人形象进行批判,形成了独特的、具有电影理论视角的话语。
在学术主题上,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第三电影”理论和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发展起来的后殖民理论都着重思考了电影和国族的关系。但是在学术品格上,后殖民理论更为精致和更注重阐释性,对后殖民文化的混杂性、“模仿”和“协商的第三空间”津津乐道;而第三电影理论既注重阐释性,也富于实践性,试图给发展中国家的民族电影指出方向,具有一种建设性的品格,它和中国的国家理论比较接近。这可能和理论话语建立的时代相关,因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一个世界革命风起云涌的年代,而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世界局势则相对平稳。但是,第三电影理论由于对好莱坞叙事美学取绝对的排斥态度,反而在实践中难以为继,走入了尴尬境地。而中国的国家理论在艺术风格上则强调大众化和人民性,并没有陷入精英主义美学的死胡同。
从时间上看,毛泽东的电影思想远早于第三电影理论,是一种具有原创性和生命力的电影思想,其理论资源至少还可以追溯到20世纪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在讲话中系统阐述了文艺“为什么人”和“写什么”的问题。毛泽东在革命最艰苦的抗战年代来谈文艺当然绝不是“为艺术而艺术”,而是为了革命和政权。更早还可以追溯到列宁关于电影的论述。列宁早在建立俄国苏维埃政权时就说过:“你们必须牢记,在一切艺术中,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就是电影”。所谓“最重要”,当然是指电影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政权(国家)的重要性。除了列宁和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他们的革命思想也对艺术的国家理论有重要贡献。
国家理论的另外一个重要的理论资源则是中国传统的文化哲学。首先,中国传统文化哲学的学术品格历来强调经世致用,有一种“功能主义”的基因(这里只是就方法论的意义而言,并非指西方哲学中的“功能主义”),接近实用主义。例如中国的儒学,强调“入世”和“功业”。中国学术对物质世界的思考也常常贯彻了一种功能主义的路线,如中华医学中所谓的“肾为先天之本”,其中“肾”的概念主要是一种功能性系统,而不是西医解剖学意义上的“肾脏”。而当代最著名的例子则莫如邓小平的“猫论”:“不管黑猫白猫,能捉老鼠的就是好猫”。这里,对“好猫”的定义并不是从解剖学(生理结构)的角度出发,而是从现实功能的角度出发。其次,中国文化历来有“文以载道”的传统。中国早期的电影理论,如“影戏论”和“软性电影论”也贯穿了这种文化基因。这一以功能为导向的电影本体论思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得到了延续,并整合了新的理论资源,发展成为一种新的“国家理论”。
结语:国家理论和中国梦
今天,我们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我们面临着在中国文化和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建设中,创建中国学派和中国话语的任务。我们以为,中国学派不可能凭空建立,具体到电影理论和批评,中国电影理论和创作批评中的关于国家理论的历史经验和当代成就是建立中国学派的宝贵资源。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主持召开文艺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文艺要服务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鼓舞全国各族人民朝气蓬勃迈向未来”。习近平的讲话继承和发扬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精神,并对今天新时代文艺的性质进行了系统阐述。“中国梦”思想作为国家建设的宏伟目标将对当下中国电影研究中的国家理论建构产生深远的影响。在刚刚过去的十九大上,习近平主席又再次强调社会主义文艺需“不断推出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精品力作”,并且以“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为目标。其中,“国家”的主题跃然而出,并增加了一种全球化的视野。
基于以上历史和现实,我们认为国家理论应该成为电影理论和批评中的中国学派和中国话语的重要建设课题之一。当然,作为一种理论话语,国家理论强调体制中心和党的引领,未来可以在其内含的人民性的内涵方面作进一步阐述,强调中华民族文化的立场和主体性,这样更有利于中国学派介入和形塑世界文化的新格局,使中国学派(象在经济和政治领域一样)成为当代世界文化版图中具有重要地位和向心力的一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