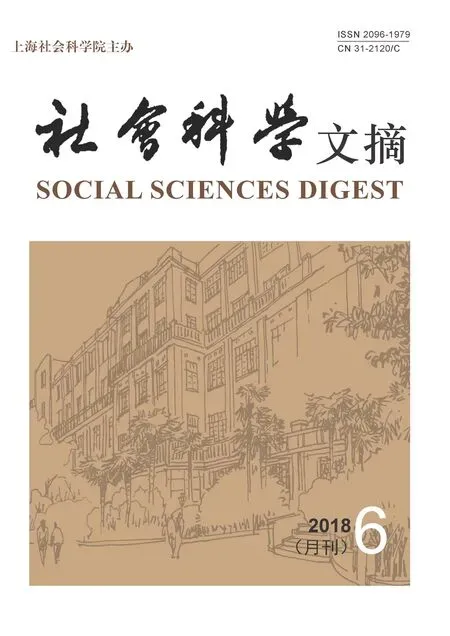近代上海城市对于贫民的意义
文/熊月之
关于近代上海城市社会的叙事,有两种最为人们所熟知:一种是穷人遍地,棚户连片,食不果腹,衣衫褴褛;一种是两极分化,极端悬殊,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这两种文字又往往糅合在一起,直指其间的因果关系,认为穷人遍地正是城市两极分化的结果:
上海是富人们的天国,穷人们的地狱。富人在高大的洋房里,电风扇不停地摇头,吐出风来,麻将八圈,眼目清亮,大姐开汽水,娘姨拿香烟。穷人们在三层阁上,亭子间里,闷热得像在火炕上,臭虫蚊子,向你总攻击,大便在这里,烧饭也在这里,洗浴与卧室也在这里。
在这强烈对比、义愤填膺的叙述中,很少有人仔细分析,这些穷人是怎么出现的?他们到底是先贫而后进城,还是进城以后变贫的?城市对于这些穷人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本文试图对此做一分析。
上海:近代中国吸纳贫穷人口最多的城市
所谓贫民,是与富人相对的概念,指物质财富匮乏之人。按照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标准,恩格尔系数在59%以上者为贫困,50%—59%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为富裕,低于30%为最富裕。乔启明根据卜凯、李景汉等人对6省农村2854户人家的抽样调查结果推算出,1922—1934年间,中国农村人口的消费支出中,食品、衣着、房租、燃料灯光、杂项所占比例分别为59.9%、7.1%、4.6%、10.4%、18.0%,恩格尔系数已达到60%,临近绝对贫困状态,可见当时农村居民基本上是贫民。依此标准,则中国农村除了地主、富农以外的广大农民,包括中农、贫农、雇农在内,均属贫穷人口。
中国各地的地主、富农所占比例多少不一。学术界依据民国时期各种调查数据综合分析,认为民国时期中国各地总平均,大约地主占3%,富农7%,中农20%,贫农和雇农占65%,乞丐、流浪者或其他不从事耕作的贫民,约占5%。不过,地主这一比例放在江南一带就显得比较高。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东方杂志》的调查结果显示,上海附近的地主占农民总数的1%,武进占1.4%,句容占2%,靖江占3%,浙江鄞县占5%,松江竟然是0%,只有太仓最高,占10%。
尽管在战乱情况下,地主富农也会离开土地进入城里,在承平时期,地主富农为了事业的发展,或为了过更好的生活,也会移居到城里,但是,在灾荒来临或迫于生计的情况下,广大农民更易于被推出农村,流入城市。按照这样的阶级比例与流动可能性而言,将进入城市的绝大多数人视为贫民,是不会与实际相背离的。
上海在1843年开埠时,城市人口20来万,1900年超过100万,1915年超过200万,1930年超过300万,1949年达到546万。这些急遽增长的人口中,属于自然增长的很少,绝大多数为机械增长,是从全国各地迁移来的。到1949年,上海80%以上的人口是从外地移入的。1947年,上海人口430万,几乎是天津(171万)、北平(167万)与南京(103万)三大城市人口的总和。所以,说近代上海是中国吸纳贫穷人口最多的城市,也不会背离实际的。
再看上海城市贫富人口的比例。1935年,上海华界农、工、劳工、家庭服务、学徒、佣工、无业人员,共占总人口80.9%;公共租界农民、工人、交通运输业、家务、杂类人员,共占总人口80.0%。这个比例,不包括商业与文教方面的人口,因为商业与文教方面人口中,有富有穷,没有确切统计。如果加上一定数量的贫穷商人与文教方面的人口,则无论华界还是公共租界,穷人的比例都超过80%。
一波又一波的贫民涌入上海,或为逃避灾荒,或为躲避战争,或为谋生发展,这几种因素往往交织在一起。19世纪50年代末,“黄河决口,江苏北境竟成泽国,人民失业,无家可归者,无虑千万,咸来上海就食”。以后,江、浙、皖一带,每遇水旱灾害,每遭战乱,农民总习惯于逃往江南,逃往上海。在1个多世纪中,共有3次因躲避战争而发生的涌入上海的移民潮。第一次是太平天国期间,长江中下游地区尤其是江、浙一带,战事频仍,大批难民涌入上海,从1855年到1865年,上海人口一下子净增11万。第二次是抗日战争期间,上海两租界人口增加78万。第三次是解放战争期间,上海人口增加208万。
城市为贫民提供了就业机会
穷苦农民进入城市以后,无论是工作还是待业,其身份都发生了改变。近代上海以下各类人员,基本上是由农民直接转化或稍加培训以后转化而来的,即工人、农业人口(农业、林业、花果、畜牧、渔业)、交通运输(服务于一切舟、车邮电行业)、劳工(人力车夫、肩夫工人)、家庭服务、学徒、佣工、杂役(理发、镶牙、扦脚、擦背)、无业(流浪汉、捡垃圾、乞讨、废疾、无正当职业者)。
就比例而言,工人最多。上海自19世纪50年代起,已有一些船舶修造厂出现,产生了一些工人。到1894年,上海工人已有5万人。甲午战争以后,外资在上海投资速度加快,清末新政时期及民国建立以后,民族工业奋起,上海逐渐成为全中国工业中心,工人数量急遽增多。1919年,上海工人总数已超过51万,其中工业工人超过18万,交通运输业工人超过11万,手工业工人超过21万。1936年,全市产业工人46.4万人,占上海在业人员的21%。1949年,全市工人122.5万,占总人口四分之一。
近代上海工业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轻工业为主,劳动密集型为主,技术含量较低,职业门槛较低。1930年,曹家渡的230户中,男工与男童工的58%是文盲。1935年,上海印刷工人的79%是由农民直接转化而来的。上海某纱厂的男工,60%目不识丁,能读自己姓名的占40%,能写自己姓名的占20%。同一纱厂的女工,目不识丁的占85%,能读自己姓名的占15%,能写自己姓名的仅8%。
仅次于工人群体的是家庭服务业人员。从1930年至1936年,此类人员在32万至48万之间浮动,占在业人口的20%至22%。此类人员与执业门槛同样不高的佣工人员相加,约占在业人口的26%。
还有一类人员所占比例也很高,即无业人员,包括失业者、无业者以及在家庭里操持家务而不外出工作的人。从1930年至1936年,上海华界此类人员在28万至35万之间浮动,占华界人口的16%至18%。1946年,此类人口97万,占总人口33%。1949年,此类人口近126万,占全市人口25%。
以上三类,即工人、家庭服务业人员与佣工、无业人员,都对文化要求与职业门槛要求不高。此三类人员相加,几乎占上海15岁以上人口的四分之三。就经济收入与生活程度而言,与商人、军政人员、新闻记者、工程师、律师、会计师、医生、教师等职业相比,这三类人员多属贫穷。这些人中又可以分为三种情况,即比较贫穷、非常贫穷与极端贫穷。
就工厂工人而言,尽管其中有工种的不同,有技术含量高低的差异,有熟练、非熟练的差异,但从总体上说,其实际经济收入和社会评价,都不是社会最底层。只要有份稳定的工作,其个人与家庭的温饱是基本能够维持的。相关研究成果表明,20世纪30年代前半叶,尽管有经济恐慌等各种波动,但上海工人阶层的生活状况总体上是基本稳定的,其工资收入基本稳定,工资率波动并不很大,生活程度基本稳定,生活费指数起伏较为有限。
在城市职业群体中,工人的经济收入与社会评价,不及公务员、商人、律师、会计师、医生、教师等脑力劳动者,但比其人力车夫、码头工人要高一档次。一个熟练技术工人的工资,大约相当于最低级文官的一半,小学教师的三分之二,大学教授的十几分之一。但是,比起人力车夫、码头工人等劳工来说,他们则好许多。1929年,上海市社会局对沪南、闸北等7个庇寒所之类单位收容的1471名游民进行问话,发现被收容人员之前所从事的职业,或为无职业者,或为小工小贩,或为退伍兵、店伙人,或为车夫、船工,其中做过机器工人的只有4人。这也说明,由产业工人沦落为游民的几率极低。
与乡村农民比起来,工人更是令人羡慕的职业。上海工人的收入比起农业劳动者要高得多,雇佣工人的最高工资是农业劳动者的7—10倍,最低工资也是农业劳动者的3—7倍。1933年,全国制造业工人平均工资为178元,而农村劳动者的平均年收入只有26元,前者为后者的6.8倍。与上海以外的其他城市相比,上海工人的收入也是较高的。同一时期,南通大生纱厂工人的平均工资要比上海纱厂的工资低10%至20%,上海火柴业工人的工资是重庆同类工人的2—3倍。
民国时期已有学者总结说,就工资水平而言,无论供食不供食,都市均高于农村,大都市工资高于小都市与内地城镇,“就此月工工资而言,农村工资低而小城市工资高,大都市工资更高。此所以农村人口要从农业转移到工业,要由农村到小城市,再由小城市到大城市了”。
由此可见,评价近代上海工人生活水平与社会地位,要注意两个维度。其一是低水准,诚如张忠民所说:“必须肯定的是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工人及其家庭,无论是工资水平还是生活程度都是低水准的。这一低水准至少可以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与国外工人阶层比是低水平的;二是除了城市中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城市贫民、无业游民阶层之外,与其他社会阶层比,也是低水平的;三是就其生活程度以及消费内容来看,也就仅仅是只能够维持最基本温饱的低水平消费。”其二是有提升,无论从实际经济收入与生活水平,从社会声望还是自我感受,无论是与乡村还是与外地城镇相比,那些由农民转化而来的上海工人,其生活质量、社会声望都有所提升。工人阶层在上海城市社会所处的地位,属于比较贫困的一群,但不是非常贫困、更不是极端贫困。
相对于工人阶层来说,人力车夫、码头工人等属于非常贫困的群体。民国社会统计分类中,通常将此两类人归为“劳工”一档。人力车夫是上海数量可观的一个群体,1930年有8万人,1937年约11万人,且不包括数量相当可观的自用人力车的车夫。由于人多车少,他们往往两人或三四人合拉一辆车,拉一日闲一日,每月拉车约15—18天,呈半失业状态,平均每月净收入只有8—10元。这个工资水平,相当于同时期工人中收入最低的缫丝业的女工收入,只及工厂男工收入的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码头工人的工作更是辛苦万分,笔墨难摹。民国时期,上海码头工人曾多达10万人。
人力车夫与码头工人的工作强度大,时间长,收入低,社会评价也比较低。他们的名字通常与棚户区、滚地龙连在一起。但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比起失业者、流浪汉,比起守在家乡的村民,他们的境况,还不是处在社会最底层。据调查,车夫每月拉车净收入为9.23元,这个水平比起农民来,还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诚如调查报告所称:“人力车夫大都为农村之破产农民,在乡间无法维持生活而来沪谋生者。彼等因未受过教育,无专门谋生之技能,遂不得不仿效牛马以图生存。……今日之下,农村破产,方在制造大批人力车夫后备军,源源而来沪求生。”
与人力车夫和码头工人相比,还有更差的群体存在,这就是无业人员,包括流浪汉、捡垃圾者、乞讨者以及其他无正当职业者。此类人员为极端贫穷者,处于社会最底层。上海历年职业统计中,有的时候将流浪在社会上的无业人员,与待在家里不上班的从事家务劳动者一并统计,有的时候分开统计。1946年将此两类人员分开统计,流浪在社会上无业人员有139968人,以闸北、洋泾两个地方最多,闸北区有15742人,洋泾区有11799人。这类人员来源比较复杂。1929年的调查表明,其中有逃避债务者,有退役士兵无业可就者,有不堪师傅虐待而外逃者,有吸毒、赌博、嫖娼堕落的,有因年老体弱无法就业者,但大多数是因穷失业、来沪谋生而未果的。
包括乞丐在内的各式流浪者的收入,没有确切的统计资料。据研究,拾荒、拾煤的儿童,每天可得三角左右,拾垃圾约月入五六元。拾荒者,走街串巷,收拾破烂,卖到旧货摊上,每天可得二三角钱;码头丐,即专候在码头上帮人扛包抬货(不属于正式码头工),生意好时,每天能得七八角钱;拾香烟头丐,将拾到的香烟头汇拢起来,卖给人家,每天所得之钱,也能免除饥饿。
此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流浪者进了收容所,或者流浪街头,居无定所。从晚清开始,上海租界、华界就陆续建立了一批收容所、庇寒所之类机构,收留流浪者。1868年,上海公共租界开放了一批房屋,收容乞丐。同治初年,公共租界会审公廨谳员陈福勋出面,在新闸大王庙后,建立上海栖流公所,经费由沪上富商捐助。公所占地13亩,收留了众多无家可归者,并对他们进行就业培训。1891年,北四川路上也有名为元济堂的收容机构建立。民国时期,上海各式收容、教养机构更多,包括沪南有四个庇寒所、闸北有一个庇寒所,有淞沪教养院,宗教界设立的一些教养机构,各种同乡组织也有一定的收容功能。上海市社会局对1927年所办各种收容、慈善事业进行统计。计施医695752号,施药89686元;设义务学校25所、有学生4677人,习艺所4所、学生215人;收养贫病3734人,收养贫儿511人,教养游民120人,留养迷拐妇孺358人,留养妇孺587人,养老213人。
民国时期,上海市社会局的职员曾分析上海游民何以如此之多的原因,将其归纳为三点:“上海固工商业发达之区,而亦游民荟萃之处。盖以工商业发达,四方之慕名而来者众,以上海一隅之地,势无以应各方之所求,于是谋业而不得者,不久而为游民矣。又以上海绾中外交通之枢纽,道出是途,流连繁华,任情挥霍,囊用皆空而流落者,胥皆一变而为游民矣。此外如自甘堕落,以及工商业衰败,失业为游民者,又更仆难数。”其实,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与上海收容流民的能力有关。流民的源源不绝与城市收容能力有相互刺激的关系。流民越多,收容呼声越大,收容努力越多,则收容能力越强。收容能力越强,对于外地流民的引力又越大。这是包括乞丐、流浪者等在内的上海流民越来越多的原因之一。
上海工人运动为何难以成功
上海城市与乡村直接的血脉联系,城市贫民的多层次性,赋予上海产业工人以浓厚的中国特色,直接影响了近代上海工人运动的进程。
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最为集中的地方,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进行工人运动的重点。但是,历次运动的效果,特别是大革命失败以后的运动效果,并不理想。这方面,学界已经有了很多的研究成果。王建初等人正确地指出,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到1936年,中共领导的工人运动,一直处在“左”倾错误支配之下,导致白区工人运动惨遭失败。“左”倾教条主义者不懂得把马列主义原理同中国工运具体实践相结合,不愿意去研究中国工运的实际,只想生搬硬套外国模式,把革命的中心规定在城市,特别是中心城市,总是驱使工人群众去孤军奋战,一次又一次地组织城市工人起义,一味蛮干,结果导致工人运动一次又一次的失败。裴宜理则从中西比较的角度来分析这一现象,指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国仍是一个分裂的社会,没有哪一个阶级能够独占上风。中国的资本主义还很不发达,中国工人阶级还极其弱小,与这一时期社会相合拍的,并不是建立在对应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资本论》的理论。他们的分析都很有道理。
值得补充的是,在上海这样的急剧膨胀起来的社会里,无论是产业工人还是苦力工人,都主要是刚刚离开乡村的农民,他们与乡村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血脉联系,其经济收入与社会地位,都无时不处于与农村的比较之中。经验告诉他们,他们在上海的生活,比在乡村更好,更能维持,更有盼头。特别是产业工人的社会地位,并不处在社会的最底层,在他们的周围,就有远不如他们的大批苦力存在,还有连苦力都不如的大量失业、无业群体存在。庞大的苦力与无业群体,映衬出产业工人还算不错的社会地位,虽然比较贫穷但有令人羡慕的地方,还有一大群待业群体在觊觎他们的位置。普通工人可能不懂得很多理论,但“他们不是党派陶工手里的陶土,可以随意捏弄”。当工运积极分子照搬“左”倾教条主义理论,来发动这些普通工人去搞那些与工人实际利益完全脱节的飞行集会时,他们怎么可能心甘情愿、全力以赴地去参加呢!据研究,1928年至1936年,上海市劳资纠纷和罢工原因中,占据首位的是雇佣和解雇问题,其次为工资问题。9年间,围绕着雇佣和解雇问题而发生的劳资纠纷共1590次,占纠纷案件总数的65.35%。“工人无论是罢工停业还是劳资纠纷,保护自己和他人工作的保险系数是放在最重要的位置的,其次才是考虑工资问题。”工人关心的首先是有没有饭碗,其次才是饭碗里饭的质量。
从全国范围来看,农民离开乡村到城里寻找工作,与离开乡村到军队里当兵吃粮,看上去不一样,但究其实质却高度一致,都是离开业已破产的乡村,寻求新的发展空间。农民在城里有了工作,哪怕收入不那么高、环境不那么好,但比起乡村农民来,算是已经上了一个台阶了。所以,“左”倾教条主义者照搬共产国际的理论,搞城市暴动,脱离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处境,只能处处碰壁。毛泽东发动农民起来,打土豪分田地,再农村包围城市,最后获得了成功。
城市集聚的多重效应
近代上海作为中国特大城市,是多重集聚的叠合。其中,最基本的是产业集聚、人口集聚与财富集聚。产业集聚带动了人口集聚,制造业、交通运输业的集聚,吸纳了众多的人口,于是,将那么多的农民变成了产业工人。人口的持续集聚,刺激了商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的发展,刺激了饮食、旅馆、理发、浴室、环境卫生保护等各种服务业的发展,于是,又将那么多的农民变成了第三产业的工作者。产业集聚、人口集聚,加上由于租界存在带来的上海城市的安全因素,使得全国各地富人麇集上海,促进了上海的财富集聚。
人口高度集聚,刺激了分工,促进新的行业发展。在上海,捡垃圾、缝穷婆、推车丐、拾香烟头、掏大粪者、算命打卦者,都可以维持最低生计,都能自成一行。这种行当,只有在人口集聚到一定规模的时候,才有可能被分化出来自成一业,在人口稀疏的乡村或只有两三万人口的小城镇,是很难形成的。以命理行业为例,1928年,在上海从事星相占卜的人就有23400余人。1931年,上海华界从事卜筮星相人员623人。1946年,上海星相同业公会成立,有四百多人参加,后改名命理哲学研究会,在社会局登记,成为正式社会组织。这种组织,在乡村或小城镇是不可能出现的。
任何行业、阶层人员的高度集聚,都会带来三大效应:
一是凸显自身存在的实体效应。乞丐多了,就能形成乞丐团体,理发师、命理师、掏粪工都能自成组织。三两个乞丐,你可以不在乎他们的存在。有三五十个乞丐、甚至三五百个乞丐,结成一个团体,有组织,有头领,社会、政府对他们就不能视而不见。人员集聚,行业形成,各种业内分工、行为规范就会出现,就会将分散变为集中,将无序变为有序,将无机变为有机,就能提升本行业的生存能力与活动能力。
二是人员个体素质的提升效应。城市人口高度集聚,异质文化共处,导致人际空间的接近性,使得商品交换与思想交流更加方便,使得城里人较乡下人更见多识广,更容易具有现代性。兹以女性素质为例。相关研究表明,上海女性更具有独立性,更具有现代意识,职业女性尤其如此。1932年至1934年离婚案件统计表明,无论哪一年份,女方主动提出离婚的案件都远远高于男方主动提出的案件,最高的是1933年,女方主动者占10.1%,男方主动者占1.4%。这一现象,与乡村正好相反,反映的是女性自主个性的崛起及权利意识的觉醒。
三是与其他个人、团体、机构对话、竞争时的拳头效应。在上述两个效应,即实体效应与素质提升效应的基础上,各种体现本行人员的经济、社会乃至政治方面的诉求,就能被集中、提炼出来,本行人员的各种能力就能被聚合起来,从而形成集体意志与群体力量。青帮在民国时期的上海能有那么大的能量,以至于任何一个群体、任何一个党派、任何一届政府对其都不敢小觑,其实就是达到一定规模的游民、经过一定方式的整合、利用上海一市三治的缝隙而呈现出来的拳头效应。
集聚在上海的那么多穷人,除了进工厂当了工人、进商店成了店员、进机关成了职员之外,他们并不属于某一个行业,也没有经过高度的整合。但是,他们生活在上海这个有限的空间里,集聚在闸北、南市、杨树浦与浦东一带,还是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上面所说的三个效应。近代上海穷人集中的地区,无论在闸北、南市,还是浦东,都有廉价的房子、廉价的饮食、廉价的茶馆、廉价的医生、廉价的教师、廉价的学校、廉价的娱乐场所(诸如“江北大世界”),从而成为虽然贫困但又相对自洽的贫民社区。这就是聚合效应的典型表现。
与充满活力的上海社会大系统紧密地联结在一起,贫民集聚会给贫民催生出向上浮动的期待。因为,在他们身边,就有从贫民区走出的成功人士:上焉者如商务印书馆的创始人夏瑞芳、鲍咸昌,如卖水果出身的青帮大亨黄金荣、杜月笙,拉人力车出身的顾竹轩;中焉者如从土山湾孤儿院以及其他各种贫民院、教养院走出来的一批批画工画匠、各种技术人才;下焉者则有难计其数到工厂里当工人、到店里当伙计的人,有些人就是从这些棚户区走出去的,或者现在还生活在这些地方。
贫民集聚的一个后果,就是使得贫民问题凸显,引起社会各界重视,迫使政府下大力气去解决。同样死亡十个人,十个人横尸街头,与十个人抛尸荒野,其信息呈现、媒体关注、社会关心的程度,会有天壤之别,前者可能成为重要社会新闻,后者则可能根本无人知晓。媒体高度发达的上海与信息极不发达乃至为信息死角的乡村,其间的差异更大。这是集聚效应的另一种表现。
城乡贫困信息呈现的不均衡性,使得城市贫民问题往往会引起政府特别的重视。且以棚户区为例:贫民集聚的产物之一,是棚户区大量出现。这在晚清已经相当严重,到1930年,上海棚户已达3万户以上,遍布租界四周及浦东地区。此后,一·二八事变与八·一三事变的发生,更加重了这一问题。这些地方的卫生、治安、消防、犯罪问题,触目惊心。1928年5月3日、10月5日,浦东、闸北接连发生棚户区失火惨案,浦东焚毁草棚500多家,闸北焚毁190余家。两案促成上海市政府解决棚户区问题。上海专门组织了筹建平民住所委员会,至1931年先后建成全家庵路、斜土路、交通路三处平民住所。1935年,又成立平民福利事业管理委员会,综合解决贫民问题,先后建成中山路、其美路、普善路、大木桥路四处平民村。这些平民住所在抗战期间,历经兵燹摧毁,损失奇重。抗战胜利后,政府又派员接收、管理、修复。人们可以从各种角度批评那时的政府对于贫民问题解决得这也不是、那也不是,但要看到,同时期各地乡村的贫穷问题,不知道比这要严重多少倍!穷人不集聚,问题不凸显,就不会受到当局的特别重视,也就更加难以解决。所以,单从解决贫穷问题的角度来看,贫民集聚也有其正面价值。
贫民生活在上海,尽管很多方面不如人意,但是,这个城市的一些综合型设施与优势,还是可以让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沾其余溉的。以对传染病的预防与救治能力为例,民国时期,大城市的能力强于小城市,小城市的能力强于乡村。在上海、南京、北平这些大城市,由于自来水厂的设立、饮用水的安全、城市排污系统的建设等,由于卫生防疫措施的制定实施和保健工作的推行,天花、痢疾、伤寒、肺病、霍乱等传染病已经得到有效的控制,但在同时期的乡村,这些设施、措施仍然缺少,这些疾病依然是农村人口死亡的最重要原因。
再退一万步说,集聚在上海的穷人,即使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比起乡村来,上海有钱人多,慈善机构多,好心人多,新闻媒体多,对于穷人的发现与救济也比乡村要好得多。哪怕死在上海,也还会有同乡组织或其他慈善机构帮其入殓安葬,而在乡村,则可能连这点死后待遇也没有。这是上海贫民,宁愿在上海受苦受穷,也不愿意返回家乡的根本原因。
追根溯源,近代中国城市贫民不断增多,在于农村破产,农民被抛出乡村,而农村破产,在于帝国主义军事侵略与经济掠夺;在于军阀混战,社会动荡,灾害频仍,民不聊生;在于中国生产力低下,政治腐败,在全球性竞争中处于劣势。换句话说,考察近代中国城市贫民问题,必须要从中国、世界两个更高的系统中去考察,要从城乡联系、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中去考察,而不能孤立地、静止地只看城市。
综上所述,尽管也有人是到上海以后才由富变贫的,但从总体上说,城市的贫民主体部分是从乡村迁移而来的,是先贫而后入城,而非入城以后变贫。乡民进入上海以后,相当部分变成了产业工人、商店职员、家庭服务人员与劳工,也有人成了无业者、流浪汉。在城市社会中,产业工人为比较贫困阶层,人力车夫、码头工人等劳工为非常贫困阶层,无业者、流浪汉为极端贫困阶层。产业工人、商店职员、家庭服务人员的经济收入与社会地位,较之他们此前在乡村,都有所提升。劳工与流浪汉,生活虽然极端困窘,但较之完全破产之农民,处境依然有所改善。产业工人正因为其有较之破产农民尚可维持的处境,在城市中所处的并非社会最底层的地位,所以,他们不可能不顾一切地投身由“左”倾教条主义者发起的工人运动。产业集聚、人口集聚与财富集聚的叠合,刺激了社会分工,促进新的行业发展,凸显了贫民群体的存在,提升了贫民个人的素质,强化了贫民群体与其他个人、团体对话竞争的力量,也有利于引起政府对贫民问题的重视与解决。
近代贫民在上海的高度集聚,为贫民群体向上移动提供了营养与动力,提升了贫民群体抵抗风险、应对灾难的能力,增强了这一群体在上海生存的耐力。美国学者格莱泽所著《城市的胜利》,讲印度、拉美国家大城市贫民窟问题,认为不是城市让人们变得贫困,只是城市吸引了贫困人口;贫民问题从根本上说是乡村破产的缘故,是整个社会的问题;大城市贫民窟的出现,说明城市对这些人的吸引力。这一结论,对于我们分析近代上海城市贫民问题很有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