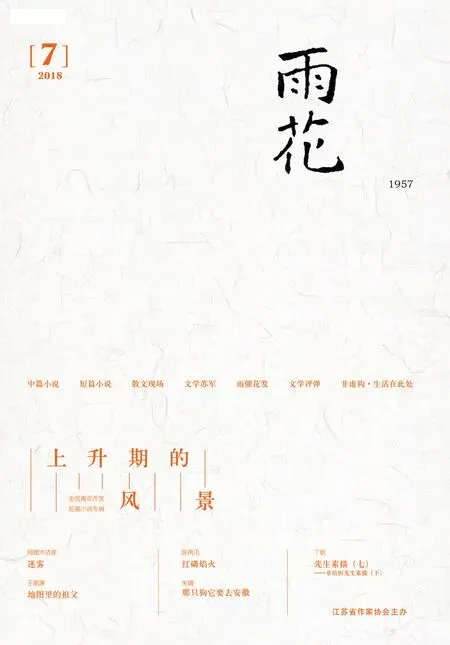流动的盛宴
赵志明
喜不足喜,哪怕到处张贴了喷红吐艳的双喜。
悲不胜悲,天意纵然不许,人间也尽是白头。
这是老张和小李恪守的人生信条,虽然他们一老一少,中间隔了二十多岁,而这二十多年的丘壑又显然并非一代人的经历所能填满。
他们的第一次见面,是在一次八音乍起的丧席上,俗称“吃豆腐饭”。
老张清楚地记得,吃到最后,小李在众目睽睽下,用几张餐巾纸把一只汤碗擦得干干净净,摁到了怀里,随即扬长而去。老张差点喊出“抓偷碗贼”来,不过是为着避免暴露自己,方才恨恨作罢,但也因此对小李印象深刻。
紧接着却是在一场喧闹骚动的婚宴上他们再一次遇到,端坐人群中的老张不免多看了小李几眼。老张以为小李是男方那头的小哥们,小李则以为老张是女方那头的远房亲,两个人各怀鬼胎,藏形匿迹,只顾埋头一通进食。事实是他们和哪一方都没有关系,好比骆驼翻跟头,两头都不着靠,不仅如此,他们与婚宴中的所有人此前也从来都没有见过哪怕一面。这种情形下,见过倒是要坏事。
这两个人虽然互不相识,但照此态势发展下去,势必低头不见抬头见,老张和小李想要继续装作陌路人断无可能。
接连几次在不同的宴席上不期而遇,主家和宾客们倒是换了一批又一批,独他们两个雷打不动。
一个人有这么多亲戚并不奇怪,可怕的是这些亲戚彼此之间竟然没有一个是交叉合集的,岂不是咄咄怪事?老张和小李自此也就心照不宣,知道彼此实属志同道合,都是来蹭席的,如果有人贸然问起,他们自然备有锦囊妙计,端的是随机应变,得心应手地任意高攀援低俯就,不是新郎的贵亲,就是新娘的宝眷,或者死皮赖脸地和死者称兄道弟,反正是死无对证。更何况,皇帝免不了有几个穿开裆裤辰光的朋友,落水狗也曾经呼朋引伴一起抢啃骨头,总之可以找到八竿子打得着的关系,落实那可有可无的亲眷,但绝对不会无缘无故出现在这样的场合。
这种游戏随时可能会露馅,好在各路神仙和菩萨齐飒飒保佑,一直没有穿帮过,但意外随时会降临。为了对付这种意外,老张在上衣内袋里掖有薄如蝉翼的份子钱,虽然从未掏出过,但是让他倍觉欣慰。小李从不额外准备礼金,他觉得多此一举,如果花钱就没有必要来这里吃饭,而是特地准备了一双跑鞋。小李脚踏一双轻便合脚的运动鞋,如同祥云,随时可以离席开溜,跑起来像风一样。
如此一来二去,三番四次,老张和小李不出意外地走得近了,有时像父子,有时像翁婿,有时像师徒,有时像朋友,有时像同事。在他们身上两个年龄相隔两轮上下的男子之间的社会关系,很快差不多就穷尽了。他们福至心灵,觉得既然双方不存在竞争和敌对关系,那就一定可以通力合作,互相有个照应。
第一次联手难免做了趟夹生饭老张和小李不仅要尽量提防被对方占口头上的便宜,也容易露出马脚让酒席上其他过来搭话的人心生疑惑,可对方毕竟心思不在这里,更不会打破砂锅问到底,到底是虚惊一场。
几场虚惊过后,无论是老张还是小李,再次对演起来就很顺手,可能他们发现彼此有空子可钻倒不失为一种打趣,即使事后得了便宜还卖乖的一方,会像炒豆子一样反复提及旧事只要不伤筋动骨,也就无伤大雅。
比如说,他们扮演翁婿,老张自然演丈人,即使老张真有和小李年龄相仿的闺女,也不觉得小李就此真的和自己的女儿有什么关系。反过来也一样,他们假装是父子,老张开始还有点飘飘然,自问这个父亲当的还算可以,小李简单一句“我的父亲早就化为一堆黄土了”,老张犹如被一盆凉水从头浇到脚,顿时自得之色全无反而觉得愧疚,虽然小李完全是一副无所谓的态度。
也因此,从一开始他们就为这种交往定下了基调,那就是可以挖空心思尽情奚落嘲讽对方,但同时也要十分清楚这种行为完全不起作用,毫无必要,也就没有意义。
有时他们自己都不觉得是在演戏,甚至巴不得会有人过来同他们聊天,最好险象环生,最后化险为夷,这样全程紧捏着一把汗,倒可以大大增加茶余饭后的谈资。不是说蹭吃蹭喝没有意思,不然他们怎么会像上瘾一样孜孜以求呢,而是这种意思显然越来越不那么大,需要辅佐其他的一些刺激,否则就会真的没有一点意思了。
通常情况下,老张和小李会结伴出现,缩缩刺刺,唯唯诺诺,找外围一张不起眼的桌子坐下。老张会对小李说:“我看这张桌子还空一点,我们就坐在这里吧。”大喇喇坐下,抢在同桌其他人脸呈疑惑费劲思索之前,小李表现得自来熟,拿起桌上的烟盒,撕开,挨个敬烟,动作一气呵成,一副舍我其谁的架势。抽烟的空当,小李不动声色甚至有些无礼地但完全是随机地审问其中一个人:“你是哪头的亲戚?我怎么不认识你?”老张就会瞬间热情高涨,拦住小李的话头,“你这个小同志,这样说可有点见外了。既然坐了同一张桌子吃饭,我们就都是亲戚了。两家亲不如一家亲。大家说是不是?”于是就热闹起来,但凡桌上有抽烟喝酒的人,一准就像失散多年的亲人重新聚首,或者是像刚做成亲眷关系的人那般假装客套。
选择外围的桌子也有说法。靠里的重要的桌次,往往安排重要的关系更近的人,基本上是一桌一家人,团团坐定,不仅同桌的人眼里揉不进沙子,主家对入席的人也很熟络,断断不可能叫不上名字,更别说是插进来一张生面孔。在安排座席时被边缘化的基本上是远亲。双方本来走动得就不亲热,仅限于红白喜事才会往来,本着一碗水要端平的原则,一方不能不请,一方不能不来,终究是带着些别扭,有几分胀气,容易让老张和小李这样的人钻空子,浑水摸鱼。坐远了还有一层好处,主家即使敬酒敬到这边边上,有可能只是装装样子走走过场,自然是一绕而过;即使真情实意要劝酒,也基本喝到数了,这时候滥竽充数的李鬼和难得冒出来的李逵,在主家眼里又能有什么区别?
细说起来,老张和小李留给彼此最初的或者说最根深蒂固的印象,倒证明了两个人确实是一路货色。
对小李来说,第一次见到老张那会儿的印象已经不深,但正因为印象迷糊,彼时的老张就很像死者从镜框里直直走出来,浮坐在板凳上一言不发,愁眉苦脸地俯瞰着一桌菜,显得毫无胃口。老张的弯钩鼻和虚眼泡让其面目如同鹰隼,也充分证明了他这么多年的死人饭毕竟没有白吃,老张这副尊容“即使烧成灰我也能认出来”。
老张则对小李私拿汤碗的细节始终无法释怀,一直苦苦地追问。小李一直打过门,吊足老张的胃口之后才告知实情。原来吃豆腐饭时取走一只小碗在乡下再正常不过,主家不仅不会阻拦,反而会求之不得。小李交代完不忘尖酸刻薄一下,认为老张这个城里人什么都不懂,简直白活了。老张无言以对,谁让他对自己的过往讳莫如深只字不提呢。
受小李如此挤对,老张对小李自然也没有好话。年轻力壮的小李在老张看来就像一只硕鼠,肥得不得了,胆子也壮,不怕人,更不怕生人。这显然是有原因的,比如说小李的脸是典型的腰子脸,两副腰子合在一起,“这个长相基本上也是到头了”。脖子上顶着腰子的小李,走到哪里遇到什么都容易激动得满脸通红,在婚宴上更是完全坐不住,恨不能像戏文里的王老虎一样抢走新娘,自己取而代之当新郎,那可真是风流快活得紧。小李不折不扣就是一具行走的精子盛器,随时都可能精满而溢。
总之,老张和小李,孟不离焦焦不离孟,组成了一对到处蹭宴席的饭搭子。熟归熟,吃饭归吃饭,他们却秉守着这样的原则,那就是坚决不会出现到对方的现实生活中。他们当然是朋友,甚至算得上是忘年交,但这是怎样的朋友和忘年交啊:不管小李如何旁敲侧击,老张对他的过去始终守口如瓶;不管老张如何循循善诱,小李就是绝口不提他的未来打算。
当两个人出现在同一个宴席中,他们就像是一个人,小李指向的是过去的经历,童年、少年和青年倏忽而逝的时光,老张则以“活着”具体而生动地诠释着他步入中年及至老年的每一天。也许,老张和小李在宴席上的相遇、相识,进而联袂追逐更迭的喜宴丧席,这显然不是没有原因的。老张习惯于在过去面前装聋作哑,小李则装作对未来丝毫提不起兴致。他们两个人就像是搭扣,是过去和未来的衔接段,也是犹疑的,不确定的,虚无的浑身上下闪耀着“既然如此”“那就这样吧”的动人光辉。
但这些早已经是十多年前的往事。十多年前,大概是2000年左右又是千禧年来袭,又是世纪之交,又是十年流转,在当年遥想起来动人心魄,在回忆中其实也稀松平常。老张和小李并没有被千禧年来临烧坏脑子,而是相当冷静地互留了手机号相约“千年等一回”,以后一定随时联系,以便共同赴宴。
那可真是好日子,在大街小巷随便转转,就能撞上开张的流水席桌子从街头一路排到了巷尾。有时左手是婚宴,右手便是丧席。左手在为两个人的结合张灯结彩,右手在为一个人的远行吹吹打打,而跳到半空中的鞭炮声,因为眼界开阔竟然从互不相让,争风吃醋,最终变成了难分彼此,融为一体。如此盛景,让老张和小李摩拳擦掌,既兴奋又沮丧,因为他们无法吃完这家再去吃那家,即使能把脸皮厚上三分,肚皮也不能撑得再薄一层了他们很希望一家家吃过来,再一家家吃过去,不能厚此薄彼,必须一视同仁。他们只能感叹:为什么不能早几天入洞房或者晚几天走呢?他们吃得满嘴流油,塞得肚满肠肥几乎抬不起腿走不动路,必须要扶着腰就近找个地方坐着歇上一会儿才能步履蹒跚地回家去,为下一次的盛宴养精蓄锐。
在无聊消食的工夫,他们会用牙签剔着牙,或者嘴上叼根烟,漫无边界地扯闲天,说的最多的是那篇《齐人有一妻一妾》。
“齐人有一妻一妾。其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后反。其妻问所与饮食者,则尽富贵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后反;问其与饮食者,尽富贵也,而未尝有显者来,吾将瞯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从良人之所之,遍国中无与立谈者。卒之东郭墦间,之祭者,乞其余;不足,又顾而之他——此其为餍足之道也。其妻归,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终身也,今若此!——’与其妾讪其良人,而相泣于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从外来,骄其妻妾。”
如果蹭席算是一个行当的话,那么这个齐人显然是当之无愧的祖师爷。老张力主每次蹭席之前应该祭拜一下齐人,烧两把香,或者望空祷告一番。小李认为大可不必,一旦这样做了,就是越过千年向祖师爷行贿,也就等同于花钱吃饭,蹭席云云,自然难以成立。话题很快扯到老张身上,小李觉得老张要是生活在齐人那个时代,其嘴脸可能比齐人更无耻,进而又断定以老张的年龄,必然也享有齐人之福,至少有一个妻子和一个情妇。老张马上矢口否认。在这个问题上他的寸步不让,反而让小李变本加厉,替老张幻想出好几任老婆,好多个姘头。老张避开话题,反击嘲讽像小李这样的种马才会需要和驾驭如此多的女人。小李是精满则溢。老张不失时机地盖棺定论。
但好日子很快就到头了。即使老张真能化身为一头鹰隼,飞在城市的上空巡视,小李缩成一团如老鼠,在地面的各个角落穿梭,竟然很难发现盛宴的痕迹了。他们为此真是想破了脑袋,觉得高楼取代平房很可能是造成宴席从他们眼前和身边消失的重要原因。在平房时代,即使在城市里,每家每户差不多都有院子,更不用说在乡村。无论白红喜事,主家都会在家里摆宴席,家里搁不下几张桌子,就绵延到院子里,院子也不够用,还有房前屋后,还有马路牙子,不管来多少亲戚,要借多少张桌子,地方大着呢,可以不断地延展出去。高楼大厦时代就不行了,一幢楼即使只修七层高,里面住了很多户人家,家里那么小的面积,肯定是办不了酒席的,也没法在楼下空地上搭棚子占用公共空间,只能让酒店饭店承办各式酒席,而去这样的地方蹭席对老张和小李都是巨大的挑战。特别是城市禁止大鸣大放后,他们再也无法在半空中和地面上找到盛宴的蛛丝马迹了。他们走街串巷,也能看到婚车的队列,缓慢驶进一个小区,停在一幢楼前,不过是接上新娘或者是把新娘送入新房,不到半个小时,车队就会开往另外一个地方,那里宾客们济济一堂,只待一对新人入席,然后开怀畅饮,再陆陆续续散尽。丧事也一样。在殡仪馆举行告别仪式,随即火化下葬,不待尘埃落定,死者的亲属们就会聚集到另一个地方吃饭。
完全没有家的感觉,悲喜也像染上了这个时代的浮躁,变得浅了,淡了。喜不是喜,悲也不是悲。老张和小李,谁知道呢?也许他们一个是鳏夫一个是孤儿,一个生无可恋,一个未来不期,都是过一天算一天。他们在街头巷尾追逐流动的盛宴,不过是想以一个陌生人的身份夹坐在诸多亲友之间,感受家的氛围,在悲欣交集中体验或悲或喜。
所以,这差不多是故事的终结了。老张和小李苦于找不到往日熟悉的宴席,彼时它们或红或白,铺展盛开在大地的平面上,具体得就像脚印,轻盈得如同吐气,两个人垂头丧气,一时不知所往。猛然间,就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一个酒楼的外显电子屏上闪过如此熟悉的信息,某某和某某喜结连理。几行字循环播出,这差不多就是全部的过程、意义和祝福了。不知道为什么,盛宴在几步外触手可及,他们却突然失去了兴致。他们很难想象自己坐在其中狼吞虎咽。太不应景太可笑,太没有意思了。仰望眼前高耸入云的华厦,它就像一座通天塔把天底下所有的宴席都吸纳了进来宛如在向云端上献祭。
老张和小李既像喃喃自语,又像在万分不舍地作别。“那么,好吧我们也走吧。”“再见了,老张。”“再见了,小李。”再见即不再见。但也可能,他们相对的背影隐含如下信息
“老张,你什么时候死,务必记得通知我,我一定会去吃你的豆腐饭并且还要当着你的面,再一次堂而皇之地顺走一只碗。”
“小李,你什么时候结婚?你这家伙,不会因为怕我去蹭席,就要一直拖到我驾鹤西去才肯动结婚的念头吧?我兜里准备多年的那封份子钱在我死之前总得给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