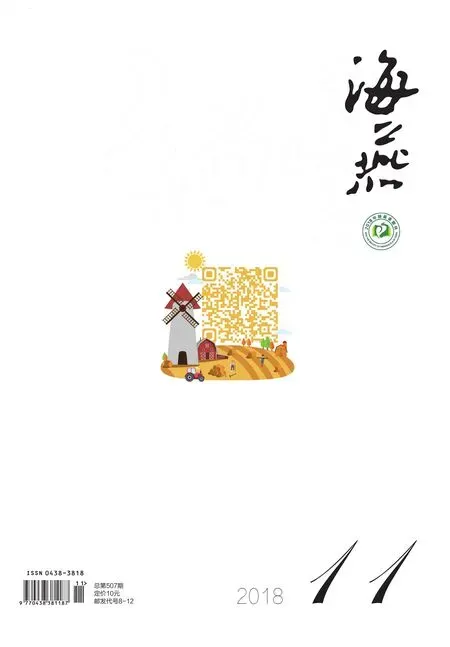在日常孤独里耸起“骄傲”气质
——读微雨含烟组诗《在低处》
□宁珍志
前两年在评述辽宁诗歌创作态势时,我对微雨含烟的诗有过印记:“于琐碎的物质生活河流中构建精神骨架,以支撑我们不断被时间侵蚀或者吞噬的思想与信念。生活与诗歌一样,都需要意外,意外的幸福,意外的感受……但意外终究替代不了个人秘密,秘密的潜流永远是内心的姿态。诗人清醒的词语亮相,组合成了清癯的生命理想。”她的诗“创作充满了‘双面性’,写亲情、写景物,写自己的‘近距离’,往往‘从个别到一般’,进而抽象出人与事的生命本质;写情绪、写状态,写自己的‘意识流’,又往往‘从一般到个别’,把知性、陌生的精神流向具象化。”现在读微雨含烟近期组诗《在低处》八首,是久违情思的再度照面,其中有《一条身首异处的鱼》,看着,看着,不由想起波兰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女诗人维斯拉瓦·辛波斯卡的《自我分割》一诗,选录如下:
遇到危险时海参会把自己分成两半:
一半给世界吃掉,
一半逃跑。
它决绝地把自己切割成灾难与救赎
罚金和奖品,过去及未来。
在海参身体的中间展开了一个深渊,
也立刻出现了两个彼此陌生的边缘。
在一个边缘上有死亡,另一个有生命
一边是绝望,另一边是抚慰。
……
该死几次就几次,但不要过头。
幸存的那部分,也可以在需要的范围内再生。
我们会自我分割,喔没错,我们也是。
只是我们把自己分成身体和破碎的低语。
身体和诗。
一边是喉咙,一边是轻盈,
很快就沉默的笑声。
……
深渊没有把我们分开。
深渊将我们包围。
这是辛波斯卡为纪念波兰另一位诗人朋友波许娃托斯卡所写,之所以几乎全文引用,是她写得深刻广阔,不舍得简略。辛波斯卡不仅言说了诗人与世界的矛盾,也犀利地指出诗人自身的多相矛盾,以及诗人在现实面临的宿命境地。诗人或诗人的诗,真的是深渊两边的绝望与抚慰、死亡与生命、罚金与奖品,“一半给世界吃掉,/一半逃跑。”因为海参、蚯蚓等生物有着超常的“自我分割”的再生能力,扔下一半死亡,留下一半活着。辛波斯卡的暗喻方向当然是人类,在遇到危险时能够自我保护,哪怕是出于本能,脱离险境,侥幸便是生存,不幸便是死亡。不过,人类不可能像动物那样可以把身体和身体的一部分切割,而是要把身体和灵魂、思想分开;身体与灵魂的分开就不像身体与身体的分开那般整齐彻底,干净利落,总会有一些高贵带上庸俗,总会有一些悲壮带上滑稽,总会有一些忧郁带上玩笑,总会有一些严肃带上无厘头。反过来也一样,现实中至纯至净的人类感情难以存活。辛波斯卡的诗,我们感受到的即是世界的惊异险峻之处,生活的苦难、人类的尊严和内在的羁绊束缚抑或自我修复整合的坚韧与真诚——这是辛波斯卡“全球视野”有关人的庞杂、复合性的考量。
诗歌创作说到底,会依据诗人的不同而呈现出丰富与多元性,人与世界在每位诗人的成像面前是不尽一致的,一方面出于诗人自身的文化背景、历史重心、现实位置不同,一方面则因诗人所处时代、出发点位不同,哪怕是面对同一类题材,当然还有技术性操作手段之误差。有的从自然出发,有的从人出发,有的从历史出发,有的从现实出发,有的从爱情出发,有的从身体出发……即便终极关怀人类,也可唱出一己衷情:“今夜我只有美丽的戈壁空空/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海子《日记》)与辛波斯卡相比,微雨含烟的诗可能在一个单元或一个小节甚至在某些情感片段上契合了大师的心灵定位抑或生命悲剧意识,她不过是缩小了场景与景深,在“小剧场”演出,日常、家庭化了而已。或者,日常厨房的普通一个“杀鱼”场面,被作者“特写”,成为怜悯同情生命本体、观照自我灵魂走势的导体。同时,《一条身首异处的鱼》(这条鱼应该是清河水库的鲢鱼)的喻体本身与海参相比,没有“自我分割”能力,被“拦腰斩断”后,几分钟之后即是死亡,两个“一半”便成为婆婆、父亲和“我”的“试心石”。诗的第一小节“敬畏”是虚,惊诧为实:“身材矮小的婆婆”斩断“十斤重的鲢鱼”,一半留给自家,一半送给“信佛,不杀生”的父亲。“面对那半条鱼的表情”,父亲“那般无奈和自责”,“像秋天的树干对即将落下去的叶子们”。此时此刻,这半条鱼“呼唤着另一半”,成为尸体的“另一个自己”,“我”恍然着,忏悔着,“悲秋”惊现。恬淡从容的叙述笔调与若有若无的生活情节,把“杀戮”之后的几个灵魂造影呈现得司空见惯,言外之意更令生命健全者警醒:刀锋不能随意指向弱小者,尤其不能对无辜者滥开杀戒——鱼在诗人笔下是人。如同史蒂文斯所说,诗歌的高贵就在于它“是一种内在的暴力,为我们防御外在的暴力”,也是希尼言及的“想象力在反抗现实的压力”。
微雨含烟于不经意间就完成了对生命姿态的把握以及对整个事相的知性命名,《在低处》这组诗选取的几乎全都是日常生活的点面,极其普通、随意,自然的,季节的,人间的,亲情的……俯拾皆是,甚至小到可有可无。低处的叶子跟风飘舞,母亲最后离别的两行眼泪,路上袋子里的三只桃子,旅游穿过那片竹林,站在秋天,在冬天里行走,在寺庙听人说手相……任何人都可以经历的事情,平凡得不能再平凡。微雨含烟就是要从这熟悉的“脸面”中再造“陌生”,彰显出语言意象的“内在暴力”。早在爱伦·坡时代,他在《创作哲学》里就讲过:“艺术作品永远都需要两种东西:一是得有点儿复杂性,或更准确地说是适应性;二是得有点儿暗示性,或曰潜台词,不管其含义多么不确定。”微雨含烟的诗,从简单简约的生活画面中,释放出语言暗示的多重意义以及“纵容”其意象蕴含的生命适应性。《在低处》的叶子们飞舞,不再与树重合——生命的一种背离现象;人与自然不同,试图离地面高一些、离光线近一些,人之常态——生命的趋光现象;一旦走进墓园,叶子、柳絮和花圈上撒落的“纸蝴蝶”雷同,一生如此——生命的必然归宿;人类不可能越过死亡线,结局会同落叶纸花一样,亲手点燃它们即是眼见肉体逝去——生命的顿悟清醒。《在低处》也许远不止这四重意义,道家哲学,尼采、叔本华思想的点滴都隐含其中,诗人只是把它们“含混”在一起,表达了自己释然理智的世界观。像《挽歌》母亲的泪眼如同镜子般照射“我”的羞愧,像《三只桃子》两个回到故乡一个在内心生根,像《穿过那片竹林》踩在“影子”上面——“那在光照中存在的/不可握住的部分”,像《站在秋天里的人》“能低头的人有很多”,像《在冬天里行走》风带着我们行走是一种负担,像《在寺庙听人说手相》的将信将疑欲说还休……微雨含烟不露声色,坦然描摹人间的自然生态,成为生命活体的情绪、心理、感知、经验,包括灵魂前行的犹疑、负重、磨难,成为女性视角内的精神财产和文化景观。
现代汉语诗歌发展到今天,全天候的抒情笔调早已隐匿或摇身几变,成为生活化的口语,成为日常化的叙述,成为外在言语递进与内在情感爆发的双向节奏同步发展,从而更接近于人与物的内在真实。而这种本真的叙述行为在微雨含烟的诗作中可以得到见证。诗人冷眼看待周围,但绝不缺少捕捉的热情;诗人“零度”叙述,但绝不弱化内心的动能。正是在这冷眼热情、“零度”动能的逆向体察中,微雨含烟才获得了内心还原客体的机缘,获得了直觉生长出理智的自然,而在字里行间闪烁出宝贵的思想火花与现实情怀,人性之美之璨之飘摇的现场感与读者的阅读情趣一一衔接汇合。“诗的本质不过是,也仅仅是人类对一种最高的美的向往,这种本质表现在热情之中,表现在对灵魂的占据之中,这种热情是完全独立于激情的,是一种心灵的迷醉,也是完全独立于真实的,是理性的材料。”(波德莱尔《浪漫派的艺术》)微雨含烟常常把这种热情稀释、化解,变作自己冷静沉着的叙述语言,而她的感觉也掩映在一副理性内敛的面孔之下。“当我抱着她的身体/当我抱着蜷在盒子里她的/没有烧碎的腿骨/她是安静的,轻的(《挽歌》)。”诗中的“安静的,轻的”其实也是诗人自己当时的泰然举止写照,而在文字背后,是隐匿着女儿失去母亲的巨大悲痛,“轻”恰恰是思念之重的反衬,“安静的”恰恰是“我”羞愧、憎恨的百感交集、一味纠缠的反衬。“风声经过沉甸甸的果实/我们想起关于果实的托付/于是站在果园里,面对打了农药的李子/远远地对它的外形加以描述”(《站在秋天的人》)。文字叙述没有任何表情,客观而镇定,可内心荡漾的波澜还是能够通过意象的边缘、缝隙渗透出来,水果蔬菜的绿色、环保已经是整个人类共识,真相却是农药对于水果就同日常饮用水,屡禁难止,直接危害到人民群众生命健康。诗人目击到了只能对外形加以描述,果实“内核”已被污染,结尾处潜台词含量尤其大,物质化的市场经济早已把一个正常社会的良知吞噬得所剩无几,我们无力目测内心,只好感知外形。“我认为身材矮小的婆婆/是个没有大力气的女人/当她把一条十斤重的鲢鱼,拦腰斩断/我忽然对这个小小身材/有了敬畏之心”(《一条身首异处的鱼》)。作为首节,微雨含烟开门见山就设置了多向度内涵,不乏下意识潜意识,因为她把“婆婆”当作了“操刀者”,若换作父母亲,她或许会有另套语言系统。当然,作品与生活是两码事,尤其是诗,细节往往是想象力的花朵,在言语的绿叶中画龙点睛。关键点是,小小身材的长辈能把十多斤的鲢鱼拦腰斩断,有时和力气有关,有时与人性中的“杀气”——暴戾、残忍的一面突现,哪怕为一饱口福。人性优劣不可貌相,诗人复指,“婆婆”是一类人,是一类表里很难划一的社会形态。
微雨含烟的诗歌创作有着自己的表达习惯、结构风范,包括题材,包括视野,包括语言,包括意象,包括叙述方式,包括细节构成……我不太喜欢说风格,就像上面列举之后再一一例举,风格还是觉得外在、表象,似乎让人一眼便能觉察到底。我想说气质,这是由内而外发散的灵魂味道、精神气象,需要时间打造,需要信念完成。具体到微雨含烟,即是她的诗正在以自己的气质而存在、活跃于汉语诗歌界。瓦莱里说:“爱、憎、欲望是思想的光明,而骄傲是其中最纯粹的一道亮光。它向人们照亮了他们要做的事情中最困难的和最美的。它将偏狭燃尽并使人本身变得简单。它让人们脱离虚荣,因为骄傲之于虚荣正如信念之于迷信。骄傲越纯粹,它在心灵中就越强大和越孤独,作品也就越经过深思熟虑和反复推敲,就会不断被放到永不熄灭的欲望之火中千锤百炼。”(《文艺杂谈》)细读这组《在低处》,或者说统观诗人业已发表的作品,包括她参加诗刊社“青春诗会”出版的诗集《回旋》,稍加思索,便会感到,的确有“骄傲”或者“傲气”从她的诗中弥漫而来。诚然,此处的“骄傲”绝非微雨含烟以为自己的诗写得好,思维、表现方式先进,并为自己近年某些进步沾沾自喜,小瞧他人,不思进取,自满于当下状态。微雨含烟的“骄傲”,是自己的一份执着、坚定、“改变”,她不希望自己的创作几十年“一贯制”,把女性的所谓爱情“专利”进行到底——与绵软不已的爱情题材签署终身合同,像川剧变脸似的一个身躯一个招式只是改换几副脸面,像厨房自来水龙头似的终日流着相同的水……
微雨含烟想从口语和书面语结合而来发挥出一套语言,和颜悦色娓娓说出,说出俗世中的高贵,说出细小中的伟大,说出家庭里的悲喜,说出大街上的眷恋;微雨含烟想从普通的日常截取诗歌断面,随手建立意象群体,不想惊天地泣鬼神,在人海里捡拾紫贝壳,在亲情里磨砺撒手锏,在沙硕里集聚金蔷薇,在自然中铸制聚宝盆……今后的时日,诗歌的生命取向毕竟还是源于大多数的人类日常。“我们探讨迟钝与敏感的话题/以及一个事物的两面”(《站在秋天里的人》),微雨含烟自信地“骄傲”着;“流泪的眼睛,让活着的我生出一丝羞愧/我有什么理由憎恨莫须有的虚无”(《挽歌》),微雨含烟执拗地“骄傲”着;“人群中的英雄,掩藏着标识/所有人都是自己的救赎”(《穿过那片树林》),微雨含烟清晰地“骄傲”着;“或者找个理由见一见/人群中不被发现的另一个自己”(《三只桃子》),微雨含烟孤独地“骄傲”着……骄傲在此是诗歌字词句章的生命态度,是人的理智情感的命运钦定,是诗人自己信心满满的一条路径——气质活现,必有代价,必有付出,必有毅然决然的性情不悔。所以,一旦“骄傲”,大多数会是“孤独者”,而在孤独中涌现出来的气质,更为可靠些,有利于诗歌的独立想象与陌生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