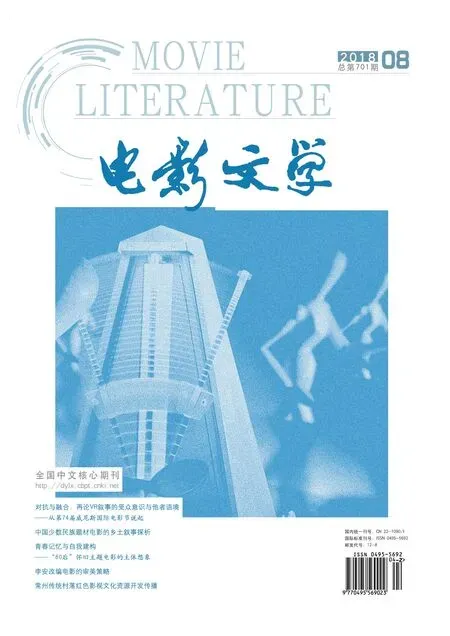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乡土叙事探析
韦惠文
(广西民族大学,广西 南宁 530006)
中国电影在少数民族题材的呈现上一直处于探索和发展阶段。自《芦笙恋歌》《刘三姐》《五朵金花》《阿诗玛》等经典作品推出以来,少数民族独特的原生态生活不仅成为中国电影重要的素材来源,其民族文化资源和统一国家形象建构的政治意义也在这样的良性展现中日益凸显出类型化趋势。可以说,从文化人类学的视域而言,少数民族题材影片是实现电影市场化和民族主体意识融合的范例,是创设现代化的民族新文化的重要推力。
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其实质归属于社会文化学意义上的“民族学”范畴,这样的内涵决定了其叙事样式无疑是乡土的。某种程度上,诸如《达吉和她的父亲》《静静的嘛呢石》这些民族影像所指呈的乡土社会的生存空间与现实语境,毋庸置疑是其实践的立足点。这种与现代化相对的乡土叙事以一种非常情感化、经验性的形式弥漫在整体叙事之中,从而为大众提供了一种陌生化的审美趣味,提升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艺术魅力。
一、从中国边域的乡土镜像到民族精神的代言类型
按照人类学家费孝通的经典阐释,“乡土性”是中国在融入现代化前社会运行的逻辑和脉络。乡土世界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占据着“主流身份”,构成客观世界里有序的叙事系统。少数民族题材的电影,自“十七年”出现《农奴》《冰山上的来客》等经典作品奠定基本基调以来,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显然不只是实现形象化反映民俗文化的功能,更为重要的,是利用其影像文本的效用展示民族电影的记忆功用。体现在人物的塑造上,是几乎不约而同地对少数民族世界里乡土群生像采取一种真实的、眷念式的再现或记录。
表现之一,是其审美对象多是少数民族的乡土世界,电影镌刻和映照出前现代的乡土中国的少数民族族群真实的社会底色。优秀的少数民族电影,在叙事中涉及乡土书写时,往往都能够比较充分地呈现出少数民族族群/个体的精神追求和价值立场,深层次传达乡土社会中少数民族主体的灵魂诉求。藏族导演万玛才旦所执导的《静静的嘛呢石》,可说对这一点做出了生动的阐释。影片所有的场景都被安置在一个似乎与世隔绝、远离现代同时又不断有新奇事物涌进的西藏乡村,这里四面环山,风沙扑面,马匹、羊群、寺院、经幢、乡村老幼、新旧事物被实景展示并奇妙地组合为一帧帧熟悉而异样的画面,而其中的群生像又都充满了寓意色彩。爷爷、刻石人、师父、经师等显然是乡土西藏旧时痕迹的符号,他们在现代社会中面对逐渐改变的现实,那种留恋和转换、守望与蜕变跃然银幕之上;而带着新奇事物归来的大哥,努力学习汉语希望走出去的小弟,对当下生活选择逃离的不在场的刻石人的儿子,以及无视传统礼法醉酒的莽汉,显然又是新的生活方式的征象。可以说,这些寄托着精神的苦闷和思想超越并存的少数民族群生像,不啻为乡土时代的缩影。
表现之二,人物塑造渗透出为乡土铸魂的色彩。由于少数民族群体的异域色彩,加上其身处乡土闭塞地域的边缘身份,使得他们作为表现对象时往往都有着意识形态或文化领域中的陌生化审美色彩,甚至作为与现代性相对立的民族精神和时代坐标被展示。少数民族主题的电影,意图引领观众穿透乡土中国及其边缘地区的内核,触摸那里的人们自身的命运脉络。这是从到早期的《草原上的人们》《鄂尔多斯风暴》等到后来的《诺玛的十七岁》《红河》诸片一以贯之的叙事关注节点。陆川的《可可西里》可说是这种对于少数民族乡土世界加以变奏叙事的一个例证——虽然它后来引发的关注早已超出乡土叙事的范畴。这部片子借助巡山队员的悲壮故事,意图展示青海的高原地区别样的乡土世界:极高的海拔、荒蛮的沙漠、莽莽挺拔的林木、蔼蔼覆盖的冰雪、错落出现的牧民、隐秘窜行的盗猎分子、栖息漫走的羚羊,这种完全异样于内陆及现代社会的乡土风貌,给银幕前的观众带来了强烈的视觉冲击。传统乡土社会中人与天、人与地、人与厚土型的传统文化在探索人性和审视人本身的生存状态的叙事中,更加凸显了其神秘的文化形态。里面的人物诸如以队长日泰为代表的巡山队员们,让人们看到了现代人情冷漠社会久违的力量和阳刚、虔诚和朴实,他们作为少数民族乡土社会遗留的“类型代表”,用生命的全部诠释了信仰、信念所能达到的高度,揭示了民族精神的核心。
二、从寻求与现代契合的理想诉说到都市想象世界的改装建构
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曾精辟地指出,现代社会秩序犹如一架巨大的机器在运转,所有的话语表达都离不开“现代性伦理话语”的核心装置。考察以《猎场扎撒》《德拉姆》等代表的新时期以来少数民族题材影片其乡土叙事的价值标准和评价体系时,我们明显可以看出,其所呈现的世界是一种充满“现代性反思”的已逝或者逐渐远离的“生活世界”,是一种寻求传统精神和现代理念契合,并且充溢了都市想象后某种理想世界的建构。
一方面,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其表现对象、呈现事件尤其是时空定位颇具特殊意味。这里的世界图景,特别是异域乡土的意象,既是作为现实生活世界的主要组成部分出现的,也是作为现代反思性的评价标准来拟制的,是一种对于边缘的、传统的、底层的世界与现代文明社会契合的想象性诉求。新世纪之际出现的《寻找智美更登》就是这种意识的当下展现。影片围绕导演、摄影师、老板一行人进藏寻找智美更登演员的故事,全面展示了西藏未被现代文明所浸染的风土人情,和藏区关联的充满前现代乡土意味的寺院、城镇、村庄在寻找的途中被赋予了所表现情怀的历史纵深感和复杂性。可以说,这里的“寻找”是充满寓意的,而“蒙脸”女孩的所有行为显然也是乡土社会由闭塞走向开放所历经的精神洗礼和情感阵痛的表征叙写。与其说藏区乡土社会的宏大叙事为影片提供了驰骋的叙事空间和实践余地,不如说正是这种寻求与现代文明契合点的冲突、交流、融合陈述,构成了影片叙事的基础与线索。从文本的结构设置而言,乡土落后但纯朴有力的思想观念与先进但冷漠、工具理性的现代文明之间的融会,是贯穿始终的叙事思路,也是影片所着意展示的思想内涵,是对民族根性的一种思考。
另一方面,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乡土叙事往往有着真实与想象混杂的叙事特征,其对少数民族地区乡土世界的“想象”,是对现代都市人群想象中的乡土“神话”的迎合。某种意义上,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以想象的方式满足着现代都市大众对于异域世界、乡土社会的窥视欲望和猎奇心理,并在这样的想象中构建出一座契合都市群生主流愿望的庙宇,遮蔽了某些真实情况。这一点,在第五代导演代表人物田壮壮的《猎场扎撒》《德拉姆》等片中就有所显露。《猎场扎撒》以内蒙古图尔布山谷地区一带围猎活动展开叙事,表面上刚健、勇武的内蒙古传统文化基因得以展示,实际上的猎场扎撒不过是丛林法则的代名词,在刻意渲染草原牧民乡土文化与现代城市文明的根本差异的同时,实际上宣扬了残酷的生存环境造就必然的弱肉强食社会的思想倾向。巴雅斯古冷、旺森扎布的哥哥陶格涛、旺森扎布的老母亲、巴雅斯古冷的妻子格日乐等人物,也几乎是导演某个观念或者某个想象的概念性衍生品。这些作品所呈现的少数民族地区的乡土现实,不能说是严肃意义与真实意义上的当代事实,是不经意间被都市想象和期待所改写的产物,是在田园牧歌中对地域文化的过滤处理。此类倾向的作品,诸如《图雅的婚事》《花腰新娘》等,也受到了程度不等的指摘。
三、从家国情怀的叙事阐释到文化乡愁的情感寄寓
正如泽尔尼克所言,电影的演绎,其深层意义结构上必有其意识形态主张,电影是意识形态被构筑而成的一个可允许的叙述。也就是说,意识形态不是一组机械的推演式陈述,它应该被理解为一个复调的、衍生于整个叙事中的文本,简而言之,是一种讲述故事的方式。因此,毋庸回避,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乡土叙事,掌控并制约其视点,影响其叙述方式的深层意义系统,是家国情怀的话语设置和文化乡愁的寄托。
其一,民族大团结的主题在少数民族题材影片的乡土叙事中依然是“主旋律”表达。这些影片,其乡土叙事往往是一种工具性存在,美丽的乡村、神奇的文明、真挚的人情、淳朴的民风,都在这种大背景和话语基调中得以印证。这些影片所要发掘的“民族性”,所指的其实不只是局限在少数民族,更重要的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民族性”。因此,乡土叙事中隐藏的家国情怀也在若隐若现中时刻得以彰显。在经典影片《红河谷》中,西藏高原乡土社会的壮丽风光、民俗风情、神秘历史、悠远传统、独特文明几乎都是点缀性存在,而在这种特设的地域环境和民族场景中展开的民族史诗和家园情怀才是其真正的主题意图。影片的开头是宏大的场面铺排:浩浩荡荡的村民在黄河边上举行河神娶妻盛典,其中的一名少女即后来的主人公达娃在汹涌的黄河中落水,被冲向对岸的沙滩,而恰好被藏族老妈妈与她的儿子格桑所救……这样的叙事本身也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历经冲刷涤荡最后重生的一种喻义,家国情怀在这些影片中得到了深情的书写。
其二 ,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的乡土叙事,渗透着一股文化乡愁的审美寄托,那些硕果仅存的边缘地带的乡土中国,日益成为现代中国人情感上的精神家园。中国社会历来都是由乡土社会构成的,人们对土地、乡情有着强烈的依赖和情感。可以说,土地是中国乡土社会的根脉,也是生活其间的人们守望的对象,寄托着浓厚的生命希望和情感诉求,更是现代文明大众频频回首、深深眷念的情感慰藉和人性关怀寄寓所在。《季风中的马》一片中,虽然世代居住在城市外的牧民不得不面临“家园还是城市”的苦痛抉择,但是影片中刻意展露的城市的喧嚣杂乱、人情的淡然冷漠,更加凸显了少数民族族群在面对乡土文化存留时的守望之情,以及乡村精神生态的健康和美好,引发的是一个全球化席卷的时代民族性、全球性、本土化与现代化如何走向的思考。《静静的嘛呢石》中,高原上的村庄仿佛世外桃源一般屹立在雪山的怀抱之中,而影片的原生态纪实性风格有意地将这种乡土时代的人情与物美刻画得淋漓尽致,工业文明的威力在这些镜像中得到了情感和认同上的弱化,同时也全面展示了创作者的艺术理想和人生情怀。这些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在乡土叙事上的情感倾向,在近年来的影片,诸如《长调》《鲜花》《德拉姆》等片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彰显。
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因其表现对象的特殊性,其乡土叙事一直以来也是相伴而生,并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可以说,随着所谓现代性的降临,边缘地区的乡土风情也日益成为现代大众精神回眸的所在,具有精神契约一般的寓意。而少数民族电影的乡土叙事,正是对以这些地方为想象对象的吟唱,是忧郁与感伤、希冀和向往的表达,也显示出中国当代电影叙事多元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