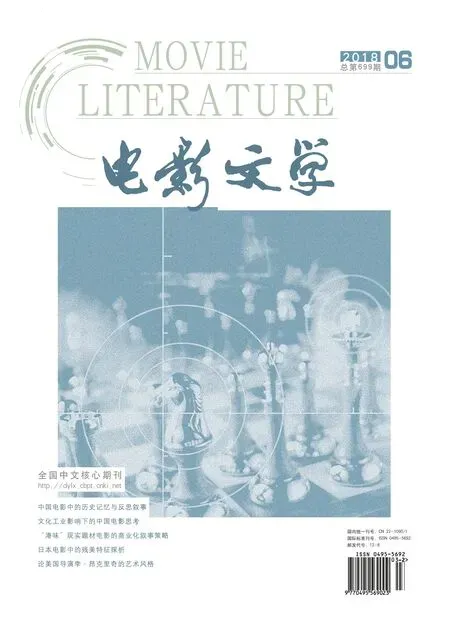《天才少女》的伦理叙事解读
胡艳娟
(内蒙古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内蒙古 包头 014010)
电影是反映社会生活与人类情感的艺术,人类的道德现象与伦理困惑当然也是电影中重要的社会内容。“‘伦理叙事’……是捕捉、分析伦理元素,即‘关于伦理的叙事’,是挖掘小说主题学的内在深层伦理核心。”马克·韦布的《天才少女》(Gifted
,2017)以一个温情的故事探讨了伦理秩序和伦理社会意识。一、具有复杂性和丰富性的教育伦理
社会教育伦理是应用伦理学的一个分支,对教育伦理的叙事性呈现则是伦理叙事的一部分。《天才少女》的叙事从玛丽第一天上霍华德学校开始,她在课堂上的过人表现也开启了全片的矛盾。可以说,教育伦理是《天才少女》的第一重伦理叙事。教育是人的基本权益,它关系着人发展中的可能性、可塑性。玛丽抵制走入学校,并非她厌倦教育,而是她更喜欢舅舅弗兰克给予她的教育。而弗兰克则明白,人的生长和发展是离不开教育和社会的,人要想实现自身的可能性,获得良好、主动的生命发展,必须有健康的社交关系。这也正是弗兰克和好心的邻居罗伯塔之间的区别。一贯宠爱玛丽的罗伯塔认为玛丽去到学校不会开心,因为她的智力水平远远高于同侪。而弗兰克则认为玛丽应该拥有正常的教育生活。正如罗伯特所预料的,学校中的种种令玛丽极为不适应,一方面是知识教授上,在玛丽已经学习了高等数学的时候,学校还在教授一年级的简单加减法运算;另一方面则是在纪律上,玛丽难以适应学校为了管理方便而设置的种种纪律,如说话前必须举手,每天必须和其他同学一起拖声拖气地对邦妮说“老师早上好”等。于是她在学校中处处表现得格格不入,如公然顶撞老师邦妮,当着校长的面让校长打电话给弗兰克接她回家等。在玛丽出手打伤一个12岁的男生后,学校提出将玛丽送到培养天才儿童的橡树教育中心。这遭到了弗兰克的拒绝。弗兰克作为玛丽的监护人,是最关注玛丽的基本生存处境的人,也处于教育伦理的旋涡中。弗兰克试图将问题解决于让玛丽受到普通教育生活这一范畴中。因此弗兰克告诉玛丽,她必须意识到,她必须去上学,正如自己尽管不喜欢修船的工作但还是必须每天上班。
事实上,弗兰克所采取的解决方式是来源于他的“个人经验”。即幼年时,他是家里被视作“普通儿童”培养起来的,姐姐戴安作为“天才儿童”在分去了大部分母亲的关爱以外,也替他承担了母亲给予的压力,即使是在日后弗兰克成为波士顿大学的哲学教授,他在母亲伊芙琳的眼中依然是一个庸庸碌碌的“虚弱者”,和他的父亲一样。在戴安自杀后,弗兰克显然不愿意再让玛丽成为第二个戴安,于是他希望给予玛丽的是作为普通人的生存际遇。而学校、伊芙琳甚至包括玛丽后来进入的寄养家庭,他们对玛丽的教育计划则出自“公共价值”,代表的是一种大众趣味,响应的是一种夹杂了名利的召唤。即当玛丽被确认为是一个天才儿童,尤其是一个千万分之一的天才之后,她就自动丧失了作为普通儿童的成长权力,她的潜能应该得到充分的发掘,从而对人类做出贡献。
整部电影的叙事主线便是一次又一次关于玛丽抚养权的法庭对峙。从双方律师的唇枪舌剑中,观众不难看出,电影是倾向于弗兰克一方的。但教育伦理的复杂性也意味着,问题绝不是非此即彼的。电影从多个侧面表现了弗兰克个人生活也存在诸多问题。他辞去教授职务搬家到海边选择成为一名修船工,这可以视作是他个人向普通人生活的积极靠拢。然而他经济困顿,无法满足给玛丽买钢琴的需求,无法建立起个人感情生活,以至于每周六都流连于酒吧,甚至曾经对一个醉鬼有过暴力行为等。也正是上述种种原因让法庭最终没有支持弗兰克继续抚养玛丽的主张。《天才少女》提出一个观点,即教育是存在悖论的,当当事人意识到何为最适合自己的受教育方式时,他们已经在他人给自己安排好的教育之路上走得太远。戴安的悲剧无疑已经证明伊芙琳的“囚禁式”教育方式是问题重重的,天才成为戴安沉重的负担和痛苦,她无法由衷地做一个儿童。然而如若戴安或玛丽被以弗兰克那样的,无视天分的方式培养长大,成为一个仅仅相对于旁人优秀一些的普通人,她们又有可能将后悔童年时个人的潜力没有得到应有的开发,没有在监护人给予的压力下得到高强度的训练以至于自己的“天才”被辜负了。这种矛盾反映了教育伦理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所在。
二、悖谬错乱的亲子伦理
电影在制造矛盾冲突上的叙事策略,便是展现一种悖谬、错乱的亲子伦理关系,弗兰克所要做的正是避免玛丽陷入这种伦理关系中,观众也自然而然在情节的推进中一直保持着对这一问题的高度关心。
在《天才少女》中,亲子伦理关系早已偏离了爱与抚养的正常轨道,呈现出一种令人触目惊心的变态。首先,随着邦妮的调查以及庭审的进行,六岁半就已经显示出过人智慧的玛丽的真实身世被揭开:弗兰克是玛丽的舅舅,而她的生母是著名的天才女数学家,被人们寄予厚望能证明一项世纪难题的戴安·艾德勒,而她的生父则从来没有承担过作为一个父亲的职责,甚至即使一直住在一个城市,这位父亲也从来没有上门看过玛丽一眼,不知道玛丽的中间名,他甚至没有上网搜索一下自己的女儿。而这一代的亲子伦理悲剧是由上一代亲子伦理的扭曲造成的。
出身英国的伊芙琳是一个严苛、有条不紊而难以取悦的母亲,她本人也极具数学天赋,但是在结婚生子后,她的科研事业遭受了一定影响,因此她将自己的希望寄托在了孩子身上。在发现女儿戴安是数学天才后,她对于戴安作为个体存在的价值就定位在了成为数学家上,甚至最后具体到了“证明纳维斯—托克方程”这一项事业上。从法庭双方的论辩来看,伊芙琳显然剥夺了戴安应有的社交,如从来没有参加过女童子军,17岁时喜欢邻家的男孩,和对方私奔到佛蒙特去滑雪,结果伊芙琳却控告对方绑架戴安,导致戴安一度尝试自杀等。面对弗兰克一方的律师询问伊芙琳是否知道戴安还有什么其他爱好时,伊芙琳坚定不移地声称戴安唯一的爱好就是数学。除此之外,在电影中出现的所有戴安的照片,无不都是短发形象,这暗示着伊芙琳对她的一种抹杀性别意识的控制。
在这样的成长过程中,很难想象戴安拥有怎样的孝亲情怀。一方面生父在自己不满十岁时去世,继父则为母亲看不起,父性崇拜对于戴安来说显然是不存在的;另一方面,母亲在某种程度上将自己当成了实现名利的工具,戴安所感受到的来自于母亲的爱和接纳是有条件的,即建立在自己是天才的基础上的,血缘亲情被一种畸形的管束进行了极端化的切割。也正是由于缺少了正常的社交教育,戴安未婚先孕。这种行为违背了一贯喜欢支配戴安的伊芙琳的意愿,于是伊芙琳放弃了戴安。戴安遭受了爱情和亲情的双重抛弃,留下了难以弥合的心灵创伤。出于一种绝望心态,她在自杀前带着女儿玛丽找到弟弟弗兰克,而弗兰克急于出门约会。弗兰克未曾想到回来时姐姐已自杀。杀死戴安的很大程度上便是伦理困境。
而单纯通过庭辩来让看似振振有词,实则理屈的伊芙琳暴露自己在母女关系上的残忍并非电影伦理叙事的全部。《天才少女》以“纳维斯—托克方程”问题的解决为这段悖谬亲子伦理画上了句号,也实现了叙事上的高潮。之前电影已经通过伊芙琳带玛丽参观学校时的介绍等铺垫介绍了“纳维斯—托克方程”,并借伊芙琳之口表示方程没有被证明非常遗憾,戴安已经非常接近证明了。然而在电影的最后,弗兰克将戴安遗留的手稿送给伊芙琳,原来戴安早已证明了“纳维斯—托克方程”,但是她提出一定要在“身后”发表,伊芙琳表示戴安已经去世多年,弗兰克则解释,是伊芙琳“身后”。这个遗嘱成为戴安报复自己母亲的一种方式。她到死也不愿意让伊芙琳完成自己的梦想,即看到女儿发表这个惊天动地的声明。而这种报复无疑也是极为可悲的。伊芙琳对着堆满孩子气涂涂画画以及渗透有戴安泪痕的手稿流下后悔的眼泪。
可以说,尽管戴安这一角色并没有在电影中真正出场,但是观众已经能得到一幅生动的戴安的心灵图像。
三、伦理自由与审美期待
作为一部商业电影,《天才少女》在让观众看到残酷的伦理关系,以及主人公有可能面对的伦理困境的同时,又给予了叙事一个符合观众审美期待的、较为圆满的结局。在法庭的审判下,伊芙琳和弗兰克谁也没有成为赢家,玛丽被判进入寄养家庭成长,到12岁以后才能自主决定和谁生活。在与弗兰克分别时,玛丽表现出了异常的绝望和悲哀,可见其尽管和罗伯塔和弗兰克一直过着幸福的生活,但她的内心深处依然有着强烈的不安全感,对于离开舅舅,玛丽认为这是她又一次“被抛弃”。而弗兰克也为失去了玛丽而陷入木然中。终于,在老师邦妮的提醒下,弗兰克发现了玛丽心爱的独眼猫弗雷德被丢入宠物寄养中心,于是下定决心拿出姐姐戴安临终前给自己的证明手稿换回玛丽的监护权。伊芙琳得到手稿后,将和普林斯顿大学的数学教授联名发表,并在未来的日子里因为收获名利而俗务缠身,而条件就是伊芙琳放弃对玛丽的造梦教育计划。在电影的最后,玛丽终于能和弗兰克生活在一起。
电影通过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戴安证明手稿来实现了一种“伦理自由”。根据斯宾诺莎的理论,伦理自由既是一种能力,也是一种人生和德性的完满境界。在《天才少女》中,伦理自由主要指的是人物的一种理想的伦理关系,人物所得到的伦理关系是符合个人意志的,那么他就获得了伦理自由。在电影的结尾,玛丽一方面能够和弗兰克过着她期盼已久的幸福生活,将得到弗兰克和罗伯塔的关爱;另一方面在教育上,她还将继续在橡树学校的学习,使自己的数学天赋能够得到发展,但同时又能够因为邦妮等人的帮助而继续结交自己的同龄朋友。毫无疑问,玛丽将不再是一个除了数学生活中只有一片空白的,游离于社会的怪人,她将过上和母亲戴安截然不同的一生。甚至即使是已经酿成悲剧的前代伦理问题,即戴安对伊芙琳的怨恨,也在伊芙琳悔恨的泪水中得到了淡化。《天才少女》在展开了两条伦理叙事线的同时,又用这样的方式同时解决了前述两种伦理问题,即教育和亲子伦理问题。
尽管这一结局是理想化的,它高度依赖于一个元素的介入,即戴安的证明手稿。相对于一个悲剧结局而言,它减少了批判的力度,但这是《天才少女》的悲悯德性的体现,也是电影迎合观众审美期待的体现。且由于电影在叙事中已经对“纳维斯—托克方程”进行了充分的铺垫,因此,当戴安已经将其证明这一结果抛掷到观众面前时,观众其实感觉并不突兀。这一叙事策略无疑是成功的。
伦理叙事是从个体性的经验走向普适性的存在,从个别的故事走向具有普遍意义的精神的。《天才少女》通过对玛丽个人经历的叙事,展现了一种个例式的生命感觉,从而引发人们对有关教育的社会意识,以及亲子伦理诉求的关注,并在叙事中通过一种“大团圆”结局试图实现符合观众期待的社会伦理自由。观众在其中感受到的除了玛丽作为个人的体认和生命感觉,更得到了关于儿童成长复杂性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