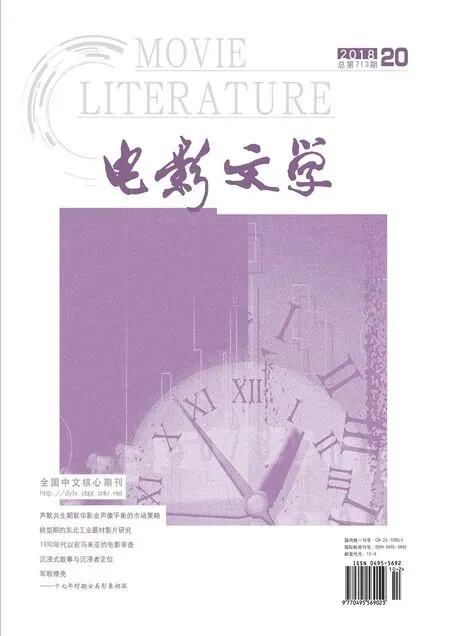国产灾难电影流变与大众审美趣味
崔菁菁
(大连艺术学院,辽宁 大连 116600)
灾难电影以自然界或人类社会出现的规模宏大的灾难为叙事题材,以各类灾难景观为视觉效果,以恐慌、悲痛、愤怒等负面情绪为主要情绪基调,表现人和灾难的冲突、抗争过程。和西部电影、歌舞电影等不同,在诸多类型片中,灾难电影可以被认为目前中国电影与世界电影的风向标——好莱坞之间起步差距最小的一种。在大众文化时代,电影市场日益交错互融,观众一方面可以更为便利、全面地接受非本土的,在世界电影市场上占有统治地位的作品,受到某种时代潮流的制约或主导;另一方面,观众的审美趣味,审美判断又影响着本土的电影创作。国产灾难电影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着流变。
一、国产灾难电影的反思与重建
八一电影制片厂倾全力打造的“惊”字三部曲面世后的反映平平,激发了人们关于国产灾难电影的反思。三部曲分别为由翟俊杰执导,以洪灾为题材的《惊涛骇浪》(2002),王珈、沈东执导,以SARS疫情为故事背景的《惊心动魄》(2003)以及同样出自王、沈之手的,以汶川特大地震为背景的《惊天动地》(2009)。事实上,就选材来看,“惊”字三部曲无不取材于深刻烙印于国人记忆的灾难,真实事件本身就具有极大的可挖掘的戏剧资源,同时又能触动观众的共同记忆;而就艺术来看,三部曲的完成度都堪称一流。
以三部曲中的《惊心动魄》为例,八一厂选择了过硬的电影主创阵容,包括《大决战》的编剧李平分。电影将叙事空间集中在一列飞驰的1120次列车之上,一名疑似罹患了SARS的病人失踪后,被发现就在列车之上。女军医杨萍和列车长、乘警等好不容易查找到这名病患并将其送下列车,疫情却已经在列车内蔓延,不少病人都出现了发烧的症状,还有的乘客强烈要求下车,列车上一片混乱。医生和乘务人员既要保证自己的安全,又要为疑似病患诊治,同时还要安抚乘客情绪,并在列车无法停车靠站的情况下与直升机进行对接以保证物资的运送,整部电影叙事节奏紧密,剧情跌宕起伏。密闭并高速前行的列车与生死存亡挂钩无疑是精妙的设定,无论是之前的《卡桑德拉大桥》《生死时速》,抑或是之后的《釜山行》等,都采用的是这一设定。然而《惊心动魄》却依然难以打动观众。“惊”字三部曲的遭遇并非个例,它们代表的正是一种传统的国产灾难片范式,即灾难救援片,救援(而非个体对灾难的承受,灾难对个体的戕害)是电影的主线,而在救援的过程中领导、军人等国家力量的象征势必要被突出,这就使得电影有政治性压倒艺术性之嫌。
与之类似的还有如向霖的《爬满青藤的木屋》(1984)、毛玉勤的《特急警报333》(1983)、陈国星的《危情雪夜》(2004)、王新生的《生死大营救》(2006)等,其在表达方式上无不具有浓郁的主旋律色彩。而随着大众对其他灾难电影的接受日益增多,这种三十余年来单一、重复,带有宣教意味的范式自然难以满足观众。
值得注意的是,国产灾难电影也在对市场的试探中悄然发生着转变。以同样诞生于21世纪前10年的,张建亚以中国东方航空586号班机事故改编而成的《紧急迫降》(2000)为例,电影在有着扎实的剧本之外,还体现出了重伦理情境而轻政治宣教的特点。到了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类似的尝试更是不胜枚举。因此,我们既需要正视部分国产灾难电影存在的问题,也必须承认其有着向大众审美趣味接轨,努力重建其影响力的一面。
二、大众审美趣味与多元叙事机制
由于类型化意识的缺乏,早期国产灾难电影在叙事上,更接近为剧情片的变种,只是灾难成为剧情中的一个重要背景或情节。而这也就导致了灾难电影叙事上的趋同,叙事时空基本都为现实时空,甚至直接取材于真实事件,情节有着较为严格的起承转合,始终体现着国人喜爱“大团圆”,笃信“人定胜天”的民族心理等。类似美日不依托真实事件的《龙卷风》《天崩地裂》《后天》,或干脆将灾难片与科幻片进行类型融合的如《哥斯拉》《2012》等灾难电影,在国产灾难电影中是难觅踪影的。
而在当下,随着电影对大众话语立场的回归,在前述美日灾难片在中国脍炙人口的情况下,观众呼唤着更为多元的叙事机制,需要电影人更为灵活地处理真实和虚构之间的关系,以更尽情地建立灾难情境。而国产灾难电影也确实呈现出了更多彩的面貌。
(一)恪守真实 以真动人
真实的魅力是永恒的,真实灾难给人们心灵投射下的阴影对于电影叙事而言实为一种助益。2008年的汶川地震催生了一批以汶川地震为题材的灾难电影,除之前提到的《惊天动地》外,还有如八一电影制片厂的《为了生命》(2009)、杨凤良的《5·12:汶川不相信眼泪》(2013)等,而其中得到最高评价的当数赵琦的《殇城》(2011)。其中的原因正是在于《殇城》以一种纪录片式的手法讲述三个遭受地震打击的家庭各自的感伤故事。如地震刚发生时人们混乱地急于出城;地震刚刚过去时,市民们栖居在绵阳九州体育馆中,将大大小小的“寻亲启事”贴满墙壁,使墙壁成为一个硕大的条幅,人与人之间急切地交换照片询问亲人的下落;地震过去许久后,老母亲带着樱桃想给女儿扫墓却被阻拦等,都极为真实,催人泪下。
(二)虚实相间 合理创造
部分灾难片则选取一个历史上的真实灾难事件,但虚构一组群像。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冯小刚根据刘震云《温故一九四二》改编而成的《一九四二》(2012)。“《一九四二》是一部追求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相统一的影片。历史性、真实性与艺术性,构成了这部灾难电影的底色。”电影具有实录的美感,但又不追求完全的真实,电影中逃难的老东家一人无疑是虚构的,但是其家庭成员陷于绝望的坎途中纷纷凋零的过程,无疑是1942年300万灾民遭际的缩影。更为难得的是,电影有意规避了传统的“起承转合”叙事模式,采取令人压抑的“去高潮”叙事,在结尾时也并未让观众得到“大团圆”结局。
(三)天马行空 设计新奇
严嘉的《食人虫》(2014)等怪兽灾难巨制的可喜出现,让我们看到了国产灾难电影也有着如《汉江怪物》《哥斯拉》等一样引入科幻元素的可能。在电影中,由于人类的科研失败,试验用的小虫子变异为食人虫,并且迅速繁殖,向着人类聚居处涌去,一群正在海岛上悠闲度假的人马上陷入危机之中,女主人公拿着电锯挥舞才得以逃出生天。这自然是一种天马行空的想象。在这一类灾难电影中,观众因与叙事情境有着距离而得以在心理上获得安全感,能够更好地享受视听盛宴带来的快感。
三、大众审美趣味与多元审美心理范式
当代国产灾难电影不仅展现了更多的叙事模式,在唤起观众的共鸣,引发观众思考方面,也表现出了对多种审美心理的迎合。
(一)科技力量与心灵创伤的冲突
早期部分国产灾难电影终结于人对灾难的战胜,而当代国产灾难电影则倾向于将观众引向另一个感受方向,即灾难在物质上的巨大破坏,终将慢慢为人类所修复,但是灾难给人类心灵造成的创伤,对于个体而言,有可能终身无法消化,譬如至亲的失去,重新开始生活的信心,而再遭遇另一类型灾难或挫折时的勇气等。对于观众而言,尽管观众有可能并未经历过主人公所遭遇的灾难,但是这种心灵打击却是可以感同身受的。
这其中较具代表性的就是冯小刚的《唐山大地震》(2010)。电影用于表现地震的天崩地裂景象的时长仅有5分钟,从此以后,李元妮、方登、方达等人就生活在了痛苦不堪的余震之中。李元妮在两个孩子只能救一个的时候选择了救儿子方达,这让死里逃生的方登从此生活在了被遗弃的心理桎梏之中,其后无论是和养父母的关系,和男朋友的关系,方登都无法顺利地维持下去,在30年人生的分岔路口上也往往做出错误的决定,如未婚先孕、退学抚养孩子,等等。她虽然在生理意义上的生命没有死于唐山大地震,但是那个心灵健康,原本可以拥有快乐人生的方登早已经随着母亲的放弃而一去不复返。而看似幸运的方达,也因为母亲的这一次抉择导致了亲情世界的畸形,在成年结婚后于母亲和妻子之间永远无条件偏向母亲,给无辜的妻子带来伤害。这是随着时代发展的高科技也无法弥补的。类似这样的,由于一个人生节点上的创伤而招致更多痛苦的情节,贴合了观众的普遍经历和情感需求。
(二)“救世主”式想象
灾难电影就满足观众的心理而言,远远不止于满足观众的猎奇需要,还在于为观众设置了一个有代入感的情境:首先,观众是这场灾难的亲身经历者,必须面对重重困难;其次,观众还在众多的受苦受难者中脱颖而出,成为一个虽万千人吾往矣的英雄,或曰“救世主”。
早期的国产灾难电影在意识形态的思维藩篱之下,无法产生个人主义式的叙事。随着21世纪以来,更多的好莱坞灾难电影乃至超级英雄电影的引入,大众审美趣味也有了对个体叙事的偏向。于是国产灾难电影也开始注重突出个体形象,让主人公展现出超乎他人的责任感和伟力。例如在张建亚的《极地营救》(2002)中,主人公飞行员范康是当仁不让的英雄角色。为了救牺牲了的战友格桑的未婚妻项莉,范康驾驶陆航直升机穿越雪山,在恶劣的地貌和天气中于悬挂在半空的汽车上救出项莉,在直升机迫降于雪山为雪掩埋时,又是范康不断鼓舞项莉,最终两人喜结连理。在这样的叙事聚焦下,观众自然能在救人自救的主人公身上满足自己的“救世主”想象。
(三)死亡痛感
死亡意味着生命的彻底终结,是人类审美活动中反复出现的主题。灾难电影不仅呈现死亡,并且呈现的是规模巨大,形式多样的死亡,鲜活的生命在灾难面前纷纷逝去,多方面地刺激观众,给予观众死亡痛感。最终,观众从痛感中走出,这不是对死亡的麻木,而是在静观生命凋零的过程中,赋予了自己生命以全新的意义。应该说,这种对于死亡的审美是一种人类共同的集体无意识,在艺术中反复欣赏死亡是一种人类拟定的心理契约。早期的国产灾难电影还难以给予观众足够的痛感,而这主要是成本所限而非意识形态造成的,在同时期的战争电影中,大量的毁灭性画面都留给了观众深刻的印象。而随着电影投资制作方式的改变,国产灾难电影也终于可以满足观众的这一审美趣味,用令人不忍直视的死亡来营造崇高和震撼,激发观众的生命关怀。仍以《唐山大地震》为例,电影中堆垛的大片尸体,楼房摧枯拉朽式的崩塌和恐怖的漏电,以及因为雨水和泥污而面目难辨,憔悴崩溃得不成人形的李元妮在无数尸体中寻找自己的丈夫和女儿,这都渲染和强化了一种死亡痛感。
在当代,“消费能力”是大众文化时代下价值批判体系的核心之一,电影是否依循大众审美趣味,是其能否成为大众的消费选择,实现自身商业价值的重要依据。国产灾难电影也不例外。从近20年来的国产灾难电影外在视觉,叙事以及对观众审美心理范式的揣摩来看,不难发现其进行了兼顾商业、艺术价值的有益尝试,在主旋律式的舆论导向与市场双重任务之中寻找平衡。而可以预见的是,随着大众审美趣味的变迁,国产灾难电影还将做出更多的探索,而二者在接触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也要求我们继续寻找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