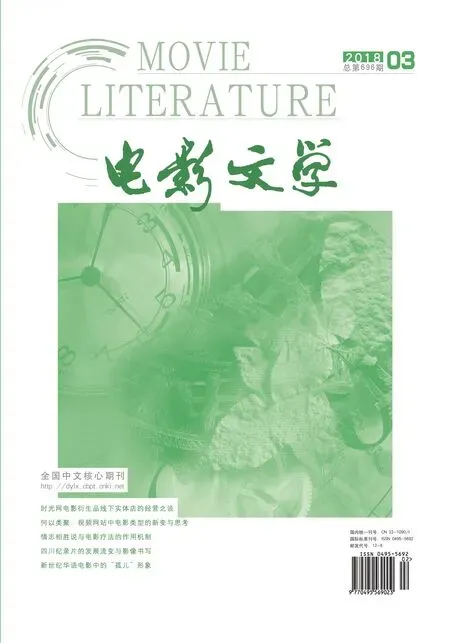《海洋奇缘》:迪士尼公主电影的新变
常海鸽
(西安外事学院,陕西 西安 710077)
罗恩·克莱蒙兹和约翰·马斯克联手打造的动画电影《海洋奇缘》(Moana
,2016)是一部典型的迪士尼动画长片,而这种“迪士尼式”除了体现在其画风、配乐以及叙事主题上,也体现在这又是一部“公主电影”上。但相比起迪士尼过往推出的公主电影,《海洋奇缘》又在体现了类型化模式的基础上进行了创新。无论是因袭抑或新变,《海洋奇缘》都体现了迪士尼对于公主电影的高度重视。一、从无心插柳到有意栽花的迪士尼公主电影
在1937年迪士尼出品《白雪公主》时,迪士尼还并没有创作公主系列电影的主观意愿。其时世界动画电影的主流是围绕动物来进行创作,迪士尼以米老鼠形象蜚声国际,凡伯伦、华纳则以《猫和老鼠》《邦尼兔》等获取卡通迷的青睐等。但是《白雪公主》的成功,包括票房上的800万美元惊人收入和奥斯卡的提名,让迪士尼看到了未来动画电影的发展方向,即向真人电影靠拢,在时长上长片化,在叙事上完整化。同时,迪士尼也是在《白雪公主》中坚定了运用音乐舞蹈辅助叙事和讲述温情美好故事的理念。在取材于格林童话的《白雪公主》的鼓舞下,迪士尼下一部集中了人力、物力打造出来的动画长片依然是一部根据童话故事改编成的电影,即《仙履奇缘》(1950),女主人公灰姑娘辛德瑞拉最后成功嫁给王子成为王妃(princess),因此这也是一部不折不扣的公主(princess)电影。可以看得出来,公主电影的最初形成,是与民众对于拥有财富、美丽和善良等特性的女性有所向往的“公主情结”,以及这种情结导致了反映在童话、传说中的集体性表达分不开的,并非迪士尼对于公主/王妃故事有着情有独钟的喜爱。
而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意识到光芒四射的女主人公和票房之间的密切联系后,迪士尼开始了对公主电影“有意栽花”的创作。而在期盼女性留守家庭的经济市场大萧条时代结束和女权运动兴起的外因,以及迪士尼创作摆脱了童话原著的内因的双重作用下,公主电影开始塑造新一批公主形象。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一批具有突破意义,甩掉了“王冠”的公主出现在银幕上。而到了新世纪,《冰雪奇缘》(2013)等电影中的公主们则走得更远,她们通过更多的渠道来证实自我。迪士尼也在用公主电影来适应经济规则下的商业规则这一点上越来越得心应手。尽管褒贬不一,但不可否认的是,迪士尼迄今为止推出的13部公主电影,几乎每一部都获取了高票房并引发了热议。
由于公主电影的巨大影响力,人们必须承认,迪士尼公主们面对人生所做出的选择,在重大事件前的表现,都深刻地影响着世界范围内银幕之前的女性,尤其是低龄女性观众。相对于迪士尼的其他电影而言,公主电影显然担负着一种非常明确的教化意义:女主人公必须成为一个时代理想女性的标准。尽可能地保持公主电影价值观上的进步性就成为迪士尼的自我要求,甚至迪士尼官方还推出了一份新时代的“公主准则”,其中包括“不以貌取人”“尽最大努力”“相信你自己”等,以此来重新为女性塑造一个“公主梦”。
一言以蔽之,人们集体潜意识中的“公主情结”是根深蒂固的,正如荣格在探讨“原型”时指出的:“所有时代与地方的人类在想象、思想和行为上存在与生俱来的共同潜在模式。”但随着科技的进步带来的经济转型,女性的地位以及人们对女权乃至LGBT等人权问题的认识又是在发生迅猛变化的。迪士尼势必还会将公主电影继续拍摄下去,但附着于公主身上的性别、社会思考是一定会处于变动中的。从迪士尼具有普适意义的“公主准则”中就不难看出,迪士尼所谓的公主,依然是一种梦想物化,但是早已从对荣华富贵身份和花容月貌等的虚拟投射变为对优良品质的追求。
二、《海洋奇缘》的类型化模式
迪士尼动画电影始终被视为“命题作文”,从其优长之处来看,这保证了电影有着标签式的高辨识度,维持了稳定的观众群,低龄观众即使在成年之后,也会因迪士尼情结而继续带孩子对迪士尼进行线上和线下的消费。另外,文本特征固定的创作模式也保证了生产的高效;而从其负面意义来说,这有可能导致电影新意不足,公主电影也不例外。在《海洋奇缘》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戴着镣铐跳舞”的类型化模式特点。
(一)主配设置
人物设置是动画电影创作的重中之重。《海洋奇缘》实质上依然沿袭了传统的主配角设置,飘零海上的莫阿娜依然是一个“受难女主角”,教会她航海和作战的毛伊则是“梦幻男主角”,而在电影中不断制造笑点的公鸡嘿嘿则担任了滑稽的傻瓜这一角色,“邪恶巫婆/恶棍”则由特菲提化身的魔鬼厄卡充当。
(二)叙事套路
《海洋奇缘》中的两条线索,一是莫阿娜的自我成长,一是将特菲提之心物归原主的冒险过程,都带有明显的套路色彩。莫阿娜和毛伊的对手分别从椰子人海盗,变成了侵占毛伊鱼钩的螃蟹怪,最后变成了一切事情的起源魔鬼恶卡,一个比一个更强大,莫阿娜正是在三次战斗中变成了骁勇的女战士和能观星、能看洋流的熟练的海洋寻路者,并且最终正义战胜邪恶的大团圆结局,也与迪士尼之前的公主电影一脉相承。
(三)价值取向
首先是女权主义的价值取向。从《小美人鱼》(1989)、《美女与野兽》(1991)等电影中不难看出,从女性逐渐从“他者”这一不平等地位中恢复过来,解构男性的话语权威是迪士尼动画一贯的价值取向(这在克莱蒙兹每次和马斯克一起完成的动画电影中体现得尤为突出)。在《海洋奇缘》中亦然,女性被标举为有能力的,女性完全可以通过学习来获取能力,成为男性的解救者。电影中的莫阿娜不仅挽救了部落中的凡人,也解救了法力无边,还有些自大、以救世者自居的半神毛伊。在莫阿娜和毛伊的冒险中,莫阿娜一次又一次地改变对弱女子有成见的毛伊的看法,最终成为毛伊身上的“文身”之一。
其次是“给孩子”教育观下的价值取向。与当前同样在动画电影产业内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日本的宫崎骏、新海诚以及美国的皮克斯等动画人或动画公司相比,迪士尼一直以来都有着鲜明的“给孩子”倾向,迪士尼动画在传递正面教育观上的意愿是极为强烈的,也正因为“给孩子”的目的,迪士尼动画不得不一直保证其能让低龄观众接受,这也是迪士尼被诟病为“老派”的原因之一。在《海洋奇缘》中,鼓励孩子进行自我突破,否认家长以个人经验来限制儿童的成长是一个重要的价值观。在电影中,酋长父亲因为曾经出海遇险失去了兄弟而认为海洋是危险的,宁可全岛人陷入生存困境也不愿面对大家的祖上是航海者的事实,让大家驾船离开内海,一次又一次地将莫阿娜从海边拉回,而鼓舞莫阿娜出海的奶奶则得到了肯定。
三、《海洋奇缘》的创新意识彰显
在公主电影的程式已经为观众所熟知后,单纯地重复这一程式显然将使迪士尼不具备市场上的优势,尤其是在动画长片的竞争越来越激烈的今天。在公主电影中加入新的元素,包括引入当代人面临的生存状况,与当代进步思想进行互动等,都是迪士尼公主电影进行创新的体现。如《花木兰》(1998)中鲜明的中国文化烙印,《宝嘉康蒂》(1995)的反殖民主义思想等,《海洋奇缘》也带来了一股新风。
(一)“反公主”的宣言
首先是对“反公主”的声称。在《花木兰》等电影中,公主们已经开始了淡化公主/王妃身份而华丽转身,花木兰最后是与李将军成婚而非王子。这种淡化也体现在《海洋奇缘》中,甚至可以说,《海洋奇缘》是有“反公主电影”的一面的,正如毛伊对莫阿娜所说,他如果是大海,他也会选择一位有着卷曲头发的“非公主”。这里的“非公主”其实就是电影给莫阿娜的一个明确定位。只要与时代最为接近的《冰雪奇缘》,甚至是和《勇敢传说》(2012),以及同样出自于克莱蒙兹与马斯克之手的《公主与青蛙》(2009)相比较就不难发现,莫阿娜和艾莎等人的区别在于,艾莎等人在获得公主身份的特权的同时,也因为公主身份而受到重重约束。例如艾莎必须继承王位担负起统治整个阿伦黛尔的职责,而不能随心所欲地在冰天雪地中给自己建立一个冰雪城堡离群索居等。为此,艾莎相对于妹妹安娜而言,举止优雅,自我束缚,终身不嫁。然而《海洋奇缘》的主旨就是“你要知道你是谁”,这一“你是谁”的问题有力地叩问着毛伊和莫阿娜。电影中酋长父亲带莫阿娜去到山顶看历代酋长垒砌起来的石堆一段,带有非公主电影《狮子王》(1994)中生生不息、父子传承的意味。未来酋长的身份对于莫阿娜来说并不是束缚,相反是她责任感的来源,也是她冒险出海的动机。电影中她为椰子的枯萎和人们打不到鱼都立即想了办法,可见莫阿娜有着主动接受酋长身份挑战的意愿。酋长之女的身份从来就不是她进行自我实现的阻碍,甚至是助力(如来自奶奶的帮助)。最终莫阿娜带领部落走向海洋,在石堆上放上了一个海螺而非前任们的石板,出海和成为酋长(女王)被紧密结合在一起,共同成为莫阿娜的成人礼。
(二)“王子”的退位
一直以来,与“公主电影”概念一起深入人心的,便是“王子—公主”叙事套路。自1950年起,华特·迪士尼就以“程式”(formula)一词明确了“灰姑娘和王子”(Cinderella and Prince)的创作程式。王子解救公主,或公主解救王子,最终王子与公主幸福地生活在一起,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程式,而这种审美中的男权(甚至还有异性恋霸权)意味也是极其浓厚的。在《冰雪奇缘》中,迪士尼已经开始尝试否定这一模式,安娜最终抛弃了心术不正的南埃尔斯王子汉斯,选择了善良的山民克里斯托弗。而《海洋奇缘》则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从头到尾都没有为莫阿娜安排一位异性伴侣,“王子”角色彻底的缺席。在太平洋壮阔的海浪中,莫阿娜和毛伊是战友关系,莫阿娜的历险最终实现的是一个女性对一个女性的拯救和征服,即莫阿娜将心还给了女神特菲堤。莫阿娜和毛伊互相欣赏,而绝不涉及男女之情,最终他们也各自回归作为凡人和半神的不同生活轨道中,这种“泛性别”情感关系的创造,其实也是《海洋奇缘》“反公主”特色的一部分。
正如人们所承认的,迪士尼不仅是世界动画电影长片的先驱,在当下也是动画电影创作和营销上的巨头,迪士尼每年精心打造的动画长片都对全球动画电影的创作方向有着巨大影响,对全世界观众来说也有着无可比拟的导向作用与教化功能。迪士尼电影人主观上也有着在从事动画产业运营,打磨动画艺术的同时,宣扬独特价值的要求。这就导致公主电影成为迪士尼进行文化和价值理念传播的载体。从80多年来迪士尼公主电影的变迁中我们也不难看到,迪士尼一方面对于进步思想和具体艺术手法有所坚持,另一方面又会根据时代的变化而在美学和价值观的传达上进行调整。《海洋奇缘》中有着“反公主电影”的色彩,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依然是一部公主电影。迪士尼在其中表现出对成熟类型电影的共性继承以及根据新时代审美倾向进行的创新,可见迪士尼对公主电影的偏爱,这对于我国电影人的创作也是有着启发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