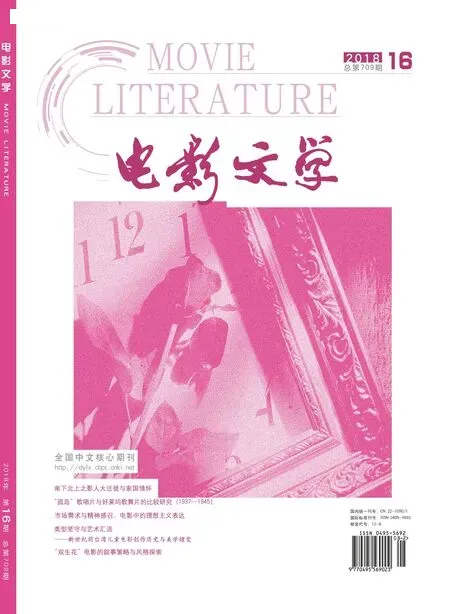《刺客聂隐娘》的意境美学
马 莹
(天津科技大学 艺术学院,天津 300457)
在当前影院观影行为已经被赋予了一种消费和感官娱乐的仪式化功能时,侯孝贤延续了自己“电影作者”风格的《刺客聂隐娘》(2015)在这种氛围中无疑是显得格格不入的。尽管这部侯孝贤“八年磨一剑”的电影在戛纳等电影节上揽获好评,但由于与国人所习惯的传统武侠电影区别较大,电影在上映后引发了较大争议,贬者多诟病其沉闷的叙事,而褒者则注意到了电影中独特的、属于侯孝贤的艺术风格。应该说,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风格,个性化表达与观众普遍的审美趣味上,侯孝贤选择了前者,在电影中营造了略显曲高和寡的审美意境。
一、意境美学与侯氏电影
“意境”的概念在我国传统艺术文论中由来已久,已成为一种跨越不同艺术领域,且具有民族性的美学理论范畴。自唐代王昌龄的《诗格》至今,人们对于意境有着林林总总的阐释,在诗词、戏曲等的理论批评中,意境所代表的审美价值和审美理想也略有不同。一般而言,人们普遍接受,所谓意境,指的就是创作者的一种主观的艺术联想,有形、有限的景与物经由创作者匠心独运的熔铸,被赋予了无形、无限的,接受者能够领略、理解到的情感。
人们已经意识到,电影作为一门诉诸观众视觉的叙事艺术,既是绘画艺术在银幕上的变体,又是叙事文学的另一种书写方式,它是完全可以实现对意境的追求,制造“虚实相生”“境生于象外”的美感的。但必须承认的是,主动地对意境美学进行追求,将中式美学在银幕上外化,即使在中国导演中,依然是属于较为少见的。电影艺术更多地承袭了西方的戏剧艺术,而非中国的“剧诗”(张庚语)。而西方戏剧自诞生以来,就高度重视叙事性,曲折的情节和严峻的冲突是西方戏剧的最高要求,也是自古希腊戏剧到莎士比亚、莫里哀等一以贯之的艺术追求。而在批评上,如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都将戏剧视为一种写实主义的“模仿”,可见西方戏剧强调的始终是行动与具有叙事性的斗争冲突。及至到电影中,中西方电影人也已经接受了电影的重点在于人的行动与冲突,斗争的出现和斗争的解决。诗的生命很难在这种电影观中得到延续。
也并非没有电影人主动在创作中吸纳中国传统美学理念,这在武侠电影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武侠电影是中国电影艺术中较为独特的,承载了中国传统文化底蕴与侠义精神的类型片。如李安、张艺谋等有意为电影打上中式烙印的导演在进行武侠电影的拍摄中无论就场景设计、人物造型或叙事结构上,都有了对意境美学的追求。如《卧虎藏龙》(2000)中李慕白与玉娇龙的竹林之战,《英雄》(2002)中无名与长空的琴馆对敌,无名和残剑在意念中完成的水上对剑等,都成为武侠电影在影像表达上注重意境美的典范,也为中国武侠电影惊艳世界奠定了良好基础。但值得注意的是,李、张从不会将意境构建与电影的商业追求对立起来。李慕白和玉娇龙在竹林中穿行本身就是视觉奇观的打造,《英雄》中更是以具有悬疑色彩的“罗生门”叙事结构全篇,影片对比鲜明、浓艳的色调本身也是服务于这一叙事的。
而初次尝试武侠电影拍摄的侯孝贤则不然,整部《刺客聂隐娘》中,电影矫矫不群,几乎难见任何一点对商业的妥协。聂隐娘在“杀”和“不杀”之间徘徊,就已经是整部电影最具有张力的戏剧冲突。正如编剧谢海盟表示的,聂隐娘的“刺客”身份是非常明晰的,身为刺客她理应遵从组织或雇主的要求,“剑道无亲,不与圣人同忧”,而抛弃属于“侠客”的个人是非判断。然而聂隐娘却屡屡自作主张,先是因为“不能断绝人伦至亲”而放弃刺杀大僚,后是因为担忧魏博动乱,加上内心的旧情而对田季安不加刺杀,反而护卫。聂隐娘的情怀越来越趋近家国天下,而与《英雄》中复杂的、令人情绪激荡的残剑刺秦王,残剑衣袂飘飘地为无名在黄沙之上书写“天下”,无名以“天下”嘱托秦王不同,《刺客聂隐娘》只是不厌其烦地展现着聂隐娘沉默的、面无表情的凝望,全片中聂隐娘的台词也极少。原著唐传奇中的神怪色彩,聂隐娘和磨镜少年神秘的、令人遐想的情感,这些本可以成为消费时代电影“卖点”的内容,在电影中也遭到了压缩。
而只要对侯孝贤之前的电影,如《风柜来的人》(1983)、《海上花》(1998)等稍作了解,就不难发现这种对剧情的弱化,正是侯孝贤一以贯之的风格。相对于建立起一条有着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的叙事李安,和精心铺排戏剧冲突,或是打造夺人眼球的刺激画面,侯孝贤更愿意以一种内敛甚至是令人昏昏欲睡的方式叙事,让人物长时间处于静止状态,并寻找自然景观中的气韵,将其与人物暧昧幽深、难描难言的情感相结合,最终形成深远而悠长的意境。而《刺客聂隐娘》也不例外。
二、《刺客聂隐娘》意境美学透视
(一)虚实相生的取景
侯孝贤的电影一贯热衷于以一种极为安静、舒缓的节奏完成叙事,长达数秒的长镜头,在叙事上形成跌宕的空镜头比比皆是。《刺客聂隐娘》中,嘉信公主和聂隐娘在漫天白雾中结束对话,以及或秋水长天、烟波浩渺,或秋草枯黄、古道西风瘦马的镜头都是例证。在无声的湖泊山林中,侯孝贤以固定机位展现了天地大美,甚至为兼顾胶片拍摄和景致之美而专程去日本取景,但也被观众批评为使电影过于沉闷,这主要是观众并未能站在侯孝贤的角度“以我观物”。有学者曾指出:“在侯孝贤电影所提供的想象域中,自然景物始终是作为某种自我认同的对象化自我展示的,作为物我合一的契机,提供了对社会现实的超离。”如外景与内景,都市公寓与小镇景象等的对比,在侯孝贤电影中,都大有深意。而在《刺客聂隐娘》中,电影尽管脱离了侯孝贤擅长的对“前现代乡土台湾”的范畴,但在将景物转化为符号域这一点上,电影与侯孝贤之前的电影,如《在那河畔青草青》(1983)、《恋恋风尘》(1986)等是如出一辙的。在电影中,静美开阔的外部自然世界,和华美、阴暗的魏博幕府内景形成了一种对比,而自然世界才代表了主人公的一种理想自我。草长莺飞,蝉鸣阵阵,云舒云卷的景物是“实”,而聂隐娘对于自由的向往,以及在磨镜少年等人身上得到的心灵慰藉则是“虚”,穿行在自然草木中的聂隐娘几乎和自然景观融为一体,放下了手中的剑,进入到了“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自由境界中。尤其是在电影结尾,聂隐娘和磨镜少年在极富古韵的美景中骑马远去,观众能从这浪漫幽远的景色中意识到,这意味着身体和灵魂都获得自由的聂隐娘终于得到了自己的幸福,终于超离了唐代藩镇割据、同室操戈的丑陋现实。
(二)意象的选用
意象来自于“立象以尽意”的美学追求,指的是在诗歌创作中将独立的客观外物视为特定抽象情感的载体。而电影也有着这样的“有意味的”镜像话语,正如马塞尔·马尔丹在《电影语言》中指出的:“由于电影画面含有各种言外之意,又有各种思想延伸,因此我们倒是更应该将电影语言同诗的语言相比。”精妙的意象提供了观众一个从能指走向所指的思维挑战,是电影意境美学能否成功建立的关键。在《刺客聂隐娘》中,“剑”和“镜”的意象是最为关键的。聂隐娘的人格完整,是在从嘉信公主宣扬的“剑道无情”走到自我选择的“剑道有情”中完成的,在剑这一外物中,侯孝贤赋予了其仁恕、不杀等儒家道德理念。聂隐娘对剑道的把握,也是她突破精神困境的过程。武侠电影将剑上升到人格高度,并非侯孝贤的独创,这里有必要着重提及贯穿全片的“镜”意象。
在嘉诚公主落寞抚琴的长镜头中,侯孝贤为观众介绍了“青鸾舞镜“的典故,而这也是理解嘉诚公主、聂隐娘,乃至侯孝贤本人的关键。这个典故出自南朝宋范泰的《鸾鸟诗序》,孤鸾被罽宾王得到后,三年不鸣,临镜后以为见到同类,便慨然悲鸣,最终展翅奋飞而死。嘉诚公主从京师远嫁到魏博,并且遣散一切随从侍女,表示从此“京师自京师,魏博自魏博”,与曾经的生活一刀两断,陷入了“一个人,没有同类”的寂寞中。而聂隐娘在被嘉信公主收养后,也丧失了自己的原初身份,在失去亲情之前,她又因为田季安已经和元氏女定亲而失去了爱情,在背负了刺杀任务时,聂隐娘早已失去了自我。嘉诚公主和聂隐娘都是极度孤独之人,悲鸣而死似乎成为她们唯一的命运。只是在面对“镜”时,聂隐娘开始了对自我的凝视和反思,终于找回自我,完成了对自我主体的塑形,即结束自己的刺客身份,与磨镜少年经由新罗归隐东瀛。而这也充盈了磨镜少年这一几乎没有台词的人物形象。磨镜少年来自倭国,与聂隐娘原本语言不通,但聂隐娘看到了磨镜少年为小孩微笑磨铜镜的场景,瞬间涤除心尘,从有碍突破到了无碍,磨镜少年就是聂隐娘这一只“青鸾”的“镜”,只是聂隐娘这只青鸾最终选择振翅飞走。
(三)叙事的留白
在意境美学中,留白是极为重要的。留白原为书画艺术中,以“空白”为载体,进一步渲染出美的艺术手段。在《刺客聂隐娘》中,电影的留白是多种多样的,如各种点到即止的镜头:精精儿面具的掉落代表了激战后聂隐娘取得了胜利,鸟群惊飞暗示了幕府中人在林中驰骋,聂隐娘后背衣服的撕裂,代表了她也为精精儿所伤等。电影省略了大量本可以成为奇观的打斗过程,体现出一种淡泊至简的美感。更值得一提的是,聂隐娘少年时代,曾在田季安生病时紧张地注视他,因为田季安被定下了和河洛元氏的婚事而成为栖于树梢的“凤凰”,甚至去元家大打出手的情节,这些本是极具戏剧张力,甚至对于观众理解剧情极为重要的情节全部被电影省去,而改为由田季安对爱妾胡姬讲述。观众与隐在帘幕之后的聂隐娘一起倾听,加上聂隐娘将内心的五味杂陈隐藏在没有表情的面孔下,使得电影显得平淡不少,也使得部分观众无法理解为何聂隐娘母亲说公主“屈叛了窈娘”后聂隐娘掩面痛哭。而也正是在这各种留白之中,电影进行的始终是一种向内聚敛的叙事,即让观众关注的始终是聂隐娘的心灵世界,而非娱人耳目的、热闹的各种斗争。聂隐娘对“我”的找寻,对既定命运的突破,以及她一次又一次地在窥视和偷听中,愈发不忍和拖延对田季安的刺杀,这种深邃微妙的心灵体验,才是侯孝贤希望观众领略的。
正如侯孝贤所言,《刺客聂隐娘》是一部他“拍给自己看的电影”。可以说,《刺客聂隐娘》并非观众所习惯的、符合观众审美期待的武侠电影。侯孝贤有意摒弃了如张艺谋、李安等导演在武侠片中常用的商业元素。尽管爱情、政斗、武打都存在于《刺客聂隐娘》中,但电影并不以一波三折、情天恨海的两性情感纠葛,声势浩大、令人炫目的打斗场面来吸引观众,而是高度重视在内容及表现形式上意境美学的营建,丰富、扩充着人们对于武侠电影的理解。在《刺客聂隐娘》中,观众得以看到“侠”文化和唐传奇故事的一种以山水写意,以风声抒怀,以蝉鸣为诗的新的讲法,而浮躁的当代中国电影市场,也多了一种可贵的美学坐标。
——从《刺客聂隐娘》看侯孝贤的“归去”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