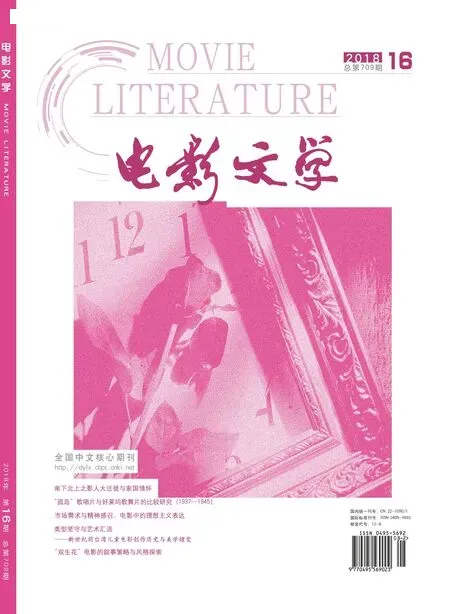南下北上之影人大迁徙与家国情怀
吕少勇 魏媛媛
(1.北京电影学院,北京 100088;2.南昌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江西 南昌 330031)
电影作为艺术总是受到时代氛围的影响,正如法国理论家丹纳所言:“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件艺术作品,我们必须正确地设想他们所处的时代和风俗概况。”他认为艺术是时代和环境的产物。抗战时期很多影人由于战争进行了大迁徙。这种电影人才的流动也带来了电影创作风格的变化。“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特别是上海沦陷后,一部分电影工作者南下,促进了香港电影业的变化。”在整个抗战期间,前后有三批影人南下香港,对香港电影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这么说战乱环境造就了那个时期的香港电影。这恰恰是丹纳所谓的时代和环境造就了当时的电影创作。这一时期因时局动荡不安,上海影人南下香港拍摄电影,尔后,常往返于两地拍摄的影人逐渐增多,直至1945年后到达顶峰,20世纪50年代后“香港制造”的影片中可以看到诸多南下影人的身影。本次“南下”迁徙使得香港国语片得到繁荣,南下影人进步的电影思想和美学观念提升了香港电影圈的整体制作水平。自1979年改革开放,国内拓宽了两地合拍片的限制后,出现了不少到内地取景拍摄的电影。2003年,在中央政府与香港特区签订CEPA协定后,大量香港影人北上拍片,使得内地的商业片市场得到蓬勃发展,延续了港片在20世纪90年代的辉煌。两拨影人的大迁徙都不同程度上促进了两地电影市场的发展。为了能够吸引更多的观众走进电影院,几位导演都把视野聚焦到了历史题材片上。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运用这一题材,避免了影人初来乍到的水土不服。因此,“如何剪裁出以一个合乎中国想象的电影场景,但同时又不会掉失了寄语香港故事的基调”,是上海“南下”影人和香港“北上”影人的探索之道。
“家国情怀,是主体对共同体的一种认同,并促使其发展的思想和理念”。在电影创作中主要指电影制作方对“家国”共同体的认同并在影视作品中得以体现。无论是“南下”影人还是“北上”影人将历史题材通过影像的形式把这种家国情怀呈现出来。本文中所探讨的四位导演朱石麟、张彻、陈可辛和许鞍华都凭借着自身对中华伦理文化的独特见解,完美诠释了家国同构的叙事特征,自发地将个人、家庭、国家联系起来,以此来表达导演们心中的家国想象。
朱石麟在1946年离开上海前往香港拍摄电影,其作为香港电影业的首批开拓者之一,为香港电影贡献了不少的经典之作。在《清宫秘史》中,朱石麟延续了他在上海拍片时的一贯风格,把“家”与“国”融合在一起,秉承了朱石麟一贯的以家庭伦理为主的叙事传统,将中华文化作为影片根基,有效地构成其对“家国”的想象。朱石麟作为南下影人,在创作生涯中始终把中原文化作为电影的根基所在。虽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香港的发展使得其想重新进行身份定位,但大中华的历史文化仍作为故事的元素在朱石麟的影片中呈现。这也是1945年后南下影人在创作国语电影时所保留的共同认知。
张彻虽差不多与朱石麟同时期离开上海,但他却没有直接到香港,而是跟随国民党在台湾拍摄电影,1957年后才到香港。20世纪50年代后,由于中英关系恶化,少有香港拍摄的电影能够进入内地市场,加上香港经济飞速发展,电影商业市场逐步扩大,影人将目光更多地聚焦于香港本土市场。相较于朱石麟仍停留在寻找两地共同文化,张彻转战到香港后则一直跟随时代的潮流,拍摄香港人的电影。张彻开启了香港的彩色武侠国语电影的时代,在其代表作《刺马》中他跳出了上海老套的武侠片模式,追求紧张刺激的逼真打斗动作片,虽没有彻底摆脱程序化的功夫表演模式,但是凭借其巧妙的剪辑手法、精彩的场面渲染,仍创造了独特的“阳刚美学”的电影风格。虽电影商业市场此时已完全针对香港本土,但是张彻作为南下的影人,身上仍有不少内地的影子。张彻的历史武打片既跳出了传统武打程序化的表演场面,又保留了中国自古以来的侠义精神并将其丰富内涵化,将现代流行元素和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有机融合。
相比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南下影人“被迫”在香港拍片,1978年改革开放后内地和香港就已经开始共同开发影片,振兴内地和香港的电影市场。两地合作拍片的历史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形成风潮,内地为影片提供风景优美的拍摄地和廉价劳动力,借此吸引大量投资方北上,降低香港电影业的投资成本。加之东南亚电影市场的饱和,香港影人进军内地电影市场则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自2003年CEPA签订十几年后,大量香港影人“北上”摸索新出路,使内地和香港的合拍片成为“大中华电影圈”的主流走向。而陈可辛是其中的佼佼者,2005年凭借《如果·爱》进入内地电影市场后,横跨了内地同香港几十年的文化差异,精准定位市场需求,探索出一条“陈可辛”式的成功之路。2007年投资四千万美元由陈可辛执导的电影《投名状》斩获8座金像奖、4座金马奖奖杯。票房虽不及《英雄》,但仍得到巨大的成功。陈可辛选择《投名状》为进军内地的第二部电影,其中可以看到香港电影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从简单的善恶观到剖析人性的多变,从《刺马》到《投名状》,也呈现出“南下”和“北上”影人的时代差异和定位取舍。陈可辛把香港现有的电影观念,融合进“大中华”的历史文化之中,并加以全新的诠释,试图在内地与香港文化中寻找到平衡点,当然陈可辛也做到了。其在之后的《中国合伙人》《亲爱的》等电影中细腻地讲述中国故事,构建两地的文化认同感,更好地针对内地与香港的商业市场,都获得了不俗的成绩。
许鞍华作为香港电影新浪潮的领军人物,也早早地加入影人北上的浪潮之中,曾拍摄过《玉观音》《姨妈的后现代生活》等以内地为故事背景的电影,虽在其“北上”时期回到香港拍摄了《天水围的日与夜》《天水围的夜与雾》《得闲炒饭》以及《桃姐》,经过一番徘徊之后,仍再次进军内地,创作了电影《黄金时代》和《明月几时有》。许鞍华的电影拥有独特的女性视角,将女性的柔情与细腻纳入时空的鸿沟之中,但其视角又很冷静,常常以旁观者的姿态审视整个环境。许鞍华导演的新片《明有几时有》虽票房失利,且口碑两极分化,但影片作为香港回归二十周年的献礼,仍是上乘之作。北上的香港影人拍摄主旋律电影早已不是新鲜事,许鞍华导演在70岁的高龄还拥有一颗向前冲的赤子之心,为观众展现抗战期间香港无数英雄的抗日场面。华语电影圈的聚焦点越来越向北京靠拢,导演许鞍华仍会把香港情怀与内地背景有机融合,讲述更多真诚动人的家国故事。
几位影人在影片题材上都选择了20世纪前后中国国家动乱的时代背景,国家的动乱使小家庭的生活瓦解,政治变革、民不聊生成为影片的主要前提依据,在家庭与国家变为矛盾双方的过程中,国家对于家庭和个人的挤压日益加重,在传统伦理约束中,人物命运也愈加悲惨。
朱石麟导演的《清宫秘史》与张彻的《刺马》、陈可辛的《投名状》年代相近,《清宫秘史》展现了1889年珍妃入宫到1900年慈禧携光绪逃离紫禁城的这段历史,而《刺马》和《投名状》讲述的都是清末四大奇案之一的发生于1870年的“刺马案”。在这个时期,中国还被称为清朝,此时社会动荡已经慢慢涌现出来,而各自家庭也随着太平天国起义、八国联军进京等一系列政治事件而跌宕起伏。在《刺马》中,米兰虽已嫁与老二黄纵,但奈何黄纵生性好色又有强烈的大男子主义,跟随老大马新贻后官运亨通,有钱有势,变得更加为所欲为,加上马新贻形象伟岸,使得米兰对大哥日渐倾心。任两江总督后,马新贻设法杀死二弟黄纵,并将弟妹米兰占为己有。在这段时间内,太平天国运动风起云涌,朝廷内斗激烈,清朝皇室也处于两宫太后垂帘听政的局面。在《刺马》中,上述时代背景成为国家的时代符号,对家庭构成以及内部成员的关系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影响,影片中也呈现出了类似“家庭乱伦”的非常规家族关系。张彻借助这一故事表现了中国传统社会中家庭关系的忠贞与狡诈、正直与罪恶的矛盾关系。《投名状》中老大庞青云的出场就与《刺马》中的不尽相同:庞青云原本就是为清朝卖命的军官,可惜在一次战役中其视如兄弟的战友们因为友军的见死不救完全战死沙场,只剩下庞青云一个人苟延残喘。社会骚动变乱,时代中的小家庭也随之起起伏伏。《清宫秘史》里珍妃被迫投井,慈禧和光绪带着其他妃子逃离北京。《明月几时有》中母亲带着方兰离开原生家庭,母女二人相依为命。在历史题材作品中,几位导演不约而同地将历史背景作为影像符号,规避了宏大的叙事场面,将时代变迁缩小到家庭的细微生活之中,展现了导演个人的历史观,把简单的家庭生活注入社会动乱的丰富内涵,用小家庭内部的伦理道德来重现历史发展进程。
朱石麟、张彻、许鞍华以及陈可辛都偏爱使用家国同构的叙事方法,将家庭的伦理失衡与国家政治有机融合,把中国儒家文化中家国同构的观念在家庭权力争斗中呈现出来,表现出导演对于中国政治的独立思考。
影片《清宫秘史》里,朱石麟把整个国家的兴衰浓缩在一个家庭之中,光绪称呼珍妃为“二妞”,慈禧喊妃子为“孩子”,唯有光绪称慈禧为“皇阿玛”,构成了三组矛盾关系。《清宫秘史》的故事虽集中描述了皇宫的小家庭生活,但慈禧和光绪的一举一动却关乎全天下百姓的生活,将家庭伦理与国家、民族结合在一起。这是一种专属“文人电影”的情怀,从家庭生活入手,把伦理化的故事打上朱石麟的标签,借助“家国”的文化内涵,有效地把大中华的历史作为主体框架,完成了其对“家国”想象的叙事。在陈可辛版的“刺马案”中,同样是老大庞青云派人暗杀老二赵二虎,老三姜午阳刺死庞青云的故事构成,区别于张彻的家庭传统伦理的描述,陈可辛把赵二虎之死归结到了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义之上,而三人之死的惊奇故事更像是对当时社会乱象的再现。三人作为立下生死状的结拜兄弟,本身就构成了儒学思想中家庭的概念。而在三人组建其小家庭的过程中,陈可辛更注重刻画“人性黑白之间的灰”。三人难辨善恶的性格特征恰好与当时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的社会性质相类似,家庭的崩塌与社会的动乱成为同一过程的两个视角,构成了陈可辛式的家国同构的叙事模式。许鞍华导演的新片《明月几时有》中也有浓浓的家国情怀。方母从最初自私自利的包租婆到成为舍生取义、宁死不屈的一代英雄,方兰为了整个游击队的生命安全和对地下工作的保护意识放弃解救方母,都是一种舍弃小家救大家的精神。方母的逝去和李锦荣被枪杀,东江游击队失去重要力量,与日本在香港越演越烈的疯狂掠夺交叉进行,将家庭生活与国家战争协调统一,形成了家国同构的叙事模式。许鞍华导演“以女性独特的细腻叙事,将艺术光影融入整个战争主题的叙事之中,展现了一幅幅红色革命历史的生动画卷”。
纵观两拨影人在内地与香港的南下与北上的迁徙,我们可以看到在他们的作品中一致呈现的家国情怀与风格变迁,始终与时代的氛围伴生,与家国命运共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