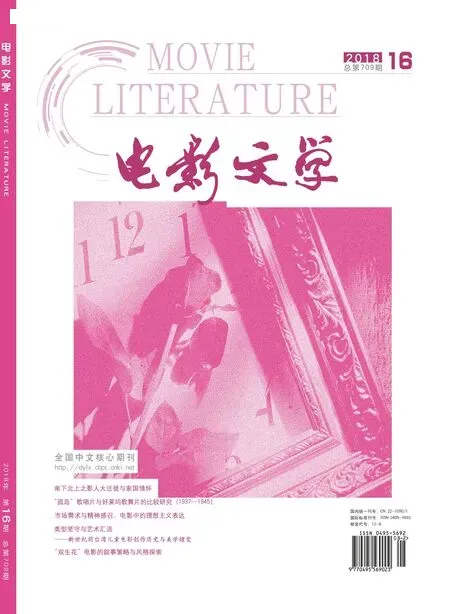《1980年代的爱情》:从文学到电影
杨涵钧
(韩国清州大学,韩国 清州 360-764)
从处女作《赢家》(1995)开始,霍建起就不断凭借着自己独特的导演风格吸引着人们的注意。在霍建起的电影中,人们几乎总能寻觅一个乌托邦式的,迥异于令人焦虑和不安的现实社会的生存净土,精神家园,或是一段纯真的,人们在社会发展中遗失了的情感。其新作《1980年代的爱情》(2015)也不例外。电影改编自野夫带有半自传色彩的同名原著,电影在对原著的价值取向、情节梗概进行了忠实还原之外,也根据当代观众的审美倾向,以及电影艺术自身的特色对原著进行了改动。
一、原著审美理想的保留
在整个故事的主要情节、人物形象等方面,《1980年代的爱情》都做到了忠于原著,更重要的是,保留了原著的审美理想。野夫对于他心目中“1980年代的爱情”寄予了最为深切的怀念,认为那是其他任何时代的爱情都取代不了的,极为纯真的一段情感。也正是在野夫的这种心理滤镜下,“我”原本条件艰苦,内外交困的这一段小镇生活被视为人生中最宝贵的经历,闭塞的公母寨也显得山清水秀,当地的土家族人也让“我”感到淳朴善良,“我”甚至不愿意再离开小镇,而只希望能够留在这里与心爱的丽雯长相厮守。整部小说充斥着大量作者的内心独白,而情节则极为简单。而霍建起正好是当代影坛的一位“电影诗人”,小说重情感而轻情节的特点是与霍建起电影的风格不谋而合的,在其如《那山,那人,那狗》(1999)等电影中,情节都并不复杂,最令观众难忘的是人和人之间暗流涌动的情感,以及电影中情景交融、唯美诗意的画面。美术出身的霍建起极擅长用美好的物象来表达情感,生活中普通的、无生命的事物都能在其镜头之下被赋予情怀。
首先,在《1980年代的爱情》中,人物理想主义的一面得到渲染。霍建起延续了原著对“人”的关注,对美好情感和品行的赞美。关雨波在内心中一直保留了给丽雯的位置,愿意为丽雯付出一切,而丽雯则更为无私地希望关雨波离开自己,因为了解关雨波是一个属于远方的人,是一个应该在路上的“天下客”,丽雯在深爱关雨波的情况下推开了关雨波,让他去闯荡四方。当关雨波借赞美丽雯的父母侧面表达出对丽雯的爱:“患难相依一辈子,留下来也没什么不好的。”丽雯直接回复道:“你懂我爸的陪伴,可你理解我妈的歉疚吗?”甚至在两人90年代重逢之后,发生了肉体关系,寡居的丽雯因为自己上有瘫痪的婆婆,下有小女儿,没有与关雨波进一步建立关系,并把自己生活困难,身患癌症的情况对关雨波守口如瓶,不让情感成为对方的牵累。
其次,为了能突出这种“水过三秋,有些话就像梦一样,说破了,就剩一地碎片”含蓄唯美的感情,电影设置了诸多犹如静美清新的小品的桥段,带观众进入到主人公的情感世界中。如在葱翠的清江边,丽雯坐在河岸晃荡着双脚,听着小雅送给她的随身听,音乐响起,是悠扬的俄罗斯族民歌《永隔一江水》:“波浪追逐着波浪,寒鸦一对对。姑娘人人有伙伴,谁和我相偎。等待等待再等待,心儿已等碎,我和你是河两岸,永隔一江水。”而关雨波则走到河边,一边洗脸,随后与丽雯在说笑中打起了水仗。这一段的色调、画面与意境实现了完美的结合。类似这样的画面在《那山,那人,那狗》、《蓝色爱情》(2000)中也多有出现,观众在看到男女主人公以及人和自然的和谐相处时,也感受到了霍建起一直用心建构的温柔敦厚的乡土意识。霍建起擅长将有别于都市文化的乡土环境打造为一个主人公心灵栖居的“家园”,让主人公和观众陷入在无限的追缅之中。
正是这种对于主观情愫和物象营造的重视,原著中平缓、温和的叙事节奏也得到了保留。在原著中,野夫采取一种主观介入的视角,不厌其烦地叙说着自己对丽雯的情感,两人一直若即若离,而生活则似乎没有任何波折。电影中也如此,包括关雨波在工作中误将诗歌当成给领导的演讲稿的失误,都因为工作调动的到来而轻轻揭过。随后关雨波在进入90年代后的坎坷经历也被一笔带过,丽雯再次出现,在惊鸿一瞥的见面后,关雨波再一次得到丽雯的消息就是她的死讯。在关雨波顺利地收养了和丽雯长相酷似的丽雯的女儿后,电影也就落下了帷幕。一切都平淡得酷似生活的原貌,但又在一帧帧画面中具有感人至深、催人泪下的力量。
二、戏剧冲突的加入
电影的创作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这也就使得《1980年代的爱情》与原著在有着大体上的“同”的同时,又有着“异”。考虑到过审以及让人物的性格和心理更为单纯的需要,原著中“我”入狱的原因被改为替他人担保受骗,丽雯父亲落魄的原因也由“第三种人”改为了在“文革”中因为丽雯大舅的海外关系遭受牵连,至今没有被恢复身份。因此,丽雯父亲对“我”说的大段与政治有关的,引发“我”深思的内容也全部被删除。原著中“我”和丽雯的父辈曾经是宿命式的“斗”与“被斗”的关系不复存在。原著呈现给读者一个复杂的外部世界,而电影则全力提供给观众一个温情脉脉的土家族山乡,尽管减损了原著的丰富性,但也避免了观众对人物形象有可能产生的混乱认识以及电影上映的其他阻碍。
电影最明显的改编就是,在《1980年代的爱情》中,霍建起加入了小雅这一人物,即关雨波在大学时候的女朋友。在原著中,“我”的女朋友始终没有正面登场,她在毕业后留在了省城,与“我”只保持着极容易受到天气干扰的书信联系。女朋友希望“我”能考研去省城与她团聚,而“我”却在见到了丽雯之后产生了留下的念头,并开始质疑自己与女朋友这种没有“痛感”的感情是否是自己需要的爱情。而在电影中,女朋友借着出差的机会来到小镇看望关雨波,并在小镇留宿了两晚,也有了一个小雅的名字。由于考虑到男女同居一室的不便,关雨波将小雅安置在了丽雯在供销社的小屋,尽管关雨波介绍丽雯为自己的“女同学”,小雅还是敏锐地感到了对方在感情上对自己的威胁。在原著中,女朋友游离于小镇叙事之外,只在“我”的回忆中出现,两位女性的对立也只在“我”的意识中展开,这无疑是较符合现实情况的。而电影则为了戏剧冲突的需要,通过制造小雅出差的巧合让这一人物登场,并让小雅结识丽雯,对丽雯产生敌视,也将关雨波不得不在两位女性之中做出抉择的心态明面化。这是一种典型的化生活矛盾为戏剧冲突的改编方式。
“生活矛盾是生活中的原始状态,一般是散漫的,进展缓慢的,错综复杂的,有的矛盾没有激化成冲突就转化了,各种矛盾交错影响,情况比较繁杂。而戏剧冲突是由作者经过长期深入生活,掌握住生活矛盾发展的必然规律,加以概括集中,典型化,根据主题思想的要求,突出一种矛盾冲突,加强它的戏剧性。”在原著中,属于生活矛盾的这场“三角恋”最终由于“我”的心志不坚,与女朋友并非情投意合而无疾而终,并没有激化成冲突。而在电影中,小雅则在幽暗温暖的供销社小屋质问丽雯:“你也喜欢他对不对?”而丽雯的回答则是:“山里人的喜欢和你们的喜欢是不一样的。”随后,小雅逐渐感受到丽雯的善良和无私,包括了解到丽雯也不愿意关雨波留在小镇上耽误前程,态度马上发生了改变,甚至将自己贵重的随身听送给了丽雯。小雅尽管出场时间不多,但是自作主张帮关雨波报名考研,又将随身听送给丽雯,抱着丽雯的肩膀直白地对丽雯表示“我喜欢你”,一个强势、开朗的城里姑娘的形象被塑造起来。相对于原著中只是一个符号式人物的女朋友而言,小雅给观众留下了较深的印象,观众也在小雅对丽雯的肯定中,进一步感受到了丽雯的美好和可贵。
三、民俗奇观的营造
而必须注意到的是,霍建起一直保持着自己在两代导演群体之间的特殊性,保持着自己并不迎合市场的诗意电影风格,并不意味着霍建起电影的创作思路是纯粹个性化,无视受众的。相反,从《那山,那人,那狗》赢得的世界性赞誉,在《暖》(2003)中邀请香川照之出演以打开日本市场,在《情人结》(2005)中选择赵薇与陆毅出演并针对情人节档期做了一定宣传就不难看出,霍建起并非是一名无意于弥合艺术与商业,自我与市场,乃至民族与世界鸿沟的导演,甚至在其作品从文学变为电影的过程中,不乏与同时期导演趋同的一面。
在《1980年代的爱情》的改编中,这种趋同就体现在民俗奇观的渲染上。在原著中,野夫对“哭嫁”和“跳丧”两个仪式只是约略提及,更多的笔墨被用于表现“我”内心的主观情感流动。然而对于电影艺术来说,相对于以旁白来表露主人公的思维和情感,观众更愿意接受多彩的画面造型和新奇的民俗意象。另外,赋予民俗意象以指代意义,将一个对观众而言陌生的封闭空间与质朴的生活气息,人们或压抑扭曲,或热烈奔放的生命情态并置,在某种程度上也能提升电影的深度。因此,在电影《1980年代的爱情》中,“哭嫁”和“跳丧”两个仪式被以视听语言综合性地渲染和夸大。在“哭嫁”中,新娘身穿红装,头披红盖头,房屋里挂着一排红灯笼,少女们则在新娘两边坐着,唱着悲哀的歌,被触动心事的丽雯也借此机会流下了眼泪。原本应该是“嘴哭心里甜”的“哭嫁”仪式在这里被悲哀化了,而大片的红色则给予了关雨波一种震撼,他本人的欲望萌动也在这一片红色中被外化了。而“跳丧”则相反,黑白两色成为主色调,作法之人在丽雯的棺木之前身穿黑衣,头戴白布,载歌载舞,用一种狂欢的方式让死者实现飞升,这在关雨波看来是美的,但他依然难以承受,备感压抑。因为死去的不仅是丽雯,也是关雨波心中永远回不去的木楼老屋,袅袅炊烟。
用一系列带有神秘色彩的民俗奇观来增加电影的辨识度,给予观众一种在视听上的来自异域情调的享受,并非霍建起的原创。无论是第五代抑或第六代导演,都不乏为了构建一个能够安置民俗奇观的时空,而改变原著背景者。例如张艺谋改编自刘恒《伏羲伏羲》的,加入了“拦棺”等民俗的《菊豆》(1990)就模糊了原著的时代背景,也对原著的故事进行了截取而非全盘复制。又如《大红灯笼高高挂》(1991)将苏童原著《妻妾成群》中的江南背景置换为了山西干燥、封闭的四合院,规整的院落更使得电影新加的“点灯”习俗显得触目惊心。这些民俗奇观的出现,在吸引观众目光,增强电影的东方色彩的同时,也使得叙事具有某种隐喻或象征修辞,可以说并非导演的哗众取宠。
同一个故事从文学到电影的过程,实质上正是观众对文学作品以影像为媒介进行选择和接受的过程。霍建起的《1980年代的爱情》正是对野夫原著的一种“重读”,霍建起在题材内容、艺术结构、人物形象等方面让文本的故事鲜活起来,又根据电影的需要对原著进行了新的阐释。另外,《1980年代的爱情》的改编也再一次证明了,电影对文学的改编引导着观众的品位和倾向时,也受着观众审美趣味、时代审美风尚的规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