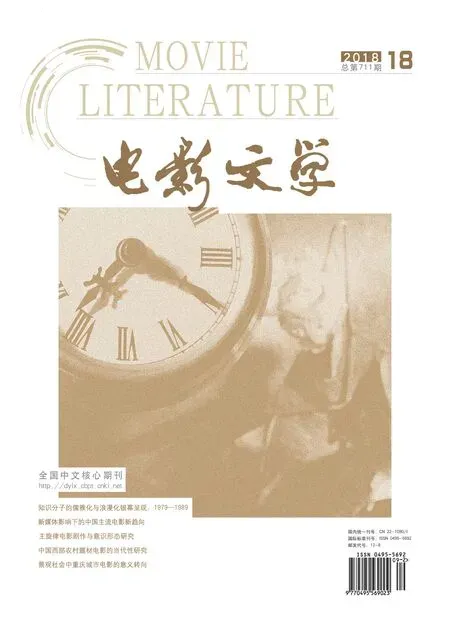克拉考尔电影美学思想的现代性分析
相龙烽
(黑龙江大学 哲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1006;齐齐哈尔大学 文史学院,黑龙江 齐齐哈尔 161006)
克拉考尔在其电影美学理论中充分融入了其对当代社会现代性的理解。基于这种理解,他对他所认定的通俗艺术媒介——电影做出了理论层面的细致分析,这种分析可以视为以电影为现象的当代审美文化批判。这种理论因其矛盾性和鲜明的“现实主义”精神而独具一格,同时他的电影美学思想也打破了技术时代所形成的专注电影语言分析的局面,使电影成为审美文化的重要研究对象。
一、克拉考尔的“现代性”思维
关于现代性,克拉考尔首先注意到的是现代生活的碎片化存在形态。现代生活中,古典的仪式感已经消失,日常生活从感官生活中逃离出来,变成了以物质追求为核心的繁复琐碎的重复动作。“那些能使人团结起来,以及不仅能把他们团结起来而且还能激发他们最高冲创力的东西”开始变得越来越少,“……最值得一提的是,灵魂最紧要的需求,即宗教性,已经支离破碎了;再没有任何一种活生生的且具普遍约束力的信仰,来表达我们的本质”。在克拉考尔看来,现代社会已经从完整的审美经验世界瓦解为碎片了,太多的物质诉求使现实沦为充满功利与欲望的荒诞社会。按克拉考尔自己的理解,他对电影的研究“目的是探溯电影手段的特性”,这种特性用他自己的话来解释就是:电影总是“热衷于描绘易于消逝的具体生活。”这正好契合了当代社会所展示出来的现代性特征,那些瞬间的、极易变化的、无中心的现象与事实。所以在克拉考尔的心里,电影天然地承担起描述当代社会的使命。然而,同一切艺术手段一样,电影在反映现实生活的时候,同样经过了选择与加工,这就引发了克拉考尔理论的矛盾:一方面,他希望电影能带来真实的物质现实,这种真实是本质的真实,而不是现象的真实;另一方面,他看到某些电影对现实的神化,他认为这种神化已经成为一种背叛,这些电影对现实充满了想象与限定,使现实只存在于电影所营造的神话空间中,从而使这种媒介形式偏离了克拉考尔所坚信的电影反映生活本质的目标,电影只是神化了生活,而没有真正反映生活。
如何反映真正的生活,则成为克拉考尔对电影讨论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在他看来,这种“真正的生活”一定与“意义”密切相关。因为克拉考尔认为,伴随现代性碎片化特征同时出现的另一个特征就是“意义的丧失”。这里既包括上述“宗教性”意义的瓦解,也包括日常生活意义的匮乏。宗教性意义的瓦解意味着关切着人类命运的终极信仰的缺失,日常生活意义的匮乏则导致了人类生存空间审美感觉的沉沦。他认为,尽管现代社会的知识内容急剧增长,但同时也出现了“世间意义之匮乏”——当然,这也是与韦伯对当今世界的最为悲观的审视相一致的一种观点。
波德莱尔说:“我们从表现现在中获得的愉悦不仅仅来源于它可能具有的美,而且来源于现在之作为现在的本质属性。”他又进一步解释了这种现代性特性理解的具体内容:“说起现代性,我指的是过渡的、短暂易逝的、偶然的,是艺术的一半,它的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即现代性既指向生活现象的“新奇”,又指向了“新奇”背后不变的本质意义。这种特性对于现代性而言,并不直接指向否定的或者肯定的价值判断,这种判断的两难在克拉考尔那里被鲜明地表现了出来。克拉考尔对电影的现代性特征所进行的思考,在表面上看是契合了这种观念,但克拉考尔所要求的电影对物质现实的复原观念则表明,在克拉考尔心里,现代社会生活处于一种破碎无序而令人厌倦甚至愤慨的状态。“新奇”不应是已然失去意义的现实表象,那些隐藏在变动不拘的现实背后的意义,才是真正的“新奇”,电影则要通过自身的优势,挖掘这些素材所包含的真正意义。这与波德莱尔在对现代性进行反思的时候,曾经给艺术家划定的基本任务目标是趋同的,波德莱尔认为艺术家的任务就是对“现在之过渡,偶然之新奇”的捕捉。而对意义的执着,则使克拉考尔对“新奇”的理解与波德莱尔产生了差异。他认为在“新奇”的现代性特征之更深处,是由“真正的意义”所连结的人类共同体,这与当今我们所讲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并无本质差异。这种观念,使克拉考尔的理论相比于波德莱尔(甚至更多人)的理论更富于鲜明的实践性。他自己也说,他的电影美学理论与绝大多数其他著作极为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它是一种实体的美学,而不是一种形式的美学。它关心的是内容。”从理论渊源上来看,这种真正的人类共同体观念会使我们想到涂尔干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的论述,也同样会看到克尔凯郭尔所谈到的宗教共同体观念,这些观念的核心都认为人类都面临着同样的个体生存困境,只有连接个体的“意义”或“本质”才会使人真正成为现实的人,这与卢卡契意义充盈的时代观也同样保持了相同的理论基调。
换言之,克拉考尔关怀的是被掏空意义的物质现实如何展现人类文明,以及丧失了或者不能实现其内核或本质的、日益成问题的个体。
克拉考尔现代性理论的第三个出发点是科学理性对完整审美经验的破坏。进入现代社会后,尤其是19世纪后半期开始,科学理性似乎使一切都有了言之凿凿的逻辑基础,一切都是可实验的、可分解的、可推断的。然而,科学理性却在满足人类幻想和生活“意义”的探寻过程中显得极其乏力,因为在这个环境中,逻辑代替了想象,认识代替了审美。在大多数语境下,这本是一个共识问题,但克拉考尔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提供了一种可供操作的解决方案,那就是对通俗文化媒介——尤其是电影的寻求。维特(Witte)为克拉考尔《大众装饰:论文集》所写的跋中曾明确表示,克拉考尔最重要的贡献在于“他的观察都是围绕着高雅文化的边缘区域,并且最终落脚在那些通俗文化的媒介上”。这些通俗文化的媒介就包括电影。然而不止维特,许多艺术家甚至包括克拉考尔本人,都对电影的文化身份存有疑虑。他既想使电影独立,又觉得所谓的高雅与古典的艺术已然不能反馈当代社会文化的大众属性。而能承担起大众文化心理描述任务的,似乎只有以电影为代表的通俗文化媒介了。
值得简单说明的是,与一般现代性理论不同,大多数理论家(也同样包括波德莱尔)主张发现和说明现代性之美,而在克拉考尔看来,现代社会的恶更多,所以,他声称电影应该回归到物质现实本身,而不是解释现代性所带来的浮躁与冲动。克拉考尔对现代性的热情还停留在对现代性启蒙的信仰中,他并没有以一种“厌倦”的方式体验物质的基本意义和社会日渐分裂的运转形式,他相信现代性的总体方向仍然是解放人类思维与审美经验。
二、作为“神话”的电影
从上述独特的“现代性”观念出发,克拉考尔通过对电影作为通俗艺术媒介的特性分析,指出电影的出现弥合了人类审美经验的诸多不足,电影从而作为一种神话性的言说方式出现在现代社会,并成为“现代性”的重要代言人。他声称电影素材是对镶嵌在时间中的方方面面的事实的复制。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复制也仍然是对自然要素的构型才完成的,以他来看,荒谬而虚幻的电影幻想就是社会的白日梦,而在梦中,真切的现实与被压抑的愿望也最终展现其本真的意义。
卢卡奇曾说,当“意义开始从世界消失”,并且“在灵魂和形式之间、内心和外部世界之间裂开一道鸿沟时”,小说便兴起。小说表达了现代“超验的无家可归感”和“解体得混乱不堪的世界”。对于克拉考尔而言,这种表达形式已经从小说转化为电影这一新媒介手段。深受齐美尔影响的克拉考尔对齐美尔关于现代性的概括深信不疑。齐美尔曾说:“一切都在闪烁,一切都在流动,一切都是含混,一切都汇聚于变动的形式。这就是我们所生活的混沌世界。”而在1923年的克拉考尔,笃信齐美尔所说的并非某一具体现实,而是由当代生活的现代性所激发出来的人们在“审美领域”对生命意义和生命形式统一性的深刻思考与不懈探求。在此,克拉考尔还指出了这种使艺术作品实体化的做法——在艺术作品中,“虚幻的现实,在他那里成了真正现实生活的替身,”现实已经沉默,电影却重新站出来说话。克拉考尔对电影的寄望,就像在对所有人说:看,难道你们都忘了吗?这才是你们真正的生活,这才是真正的现实,你看到的神话就是你的生活,你本质的生活。而你已经麻木,已经忘却,已经破碎。电影把这一切贯穿起来,让你眼前闪亮,让你重新看到了生活。现代性是我们的错,是我们不可避免的一切结果,然而,并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
克拉考尔眼中的电影作为现代性的结果,却从骨子里反叛现代性笼罩下的现代生活。这恰恰如同神话作为文明混沌的结果:人们在生活中得到一切,却又渴望着对未知生活知识的反叛,从而转身求助于神明。只是今天,这个“神”变成了一种艺术媒介。克拉考尔眼中的当代社会是充满了种种问题的,作为敏感的局外人,他认为现代性主要表现在:它(现代社会)把任何永久的和不变的东西都从生活中剔除并禁止它们发生作用,剩下的就只有日益“原子化”的自我。从这些问题可以看出,克拉考尔所执念的电影对物质现实的回归,是出于纠正人们对世界的偏见而做出的最大声疾呼。人们在现实中已经扭曲了世界景象,他们所欲求所生存的世界时空已经被种种缥缈的欲望所掩盖。正是带有这样一种悲观的情绪,克拉考尔不相信人能创造现实,也不相信人能创造脱离世界的真正正确的观念。
所以克拉考尔的理论当中,最主要的核心是:电影是发现而不是创造。在他看来,人们所有的创造都是扭曲的、变形的,只有电影才能回归现实,只有回归现实才能发现真实,只有发现真实才是这个时代最需要的思想起点。技术从来不是救世主,技术更多带来的是假象,技术只适合充当恰当的手段,只有通过技术而进行的发现活动,才能带来对真实世界的理解。应该说,克拉考尔是积极而不是消极的,尽管面对着难以言说的混乱的现实世界,但他对世界本身并没有怀疑,他仍然相信人类还走在求真求美的大方向上。这一点,他超出了历史上许多哲学家,那些看到人类文明危机就主张“小国寡民”思想抑或“自然主义”思想的哲学家,与克拉考尔相比较,就显得消极了许多。从这种认知出发,当克拉考尔有一天突然发现了电影之于现实的意义时,他便义无反顾地走上了“神化电影”的道路。他把现实的混乱归结为人们对现实的操控,归结为人们为了表达个人抽象理想与观念而对现实(真实)的破坏。他考察了种种艺术形式后,断言只有以摄影为基本手段的电影,才是与现实最接近的艺术形式。电影才是真正的信仰,电影才是真正的人类文明的神话,电影同神话一样具有隐喻性的语言,这种话语系统可以保障“意义”的存在;电影同神话一样具有情感的逻辑结构,这种结构可以保障叙事的真实感;电影同神话一样具有审美共通性,这种共通性建立在人天生的审美能力基础上,它确保人们对意义的理解可通过审美感觉而非理性逻辑进行。在这里,克拉考尔强调的是 “神话思维”的持续,而神话思维的任务就是构筑真理。电影所表现的世界,是一个早已在真正的神话中被构想出来的王国,那些神话讲述的并非奇闻趣事,并非是资本主义对集权意识进行艺术建构而形成的“白领文化”的神话。同这种叙述相比,“克拉考尔觉得电影的神话更具有启蒙价值。因为正是电影让人们在屏幕上看到一个现实,看起来很美的表象之下,是工厂机器流水线一样的生产现实。”
不过,如果把电影作为纯粹的一种艺术形式,克拉考尔本人应该是不能同意的。所以我们也清楚地知道,他小心翼翼地防范电影沦为艺术是因为艺术天生是现实的藩篱,在艺术的世界里,只有思想是自由的,而现实早已扭曲。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克拉考尔对电影发展前景深深的忧虑与他对现代文明的怀疑与批判,而这些顾虑也正是他的电影理论充满矛盾性的根源。
三、充满现实主义精神的现代性反思
克拉考尔所说的“物质现实”是胡塞尔“现象”概念意义中的“现实”,这种现实是一种带有“意向性”的“纯粹意识内的存有”,这种理解刚好符合克拉考尔对完美现实的想象。现代性的“新奇”观念对克拉考尔来讲似乎是一颗毒药,他立志要将“新奇”的浮尘去掉,留下澄明完美的现实本身。这就决定了克拉考尔心中的电影必然具有独特的叙事方式,一种借用了古老神话外壳的现代意义叙述。
克拉考尔的理论中,电影不是电影本身所表现的单纯艺术形态,电影只是手段,犹如古老的神话从来不是表达神话本身的文字意义,而是延指语意逻辑的中心,一种对现实的想象与还原。神话的初始表达形态是言说与文字。德里达甚至认为,只有言说才是真实,所有的文字(书写)都带有先天的隐喻性特征,亦即书写本身就是对现实的神化,从而书写成为神话的基本表现形态。随着非理性主义的出现,传统神话言说方式,譬如箴言与训条,已经无法满足现代人对意义的发现与理解。电影从技术手段进行革新,改变了人类的“书写”方式,开启了思维的新途径,电影从而在某种意义上成为神话的“现代性”形态。神话在现代社会中以一种全新的面貌出现在大众视野中,它攫取了文字在生活中的位置,使沉默的文字退居思维的底层,神话欢欣鼓舞地开始选择电影作为自己的言说方式,毋宁说,在书写与言说的现代对抗中,神话选择了电影这种言说的方式。正是在此意义和基础上,克拉考尔才认为电影对物质现实的复原是天然使命。
不同于后现代主义反理性主义目标的快乐主义,克拉考尔反理性的目标骨子里仍然是现实主义的。这是其现代性审美思维的重要特征,阿多诺甚至称他为一个“好奇的现实主义者”。与其同时期的现代主义思想相比,克拉考尔的现代性思想仍然是建立在传统文化批判的角度上的。克拉考尔是以一种理性的神话对抗非理性的神话,以一种启蒙的艺术对抗集权的口号宣传(他称之为盲目的理想化共同体)。克拉考尔所强调的对内容的表现,对物质的现实的复归,都基于人类对自身生存环境,即其所言的“存在”(being)的渴望与认同,这个“存在”甚至也包括了“人”这样一个物质现实。在西方哲学的历史中,存在被无数次提起,也被无数种方法所阐释,而克拉考尔应该是第一个把这样一个抽象的词汇变成活生生的现实的理论家。在他心里,本质存在的稳定性和生活意义的挖掘是一个难以释怀的梦想,而变幻无穷、转瞬即逝的现代性的生活,则呼唤着电影这样一种媒介挺身而出,扛起启蒙的大旗,记录那些短暂却本质的瞬间。这恰好符合他利用充满现代性特征的现代生活作为电影素材,却转而抨击现代生活中现代性弊端的美学逻辑。
总体而言,同时期的现代主义浪潮并没有使克拉考尔走向后现代主义的犬儒主义,反倒可以认为,正是克拉考尔接近极端的“现代性”启蒙思想,才使其电影美学的观念传诸后世并产生巨大影响。如果没有这种带有浓重“现实主义”味道的现代主义对抗,克拉考尔的电影美学思想特色将不复存在。
注释:
① 齐美尔认为,启蒙运动所倡导的永恒理性的自我在物质主义和资本主义时代日益原子化,而克拉考尔对这一点深信不疑。所谓社会原子化是指“由于人类社会最重要的社会联结机制——中间组织的解体或缺失而产生个体孤独、无序互动状态和道德人际疏离、社会失范的社会危机”。具体可参考田毅鹏、吕方:《社会原子化:理论谱系及其问题表达》,《天津社会科学》, 2010年第5期,第68-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