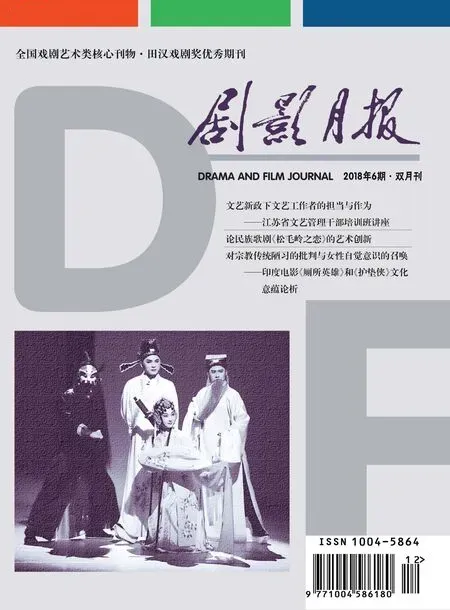多时空交织的命运交响曲
——评话剧《张謇》的悲剧精神
近年来传记体戏剧活跃于中国舞台上,在传记体戏剧中,人物的性格和生活是其唯一的内容,如何掂量传记人物的生命厚度,用怎么样的方式触摸传记人物的灵魂深度,则需要剧作家在得历史三昧之后,在其戏剧观关照下,将琐碎素材加以裁剪,重新组合元素,谱写属于传记人物的命运交响曲,而后由有才华的导演将之演奏于舞台上。而话剧《张謇》(李明华导演、罗周编剧)就是这样一部独出心裁的史诗巨制,是一部用家国情怀书写孤独者壮举的壮丽诗卷,有着不一般的分量。
话剧《张謇》无疑是一个悲剧,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为悲剧的性质下了定义,“悲剧是对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它的媒介是经过装饰的语言,以不同的形式分别被用于剧的不同部分,它的摹仿方式是借助人物的行动,而不是叙述,通过引发怜悯和恐惧使这些情感得到疏泄。”而悲剧之所以成为悲剧,主要在于悲剧人物,而悲剧人物的选择往往是特定。“希腊和现代的伟大悲剧都产生在时代得转换之际:它的出现就象是从吞蚀一个时代的烈火中升腾起得火焰。”而“张謇”正是做成悲剧的一块好料,“张謇”正是一个伟大的悲剧人物。胡适先生曾这样评价:“张季直先生在近代中国史上是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他独立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三十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百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终于因为他开辟的路子太多,担负的事业过于伟大,他不能不抱着许多未完的志愿而死。这样的一个人是值得一部以至于许多部详细传记的。”
张謇究竟何许人也?张謇不是末路英雄项羽,他是晚清状元,是著名的实业家,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历史命运,是与中国的国运、是与多舛的时代联结在一起的。因此,只有将“张謇”置之于广阔的社会背景、政治背景中,才能正确地理解张謇的个人命运与社会命运,他的悲剧精神才会以如此强烈的艺术形象震撼人心。
话剧《张謇》的结构颇有特色,其在舞台上并置了多重平行时空,将“张謇”置之于诸多社会空间中,在家国危机之中拉开了大幕。可以说,此剧的结构完成了“张謇”悲剧精神的呈现。一开场,则是1922年张謇的七十寿宴,人生看似达到了巅峰时刻,但实质上危机已现。直奉二系的贺礼官拔枪相斗,这一无厘头小插曲折射出军阀纷争的年代,这也是“危机”的一个侧面,直奉二系开战,商路全断,也断了滞销棉纱的东北销售之路。朝代的更替、时代的动荡或通过像这样的小插曲、或通过点滴的回忆——一种近乎意识流的手法自然地勾勒出“张謇”的人生轨迹。山雨欲来风满楼,寿宴还没开席,坏消息一个接一个传来,40多家盐垦公司无一盈利、赔累不堪,大豫、大赉、大丰三家负债250万元……于是有了“两次”公开盘账。第一次是在“张謇”的回忆时空,在噼噼啪啪的算珠声中,某年舞台后方的银幕上数字闪烁、不断增加,从满清到民国,皇帝、总统、政客如走马灯似的换,可张謇办的大生两处纱厂总共赚了16620173两白银,可他力排众议,不想着寻钱生钱,却想着用钱散财,想着通州应有剧场、医院、图书馆,应有公共汽车,应改善育婴堂、残废院甚至监狱,他已经办了300多所学堂,仍怜悯学童在暴雨天气在泥泞的马路上步履艰难,决定将计划中25方里设一所学堂改为每16方里,打算增加200多所学堂。第二次则是在当下——七十大寿第二天,银幕上的数字依然闪烁,却不断锐减,大生三个纱厂共亏损15948724两白银,这些债亦不都是纱厂之债,也是公益之债、是南通乃至淮南地方之债……“张謇”眼见着起高楼、眼见着楼塌了,然而“张謇”在大生的重重危机中,仍然决定遵照承诺建设第三养老院,靠变卖寿礼、登报卖字凑钱……以一己之力竟然兴建成功了。一边要“亡”,一边要“兴”,这两边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戏至这里,让我联想起一个故事,王尔德童话里的“快乐王子”悲天悯人,为他的城市里男男女女所遭受的苦难、所遭遇的悲惨生活无法释怀,央求小燕子把他的蓝宝石眼睛、剑柄上的大红宝石、身上贴着的纯金叶子衔给贫穷的人们,冬天来临,当“快乐王子”看见小燕子冻死在脚下,铅心瞬间裂成两半,可失去了装饰的快乐王子却被市民们嫌弃了,最后被工人们放在炉子里熔化了,铅心扔在了垃圾堆上,春天来临时,天使带走了这座城市最美的两样东西——铅心和小燕子的尸体,上帝复活了他们。
张謇所建造的“南通”像是“童话王国”、中国的“乐土”——“烟囱高耸,工厂井然,水陆运输线四通八达,每一寸土地都得到耕种”,但是“张謇”却不是童话中的“快乐王子”。当其散财为国为市为民之后,独自承担起其自谓的“张謇之债”,旧识日本实业家宫本弘之委托佐藤资助800万元,张謇以“鱼欲吞龙、鼠欲食虎”拒绝了。其翘首以盼美国福特公司放贷,但福特因中国年年战争拒绝放贷,在毫无出路之际,宫本又托佐藤前来主动放贷1000万元、参股40%,但张謇却选择与四家国有银行签署“清资抵债协议”,宁愿“拆碎”大生,也不愿它落入日本之手。张謇“没有因令人困惑的问题而引起的心智挣扎,也没有对解脱的渴求。”戏至此,“张謇之悲剧”已经刻画得淋漓尽致了。
但编剧仍觉不够,编剧罗周曾说过在这个戏里有两条线索,一条是70岁往后发展的线,一条是70岁往前回溯的线。在我看来,其实并不尽然。这两条线发展到“平行空间”这一层次,已不再只是交织了,这种“平行空间”升华了悲剧人物以及悲剧精神,恍惚间我似乎看到了《星际迷航》中青年斯波克在平行空间中遇见了老年斯波克。话剧《张謇》中,老年张謇在“平行空间”中两次遇见了中年张謇。第一次是老年张謇似在幻境中徜徉于江边,把伏栏准备自杀的中年张謇一把扯开,为钱烦神的两人展开了对话,中年张謇应承办纱厂整整4年了,既利国利民、抵制外货,又可为乡人开条生路,但钱却无着落,老年张謇告诉中年张謇只要一直往前走,大生便可开车纺纱,在此后20多年将会开办国内诸多第一,如第一所私立师范学校、第一个商会、第一间渔业公司、第一所博物馆、第一所民办气象台、第一处警察学校、第一个医学院、第一所戏剧学校……倚赖大生生活之人少说几十万,每年为地方兴的利益将近千万。但尽管如此,其人生仍是不幸的,因为70岁之时,当人颐养天年之时,大生垮了、欠了无数的债,荣誉名声一一脱落,可谓人到暮年一无所有。中年张謇闻此语,发了三问,那些学校还在吗?那些残废院、养老院、育婴堂还在吗?那些四通八达的全县道路还在么?既然都在,怎能说“一无所有”?“何必悔?”“悔什么?”而第二次相遇,更是神奇。大雨倾盆,后台一声“銮驾回京”,舞台上一束光照在匍匐跪地的晚清官员身上,大雨如注般地淋着他的头顶,中年张謇却兀自站立一旁,如电影中的“特写”镜头。只因雨中接驾这一幕,中年张謇辞官还乡,而两位张謇在这个时空再次相遇了。中年张謇说其平生之志未能实现者十之八九,问老年张謇可是个败者?老年张謇答曰,“人道无路之处,我便筚路蓝缕,要开条路出来。纵有万般苦处,都是自找、该当自受,安之若素、甘之如饴!求仁得仁,三十年矣。”中年张謇问其所生何念何想,老年张謇答曰“中国之大生、大生之中国。”三十年的跌宕,三十年的奋斗,做官求作为不成,经商求发达难为,一个理想主义者的伟大孤独感染了在场的观众,全场掌声雷动。
这两段可以视之为该剧的华彩段落,明知未来的悲剧结局,明知命运的走向,明知毁灭自己的困境所在,但仍然始终不渝、不改初衷,不问胜败,忍辱负重,只求理想之实现,这也实现了张謇自身的超越,这怎能不让人动容?这怎能不让人的情感得到升华?这怎能让历史忘却?联系到当下急功近利之社会,此剧无疑具有强烈的指喻现实锋芒。
正是在多重时空游刃有余地游走,话剧《张謇》在处理一些重大历史事件时能达到“举重若轻”的效果,最让人深刻的是改朝换代“祭辫子”这一场。辛亥革命那年,张謇快60岁,革命军到了通州,众乡绅惶惶不可终日时,他让妻子为其梳理好辫子、系上了大生纺的白棉纱,“咔嚓”一声,辫子断了,这里又是一个“特写”,一束冷冷的白光照在了辫子之上,似乎是在祭奠“状元”称号,也在祭奠一个逝去的王朝。
此外,话剧《张謇》“闲笔”运来娴熟,有一笔不得不提及,那就是和尚这一笔。七十大寿宴席开始前,张謇在谦亭“遇见了”来随喜的了然和尚,实则是在梦中相遇,但梦醒时仆人却来相告外头有个和尚送来了一份礼单,即偈诗一首:“一树菩提满眼花,霎时明灭入烟华。千丝万缕剪难断,兴也在它败亦它。”在佐藤第二次想收购大生之际,了然和尚又来了,此次则是在真实的当下展开了对话。和尚与偈诗使得此剧增添了一份神秘,一些禅意,叩问了命运,开辟了另一重境界。
话剧《张謇》的戏眼是“大生”危机,整个舞台上流淌着朋克工业风格的诗意,舞台上用金属材料做成了一个巨大的斜坡,戏就在“斜坡”上展开了,“斜坡”具有明显的象征意义:70岁的张謇看似走到人生的坡顶后一落千丈,然而他的精神就像“快乐王子”般始终矗立在顶峰关怀着一民、一养老院、一座城乃至这个国家。这种朋克工业风格的舞台恍惚让人回到了黄金工业年代,剧中有一场景发生在大生公司最为鼎盛的时期,张謇有意带领众乡绅参观,金属“斜坡”有了一个变化,在机器的轰鸣声中,舞台上营造出千纱万线状似飞瀑的景象,这种风格是对张謇实业精神的致敬,亦是对黄金工业年代的致敬。
注释:
1.[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陈中梅译注:《诗学》,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0页。
2.[德]卡尔·雅斯贝尔斯著、亦春译:《悲剧的超越》,北京:工人出版社,第9页。
3.胡适:《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序》,《吴淞月刊》第4期,1930年。
4.[德]卡尔·雅斯贝尔斯著、亦春译:《悲剧的超越》,北京:工人出版社,第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