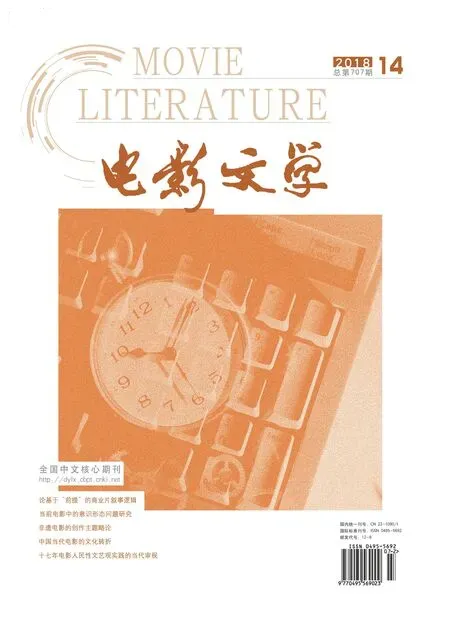女性主义视野中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
韦惠文
(广西民族大学,广西 南宁 530006)
众所周知,就影像的历史文化属性而言,电影存在着“地方性知识”指向,其所建构起来的阐释对象必然会涉及“民族电影”范畴,意即由于电影的运作机制特性,其所显现出的意义世界,也必然随着时代、社会、文化、族群进行变迁。就此点而言,中国的民族电影,尤其是最具代表性特征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毫无疑问是一道有思想阐释深度和深层价值的文化景观。
而在这些纷纭复杂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其话语生产除了多元异质的民族身份书写外,与之并存的性别表达自然也是不可忽视的重心。可以说,作为一种包含性别差异的形象符号,无论是早期的《摩雅傣》《阿诗玛》等片还是晚近的《新康定情歌》《额吉》诸片,女性在其中充当的角色,既是男性权威话语下的主要表现对象,同时也是文化立场上的政治诉求、身份认同、国族想象等要素的重要载体。所以,从女性主义的视野出发,探究、解读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所潜藏的观念意义,揭开隐蔽在符号背后的意识形态,无疑是有益的尝试。
一、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以女性为中心的叙事
女性主义,按照通行的观点,其主旨是对“一种正常平等权”的维护和争取,是对父权主导的社会体制予以反思,其整体性特征并非是二元对立的模式,而是更为强调女性人格的再现,而具体到在电影上的政治和文化实践,其核心则在于让女性冲破限定的性别体系,推动作为女性主体的“人”走到银幕乃至历史的前台,进入女性主义反思的视野中去。中国电影中的少数民族题材影片,以《五朵金花》《芦笙恋歌》等最早期影片为滥觞,一个显著特色,就是其对女性的塑造和主题的传达上,几乎和“五四”以来的女性解放思潮同步,有着写实叙事电影的套路,强化女性经验对于少数民族电影文本的补益,富有中国特色。
一方面,在少数民族题材影片中,女性人物往往被置于叙事的中心,并在电影语境上配合以写实感极强的日常生活的还原。影片并不刻意抹杀由于民族之间文化的差异性而导致的女性性格的区别,而是在承认差异的前提下将之作为一种整体性的对象来呈现,在一种日常生活的书写中,凸显其来自边缘的、异质性的、作为反差存在的符号效果,满足大众对于异域文化的想象与窥探的心理需求。在这种语境中的女性符号,不同于新中国成立前的温婉而逆来顺受的女性形象,也差异于现今好莱坞为模板的几乎泯灭性别区隔的角色塑造,而是渗透着一种日常生活的记录式表达。《黑骏马》展示了一个全新的也是完全和内陆地区异质的新疆草原世界,离家十多年的白音宝力格带着希冀重返草原,力图寻回记忆中的温情和爱人。画面中的镜头所至,都是“尽可能地直来直去”,避免人物和行为被剪切得支离破碎。而作为中心人物的索米娅,所有的言行、情感几乎都是透过对她日常生活的记录式方式来完成。影片不动声色、细致耐心地全面铺陈了索米娅生活起居的点点滴滴,既没有一般叙事电影的戏剧冲突,也缺乏画外音等手段插入式的表述索米娅的内心起伏,几乎每一个时刻的镜头处理都是微妙的环绕索米娅作为女性的“性态”展开,与同类电影虚拟、想象的立场差异明显。可以说,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在主流的、传统的叙事电影的模式之外,观看者不仅窥探到了少数民族差异性的生活景观,也借此从女性角色条理井然的生活中,感受其隐藏在这种生活秩序之后的压抑、无奈、奋争,并最终理解人物的命运。这种叙事样态与《苦菜花》等经典影片一脉相承。
另一方面,少数民族题材影片中,女性的形象呈现为多元化。在《冰山上的来客》《阿诗玛》《天山的红花》《尔玛的婚礼》等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影片中,与少数民族从落后走向“解放”抑或“开放”的启蒙主义叙事相应的,女性无论是主角还是配角,不管是“女英雄”还是“日常家庭妇女”,都能够被允许进入过往男性才能进入的场域——比如战场、家庭主力等社会角色担当,破除了女性一贯的被描绘为柔弱虚从的刻板印象,女性的话语权得到伸张,价值编码上出现一种另类认同的想象性建构。2010年上映的藏族电影《寻找智美更登》就是其中显在的例证。影片以藏族姑娘卓贝寻求自我的故事为基底,围绕她的情感蜕变展示了新旧藏区的生活境况,并在叙事中完成了对追求爱情和生命绽放的少数民族女性的阐释。作为片中唯一的女性,卓贝自始至终未曾摘下面纱,只露出两只眼睛默默注视着世界,她所有的情绪流露都是真情至上的,是率真、执着、勇敢、与众不同的,仿佛是藏族女性世界的代表,有意地与无名老板的爱人形成反差,制造了一个与藏区之外的现代化世界截然不同的女性形象,和一种另类色彩的主体形象认同。可以说,以藏族女子卓贝为代表的女性形象是少数民族题材影片中常见的想象符号。
二、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对女性的人文关怀
新中国成立后,少数民族电影的叙事基调在《景颇姑娘》等片中已经形成基本程式,即少数民族整体告别愚昧、走向自我确认之路的讲述。这种从民族旧俗中得到解放的话语模式,实际上是一种启蒙话语的变奏与再现。而在书写少数民族文化和现代文明碰撞时发生冲突的影像重构的同时,影片也在塑造一批美好价值传承者的女性形象,既引导观看者生发对少数民族区域境况的关注,也让强大的社会文化系统借此展示新型的行为、思想、观念范式,最终让启蒙话语和人道关怀渗透在主旋律的中国式重构之中。
首先,在某些民族题材电影中,女性不再是一种常规上的挑战力量,而是含混在启蒙主义的话语中,以超越性别、消弭二元对立的方式揭示出女性概念所涵盖的多样性、异质性。中国传统意识和历史现实中的女性,几乎都是被男权统治所异化的存在物,女性本身的自我意识和潜在力量在男性主导的体制内被抑制和剥夺。但是在此后的中国少数民族题材影视中,女性却脱离了性别范畴,与男性共同形成了对等的社会关系,但与此同时,女性本身的差异性也被消弭,其所有的价值承载是建立在性别属性被阉割、缺失和拒绝承认的心理/社会机制之上。如,《景颇姑娘》中的景颇族姑娘黛诺,受尽封建山官制度折磨,但她决不屈服。这种女性角色勇敢无畏,充满刚强的力量,女性的性别特质在主旋律的启蒙叙事基调中,在摆脱被奴役的命运的同时,其异质性元素也被悄然替换,成为一种被想象的身体意象存在。但这类电影并不多,在大部分少数民族题材的电影中,女性形象还是非常鲜明、丰满的,具有女性的独特魅力。
其次,少数民族题材影片在文化的冲突与碰撞、民族融合和互相尊重的书写中,也对女性倾注了人文关怀。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在涉及女性的叙事时,都会对两性的不平等强烈抵制,并质疑传统观念中对女性的歧见,积极塑造健康、美好、令人向往的女性形象,描绘新时代女性的自我觉醒,对女性人生的尊严和价值追求给予充分肯定。这种思想传统即便在如今的商业大片时代,依然得到了一以贯之的表达。如近年涌现出的优秀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新康定情歌》中,对于女性的多样关怀更是得到了与时俱进的改写。它择取了以汉族男子李苏杰重返康定找寻六十年前初恋藏族姑娘达娃的视角,分别陈述了三位迥然不同的女性的人生故事。在片中,达娃既是寻求自我的女性主体表征,也是藏区女性世界中作为“他者”存在的化身。影片颂扬了她的忠贞、乐于奉献与执着的品质,同时也对她在矛盾纠葛中的自我选择有了充分的尊重和体己的认同感。可以说,少数民族题材影片正是因为不断游走在多重文化棱镜之中,让它在关注文化差异的同时,对多样性的关怀视点有了更多的可能性理解。
三、历史语境下的性别书写
任何艺术反映都是历史语境下的产物。历史语境是决定所有文本意义、某个语句、甚或一个语词所必需的各类因素的综合关联体。从历史语境角度而论,中国少数民族题材影片其形态特征、人物构建等,均与特定时期诸如政治、文化、经济等生态因子息息相关,其所涉及的性别话语也必然遭遇意识形态机制的作用规约。可以说,从女性主义的视野考察,其所显示出的思想价值、审美取向,都是这种国家意识形态所伸张的民族认同和历史重建的衍生之物。
其一,在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有关性别的叙事被明确无误地融会到民族/国家多元一统的认同主题之中。在这些影片中,所有对于女性的塑造以及所有看似明确的女性主义意识,都是某个更为宏大的主题的附属品,和对于少数民族多元文化的体认和尊重的叙事一起,都是服务于强化巩固一体多元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表达。也就是说,这些影片中对于女性经验、女性意识的呈现,从女性主义视角审视,其实都是现实变迁需要的工具性存在。这一点,在新时期以来涌现的众多少数民族电影——尤其是历史题材影片中表现尤为充分。诸如在《奢香夫人》《傲蕾·一兰》《大凉山传奇》《悲情布鲁克》《月圆凉州》等片中,里面穿梭的女性群体,无一例外地都穿着自身民族最鲜艳的服饰,在与现代化空间和中原文化显示差别的异域,或上演突破汉民族禁忌的爱情神话,或无意间成为主题叙事的娱乐元素,抑或只是作为男性性别内心完美的“女性乌托邦”的存在。而其深层核心,都指向了国家/民族对既定秩序维护的需求和认同的依据。可以说,这些少数民族题材影片的女性意象,是性别意义上的民族认同的变异组成。
其二,以女性主义的视野立论,少数民族题材影片其镜像策略所衍生的审美追求和价值彰显,特别是其中女性主义的表现诉求,无一不带有历史重建的职责,即在国家统一、多元文化盛行的当下重生“存根”的冲动,充斥着对自身民族历史文化加以追寻的渴求。《喜鹊岭茶歌》里,一群畲族女孩在汉族青年小柳的感召下,意识到了本土保守势力的顽固,她们群起反抗。与此同时,在积极吸收外来文明新鲜空气的过程中,她们也意识到了自身民族文化身份那份古老记忆的厚重和温情。而《静静的嘛呢石》里,导演万玛才旦通过一老一少两个喇嘛的刻画,向消费文化泛滥年代的观众展示了一个深沉有力又静美无言的西藏。其中的女性开始隐没“五四”以来被认为政治正确的自身的性别主体性,回归本民族固有的传统美德,重归家庭、守望家园,在这样的镜像策略书写中,少数民族族群本身的文化力量得到了最大化的张扬。因此,可以说,这些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本身就是精英话语、民间情趣、国家形态彼此渗透、交叉的场域,是历史重建的意识潜在驱动下的产物。
综上所述,在历来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女性由于身份性别的特殊属性,一直都是重点表述对象,更是电影的公共空间领域内众多价值观念的承载者。可以说,依据女性主义的视角,这些女性与其说是一种性别存在,毋宁说是国家宏大叙事、族群政治/文化诉求、个体幻象三者混合后的符号。但电影也借此传达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少数族群女性群体的内心世界、女性经验、独特感悟,乃至其生命体验也得到了多元化的、深入的呈现,成为珍贵的影像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