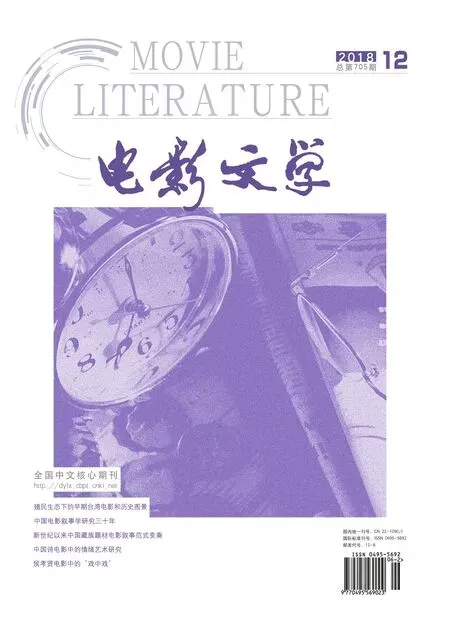比较美学视域下的任意空间与空灵之境
王 珂
(山西师范大学 戏剧与影视学院,山西 临汾 041000)
德勒兹视电影为一个生命体,它有两个维度的存在方式:一个遵循着感知运动模式,被称之为运动—影像;另一个打破了感知运动模式,被称之为时间—影像。所谓感知运动模式就是指遵循着日常生活逻辑和惯例的生命存在方式。由此可知运动影像就是指符合传统叙事程式、塑造中心人物、以建构意义为核心的一类电影,而时间影像就是打破传统叙事程式、去中心人物、以解构本质主义为旨归的一类电影。运动影像和时间影像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存在,而是电影这一生命体的两个相依的维度,运动影像只不过是间接的时间影像,而时间影像正是打破了感知运动模式突出呈现生命本真状态的影像。遵循感知运动模式的生命体可以按照日常生活逻辑做出种种反应和行动,生命体在这样的反应和行动中确证着自己的存在,而打破了感知运动模式的生命体无法依据现实生活逻辑对外界的冲击做出任何反应,陷入了无可奈何或曰动情的境况,在这样的境况中失去了方向和重心,无法找到存在的坐标,德勒兹称呈现这样境况的空间为“任意空间”。
有学者指出德勒兹的理论精神在于打破西方二元对立式思维方式,其理论与中国传统思想有着契合之处。而任意空间与宗白华所言的空灵与充实就存在这样的契合点。本文将通过电影《小城之春》深入阐述任意空间概念,并分析任意空间和空灵与充实之间的异同,指出看似相似的概念背后存在巨大的思维差异,为反思其理论的适应性问题,并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论以及构建中国电影美学理论体系提供一个启发。
按照德勒兹电影理论的逻辑,费穆的《小城之春》就是一部典型的通过任意空间呈现出来的陷入动情状态的电影。当周玉纹、戴礼言、章志诚等人相遇的时候,原本小城的日常生活流程被打破,影像突出地呈现着众人因遭受冲击而陷入无可奈何的动情状态。周玉纹已经和戴礼言结婚八年,八年里和丈夫相敬如宾,却相顾无言,面对来访的昔日情人无由地陷入了两难的境地。章志诚和戴礼言也同样面临如此的境况,一方面戴礼言因为戴家的毁于战火和身体的多病对妻子愧疚却又无所适从;另一方面章志诚旧情难忘却又不能罔顾和戴礼言的友谊。感知运动模式由此被打破,影片不再遵循传统的叙事程式,影片中的人物也从社会赋予的身份中脱离了出来。因此影片中的一切事物如残缺的城墙:破败的戴家、病恹恹的戴礼言、心事重重的周玉纹、无所适从的章志诚、陷入单恋的戴秀都脱离了日常行为逻辑,无法纳入现实社会的参考系中进行定位,如处在一个任意空间之中。此空间中的残墙破院既不指向曾经的恢宏完整之建筑,也不暗示消散成尘埃的破落,而仅仅是指向自身的半衰,即所谓残破本身的残破状态。周、戴等四人不再是为了某一世俗的伦理规定而努力解决所遭遇的困厄的丈夫、妻子、妹妹、朋友,他们就是自己,无法被任何价值系统和伦理观念所定义的自身,也就是说他们展现着生命本身的纯粹情感,散发着某种强烈的“纯粹性质”。
在德勒兹的电影理论中,任意空间所呈现的纯粹情感有两种特性:一种是上述的“纯粹性质”,另一种就是“纯粹力量”。纯粹性质和纯粹力量是纯粹情感的一体两面。即二者可以相互转化,性质的极限呈现,就可以化为一种力量。在《小城之春》中有数场室内戏,举其中一例就可以说明之。章志诚来到戴家后,四人聚在了一间屋子里,屋子正中是戴秀在唱歌,戴礼言坐在左侧,章志诚在右侧,周玉纹从后景来到了前景,正好站在了戴和章的视线交汇点上,而章的视线始终跟随着周玉纹的移动而移动。他们三人形成了一个既稳定又充满张力的三角构图。毫不知情的戴礼言是此三角构图中最弱的一极,心不在焉的章志诚处于另一极,心绪难宁的周玉纹则构成了第三极。三极之间的不平衡使力量在其中激烈奔涌,此境中的三人由此化身为力量本身。这种纯粹的力量沿着三角的三条边相互蹿涌,挟吞噬一切的态势誓要打破三者的平衡。虽然力量誓要打破平衡,但在极度危险的状态平衡依旧被保持。这就是说纯粹力量走向极限时反而呈现出一种动态的平衡,即动态平衡里有一种静态的性质。纯粹情感就是由这两极所构成的,它们的不停转化就是纯粹情感的涌现。周、戴、章三人,桌椅布景及周围的一切在性质与力量的不停转化中被“吸纳”,剩下的只有纯粹情感的流动。构成这样纯粹情感的任意空间就如同一个空灵之境,但又充实无比,处于其中的所有事物都成了存在的缺席者,而纯粹情感本身就成了唯一缺席的存在,弥漫在整个空间当中。
《小城之春》所构造的任意空间及其呈现的情感—影像,在乍然呈现自身的同时走向了塌缩。塌缩是指有生命的影像虽然陷入了一种无可奈何的境况没有引发对情感的回应,但是这种境况最终会被打破,人物终将从情感震惊中恢复并采取行动。在德勒兹看来当纯粹情感跌落进了日常中时,情感—影像就只是运动—影像系列中的一环,时间的绵延之流就如此被现实所困厄。《小城之春》的最后周、戴等四人从情感震惊中走了出来,随着章志诚的离去,一切又恢复了平静。周玉纹四人在种种原因之下达成了和解,看似解决了情感的危局,在现实中重新找到了自己存在的坐标。但在德勒兹看来这只不过是生命再一次被遮蔽,因为任意空间是超越日常的无定形空间,代表着生命的纯粹情感状态,当这一空间塌缩时,也就意味着现实重力的恢复、日常坐标的建立,影片中的一切事物都恢复了日常的状态,重新遵循着感知—运动模式的支配。
然而,恰恰在这里可以看出任意空间和空灵与充实之间的差异所在,在指出差异之前,需要先分析德勒兹的任意空间和空灵与充实的相同之处。它们的相同之处标示着西方非理性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的某种相似点,而它们的差异既让我们思考德勒兹理论的适用性问题,又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论以及构建中国电影理论体系的契机。
空灵与充实是宗白华论述中国古代艺术精神时提出的两个概念,它们根植于中国传统哲学和文艺理论。空灵和充实不仅代表着艺术之境界,也体现着人格之理想,艺术境界和人生理想在宗白华这里是不分的。这和德勒兹关注电影这门艺术的态度是基本一致的。德勒兹关注电影是因为他发现电影透露着时间的奥秘,诉说着生命的绵延。电影成了一种反抗西方理性主义传统,打破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确立生命的本真状态的有力工具。生命、时间、电影在他的逻辑框架中是同一的。因此,德勒兹论述电影,就是在阐述他的哲学思想,也是在关注真正的生命。任意空间概念不仅仅是对于电影处于动情时刻状态的描摹,更是对于生命本真呈现时刻的揭示。
在谈到空灵时,宗白华指出空灵之境不是无物存在,而是境中的人和物与世俗的暂时绝缘,呈现出一种超越现实存在与利益纠葛的自在和谐的状态,它们不再是异己的可利用对象,而是“如我一般的生命,如我一般的活泼之物”。而“充实”就是在如此空灵之境下诞生的“真意”——宇宙生命最广大、幽深的奥秘,灿然绽放,灵气四溢。空灵与充实之境就是要求在艺术上追求人与万物的本然样态,把他们从庸俗的世俗生活和物我的利用与被利用的状态中抽离出来,形成一个圆满自足的小宇宙。
这与德勒兹的任意空间概念有异曲同工之妙。德勒兹认为任意空间就是超越世俗生活的无定形空间,其中只有纯粹生命的流动,纯粹事物本然的呈现,这如同宗白华所认为的空灵与充实之境。它们的相同点都在于强调摆脱世俗的困扰,去除存在的遮蔽,脱离物欲与利益的萦绕直面生命本身。因为生命本身就具有不可言说之韵律。在德勒兹看来是性质与力量的生成与转换,在宗白华看来是宇宙大和谐的乐章。但差异也在这里,德勒兹追求事物本然之所是,瞩目万事万物乃至宇宙原初的混沌时刻,现实的人和事物不过是这原初混沌的“辖域化”,在他那里人只是一种沾染着日常的喜怒哀乐的“有机体”,其存在遮蔽了“无机”的纯粹生命之流,德勒兹眼中的生命已经是抽象意义上的生命,是一股无始无终、无穷无尽的森然法则之变动。而宗白华追求的是万物和谐之态,即人与自然平等相待的同时人又是自然的一部分,他没有取消人的存在,也就是说宗白华的空灵与充实其超越性是基于现实人生却不脱离现实世界的超越,德勒兹的任意空间的超越是基于彼岸的超越。空灵与充实之境虽然伸向宇宙星空却根植现实土壤,任意空间却携离去之势朝彼岸进发。
两种不同的超越方式的原因在于中西思维方式的巨大差异,宗白华的空灵与充实根植于中国传统哲学,而德勒兹的理论则根植于西方的非理性主义哲学,深受伯格森的影响。尽管在某种程度上中国的传统哲学被称为“非理性主义”,但与西方的非理性主义仍有着巨大的差异。体验性的诗化是中国“非理性主义”哲学的根本,而西方现代非理性主义恰恰有一个理性主义的根源。宗白华的空灵与充实是一种体验式的艺术精神和人格理想,具有“前理性”的物我不分的性质,而这种物我不分的和谐状态在宗白华看来就是生命的本真存在。德勒兹的任意空间所呈现的生命尽管也是一种物我不分的本真存在,但这种物我不分中“我”是被彻底取消了的。因此,任意空间被定义为超越日常生活,脱离三维坐标的失重空间,一旦恢复重力和回归生活,任意空间就会消失。
由此再看《小城之春》,用德勒兹的任意空间概念来把握之,只有周玉纹等人永远处于抉择的状态,永远陷在无可奈何之境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时间—影像,影片最后的和解和回归意味着任意空间的塌缩,生命之流的终止,现实日常的再度侵袭,生命的再次被遮蔽。众人将继续按照各自的社会身份生活,在日常庸俗中挣扎,周玉纹等人没有勇敢地面对自我,而是选择了忍耐或曰逃避。而用宗白华的空灵与充实把握之,《小城之春》的一景一物、一砖一瓦,皆注入了人的色彩,人融入了景,景也沾染了人的情感,残墙破院是周、戴等人心境的外化,它们诉说着往日的繁荣胜景和昔日爱情的甜蜜温馨,也暗示着此刻主人公颓然哀婉之心境。最后周玉纹等人在个体与他者之间、道德与情感之间、人与世界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点,达成了和解同时也是一段无由情感的释怀和个体的新生。导演截取了一个生活的片段,甄选意象营造出物我相融、空透和谐而又意味无穷的意境,传达出一种含蓄婉转、千回百转的审美趣味。
对同一文本用两种看似相似的概念分析之,却得到了不同的结果,周玉纹等人究竟是逃避、忍耐还是和解与新生,对电影理解的微妙差异背后必然是不同的理论观照,而不同的理论背后隐藏着巨大的思维差异。用德勒兹的理论来解读中国的电影,当然可以获得一种全新的视角和对文本的全新认识,但它一定会遮蔽甚至取消文本中不符合它理论框架的东西,所谓理论就是盲点。电影理论应当在具体的历史情境、当下语境中分析现象与问题,提炼出自己的理论思路与观念。从对任意空间与空灵之境的对比中,可以发现中国文论和哲学思想是一个宝库,它根植于中国社会文化语境,是对中国这片土地上艺术活动经验的抽象与思辨,批判性继承它们背后的思维方式才能更好地把握中国本土的电影现象,构建属于中国的电影美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