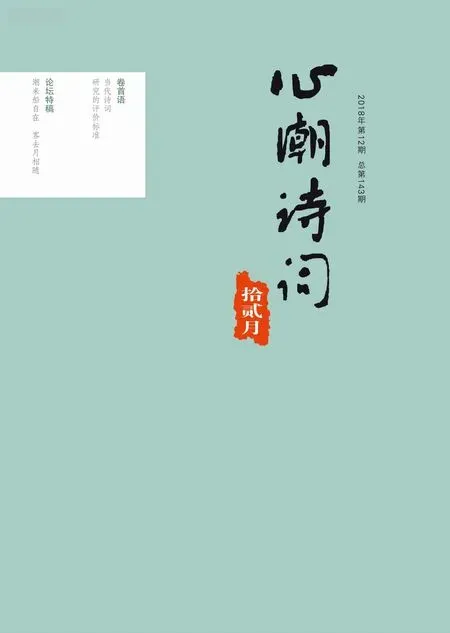旧体诗对早期新诗变革的影响初探
自晚清诗界革命以来,中国诗歌革新的试验浪潮就一直此起彼伏喧嚣不已,然而彼时诗歌改革的步伐又常令人惋惜地停留在新词新语的简单应用层面上,直至胡适、陈独秀高举“文学革命”的旗帜才真正开启了现代中国诗歌变革的序幕。如果说1917年《新青年》第2卷第6号刊发胡适的《白话诗六首》拉开了现代中国新诗的序幕,那么1922年出版的《新诗年选》中的一段话似乎就宣告了新诗在文坛的正统地位:“胡适登高一呼,四远响应,新诗在文学上的正统以立”。而胡适《尝试集》的出版更是加速了白话新诗争奇斗艳的历史进程。从胡适号召“诗体大解放”的中国新诗草创,中经郭沫若、李金发、闻一多等新文人的多路调试,新诗在新文学的第一个十年大致呈现出“自由诗”“格律诗”“象征诗”的三张面孔,可以说,新文学第一个十年,新诗交出了一份不错的答卷。但是,透过新诗写作变革之因来考察新诗十年的实绩,不难发现,新诗的每一次转向都与旧诗强悍的“影响的焦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换言之,旧诗成熟的体制与美学特质时时拷问并制约着新诗的写作。毫无疑问,新诗发生期的十年,不论是“对抗”格律还是“趋律”式的回归,旧诗在新诗写作中或明或暗的“印痕”既是一道亮丽的风景,又是贯穿新诗写作过程的“灵魂”式伴侣。本文试以新文学发生期的自由派新诗为讨论对象,探寻旧体诗对早期新诗变革的影响,以期丰富现代中国诗歌内质要素。
出离与回返:从胡适到郭沫若的自由派对抗
1922年,距离新诗在《新青年》杂志发表不过几年,胡适非常得意地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宣称“《学衡》的议论,大概是反对文学革命的尾声了。我可以大胆说,文学革命已过了议论的时期,反对党已经破产了。从此以后,完全是新文学的创作时期”,这段豪言壮语装扮了新文学的表面繁荣,可是倘若回首新诗发生期的艰难历程,又不免让人想起胡适的另一篇文章——《逼上梁山:文学革命开始了》——新诗发生期的历程充满了“逼上梁山”的艰辛。众所周知,胡适赴美留学耳濡目染亲身体验到了西方文化的神奇。在民族救亡的赤子情怀驱动下,以文学来救亡、启蒙的理念开始加速。与此同时,严复等人的进化论对胡适的文学革命观显然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在与美国友朋的诗学争辩中以及诗歌写作的反复亲身体验下,以白话来写诗的想法在胡适心中越来越成熟。《尝试集》被公认为新诗的开山之作,在文学史上的意义自不必赘言,不过,打开《尝试集》的附录《去国集》,翻阅新诗写作前胡适曾经写下的那些旧诗,其间,给人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其域外体验在旧诗写作中的别扭与分裂——诗中所表达的与实际想表达的场景出现了巨大的文化裂缝且难以调和,例如,《耶稣诞节歌》明明是为了叙写胡适在美国参加圣诞节的观感,何奈旧体诗中严重匮乏对应的语词去描绘彼时的场景,所以诗中使用了诸如“明朝袜中实饧妆,有蜡作鼠纸作虎”之类的生硬句子来转换实景的描写,以应对旧体诗在现代场景中的写作尴尬,而这也恰好回应了胡适自己所批评的“陈言未去”。可以说,正是因为现代文化启蒙的需要,以及旧诗在现代语体表达上的短板,直接启发了胡适关于文学工具革新的思路,而中西文化体验的深厚积累正好又为胡适的新诗写作也提供了坚实后盾,《尝试集》的出版成功更是夯实了新诗写作的道路。在白话新诗的创作中,胡适坚决贯彻了“作诗如作文”的诗学理念,以“诗体大解放”来推动新诗的探索与变革,比如早期发表《鸽子》《人力车夫》《一念》读来虽然平白如话却又别有风味,充满了现代的情愫,一举摆脱了旧体诗在某些时刻词不达意的窘境。且以《一念》为例:
我笑你绕太阳的地球,一日夜只打得一个回旋;
我笑你绕地球的月亮,总不会永远团圆;
我笑你千千万万大大小小的星球,总跳不出自己的轨道线;
我笑你一秒钟行五十万里的无线电,总比不上我区区的心头一念!
我这心头一念:
才从竹竿巷,忽到竹竿尖;
忽在赫贞江上,忽在凯约湖边;
我若真个害刻骨的相思,便一分钟绕遍地球三千万转!
此诗作于1917年秋冬之间,作者时在北京竹竿巷居住,突然想到家乡的竹竿尖山而作。诗语朴实却充满了现代气息,一洗板着面孔为政治说教而作的诗风。以小清新、甚至调皮的现实格调现身,在口语化的句式中借助西方科技知识将乡愁乡思的传统表达予以陌生化呈现。这首诗,且不论其现代思想的表达,至少在诗歌形式上,旧体诗也难有此魄力去自由应对现代语境,估计擅长旧体诗的民国遗老也难以如此轻快、细腻地表达胡适在诗中传递出来的现代性体验。还应特别指出的是,该诗在艺术手法上处理得干净利落:以四个“我笑你”的排比句式层层推进现代情愫的表达,整首诗的节奏感很强,而分行写作的形式也冲破了旧体诗写作的藩篱,切合了现代阅读求新的审美体验。诗的篇幅虽短小,但诗中思想的表达却很流畅,同时也回应了现代文学要突出人的这一伟大时代主题呼唤。然而,如果稍微注意一下《一念》诗中句尾之字,就不难发现,无论是“旋”“圆”还是“线”“念”都是诗人精心的韵尾安排,很显然,这种安排终究还是逃不脱旧体诗在韵律美学诉求上内在的影响。
在胡适写作的自由诗中还有很多此类作品,写于1920年的《湖上》,其意境的营造与《晨星篇》非常类似:“水上一个萤火/水里一个萤火/平排着/轻轻地/打我们的船边飞过/他们俩儿越飞越近/渐渐地并作了一个”。这首诗是与友人王伯秋夜游玄武湖时所做,虽然没有《一念》那么明显地追求诗韵,但细读之下也能影影约约感受到旧体诗的味道。整首诗以“萤火”为意象,以景喻情,将传统与现代的艺术手法溶于一首短诗之中,诗歌语言干净凝练、意境清新典雅、淡远含蓄。回环往复的吟咏、层层推进的韵味都令读者难以忘怀,但这些诗都逃不脱一个共同的特点——此类新诗韵味的形成有着明显的旧诗审美痕迹。
如果说仅仅看胡适一人的诗作尚不足以看清旧体诗对新诗影响有多大,那么再考察一下当时新诗群体的诗作,问题大概就能更为清晰。在胡适、陈独秀、沈尹默、刘半农、钱玄同等人的影响下,以《新青年》杂志为中心,中国现代新诗开启了多路调试的步伐。据刘福春的《新诗纪事》统计来看,仅是1917-1921年之间《新青年》一份刊物就先后刊发了如下一批新诗:《白话诗八首》(胡适)、《鸽子》(胡适)、《鸽子》(沈尹默)、《人力车夫》、《相隔一层纸》、《月夜》、《宰羊》、《车毯》、《老鸦》、《除夕》(沈尹默)、《丁巳除夕歌》、《除夕》(刘半农)、《新婚杂诗》、《雪》、《学徒苦》、《梦》、《爱之神》、《桃花》、《买萝卜人》、《春水》、《他们的花园》、《四月二十五夜》、《月》、《三弦》、《“人家说我发了痴”》、《山中即景》、《小河》、《一颗星儿》、《散伍归来的“吉普色”》、《D-!》、《欢迎陈独秀出狱》、《答半农〈D-!〉》、《爱与憎》、《牧羊儿的悲哀》、《题在绍兴柯岩照的相片》、《我们三个朋友》、《秋夜》、《慈姑的盆》、《梦与诗》、《莺儿吹醒的》、《四烈士冢上的没字碑歌》、《一个小农家的暮》、《病中的诗》。新诗仅从诗题上看就不难发现,这些诗歌整体上开始趋向了口语化。很显然,就用词而言,他们讲究平淡、清新;在标题内容所指而言,诗作对现实生活关注得深入而贴切,叙事特征较为明显。这一批诗歌的问世从文本实验的角度证实了胡适所开创的新诗路径是可取的,在很大程度上也有力回应了旧体诗人群对新诗的质疑与嘲笑,尽管其间存在的问题也不少。不过,短板就是短板,早期新诗屡为人所诟病的也正于此:毕竟诗歌本是以抒情为主的艺术样式,一旦过度追求口语化、散文化也就弱化甚至取消了诗歌的审美艺术功能。
口语化虽然开辟了新诗的一条新路,然而作为一把双刃剑,模糊诗歌审美特质的硬伤是无论如何都无法回避的,所以,典雅深致的旧体诗对新诗所形成的焦虑日渐凸显。简言之,旧诗形成的审美阅读体验也逼迫着新诗力图克服口语化、散文化带来的弊端。不过,反过来看压力也是动力,也正是因为有了旧体诗形成的焦虑才更为迅猛地推动了早期新诗的自我革新。俞平伯在写给新潮社同人的信中,他敏锐地直陈白话诗的问题:“我现在对于诗的做法意见稍稍改变,颇觉得以前的诗太偏于描写一面,这实在不是正当趋向。因为纯粹客观的描写,无论怎样精彩,终究不算好诗——偶一为之,也未尝不可”。可见,克服一味的描写、恢复诗歌本有的审美情趣刻不容缓。郭沫若的《女神》以及冰心、宗白华为代表的散文小诗、俞平伯《冬夜》横空出世在新诗坛掀起的三股浪潮显然为新诗缓解此前的焦虑带来了新的希望。回看新诗草创之时,以胡适为代表的早期新诗写作的窘境基本上是当时新诗人普遍困境,他们一方面大声疾呼要打碎旧体诗的枷锁,然而又常常不自觉地迎合旧诗的内在约束。但《女神》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早期新诗创作的尴尬,所以闻一多赞叹:“若讲新诗,郭沫若君的诗才配称新呢,不独艺术上他的作品与旧体诗词相去最远,最要紧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的精神——二十世纪底时代的精神,有人讲文艺作品是时代底产儿,《女神》真不愧为时代底一个肖子”。郭沫若的《女神》以其气韵生动、惊天地泣鬼神的浪漫气息获得了文坛广泛的响应,而闻一多的论断最让新文人感到自豪的恐怕是,郭氏的新诗终于与旧体诗拉开了距离,应该说,《女神》探寻雄浑气概的自由体诗新路令新诗面目为之一新,一洗《尝试集》中旧体诗的明显印痕,从这个意义上说它确实冲决了旧诗词格律的罗网。《女神》的成功不仅因为其雄浑奔放的诗学特征,内容上美学意义上的时代气息也引领了新诗的审美精神追求。其想象力之丰富、抒情之豪放,强力映照出了五四时期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郭沫若诗中多采极富生命力的意象来增强诗歌情感表达的力量,让时代感情的奔涌有了强力表现的符码,而动人心魂的鼓噪力为新诗的大众化开辟了新路。更值得注意的是,《女神》在诗歌形式上大多不讲究整齐与押韵,但外在形式上摆脱了当时新诗人饱受旧体诗影响的困境,引导早期新诗逐步去除白话诗的粗糙,从而走向了真正的现代新诗。正如郁达夫所说:“《女神》的真价如何,因为郭沫若君是我的朋友,我不敢乱说,但是有一件事情,我想谁也应该承认的,就是‘完全脱离旧诗的羁绊自《女神》始’的一段功绩”。与此同时,《女神》中的《凤凰涅槃》《棠棣之花》《湘累》《女神之再生》为中国新诗的诗剧之路也打下了坚实的探索根基,郁达夫在《文学旬刊》上撰文:“我国对剧的研究本不发达。诗剧尤为凤毛麟角——可以说完全没有的——诗剧界得这篇《女神之再生》,做先锋去开辟路径,真是可喜的事”。这些同时代人所作的评论都充分说明了《女神》在当时已经取得了广泛认可,并且为新诗变革之路做了很好的示范。
对话与圆融:从湖畔耳语到小诗心灵的探寻
当然,作为自由体诗探索现代诗歌的还有“湖畔”诗人的创作和冰心、宗白华为代表的小诗创作。但无论是翻阅动人心扉的湖畔诗歌还是阅读颇富哲理的小诗时,一个虽显微却又不能忽视的特点涌现了出来——正是旧体诗的典雅意境让作为新诗代表的小诗获得了读者的认同。1922年,汪静之、冯雪峰、潘漠华、应修人在出版了他们的合集《湖畔》之后又有了《春的歌集》出版,可谓诗潮涌动。
“湖畔”诗人于新诗的贡献更多容易体现在对情诗的勇敢抒写,但其在人性启蒙方面的功绩显然也不能忽视。应该说,在五四新潮的启蒙下,“湖畔”诗人高擎爱情旗帜,强烈反对封建礼教,号召个性解放,在社会上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同时也招致了很多批评。但废名认为“康白情的《草儿》同《湖畔》四个少年人的诗,是新诗运动后自然的发展”,他还认为湖畔诗人的诗是“没有沾染旧文章习气老老实实的少年白话新诗”。的确,“湖畔”诗人大胆熔铸中国古典诗歌的意境以及日本俳句的美妙,大胆歌唱青年人的美好情愫值得肯定,他们的诗读来更显得率直、清新,尽管在艺术水准上仍显得不够老练,但正如朱自清所言“中国缺少情诗,有的只是‘忆内’‘寄内’或曲喻隐指之作,坦率的告白恋爱者绝少,为爱情而歌咏爱情的没有。这时期的新诗做到了‘告白’的第一步,《尝试集》的《应该》最有影响,可是一般的趣味怕在文字的缴绕上。康白情氏《窗外》却好。但真正专心致志做情诗的,是‘湖畔’的四个年轻人。”可见真情在新诗中的涌动对于恢复诗歌的审美抒情功能极为有益。不过,以汪静之为例,其早期的《惠的风》确实有散文化的倾向,也不讲求韵律,但随着人生阅历的加深,尤其是新诗整体上的自我修正潮流,及至1927年出版《寂寞的国》,汪静之的诗风出现了大变——走向了格律体的形式探索,故此朱湘也在与他的通信中赞扬他“能在诗的形式美上做有力尝试了”,事实上,湖畔诗人的诗风的演变恰好证实了旧体诗对新诗形成的“影响的焦虑”。
如果说率真烂漫的湖畔诗风与充满叛逆精神的《女神》同时构建了五四诗坛的时代精神,那么1923年冰心与宗白华的哲理小诗则一扫狂飙突进之后社会的整体压抑感,为诗坛带来了清新的心灵安抚。这些小诗往往三五行成一首,短小隽永、令人思索回味。小诗的出现是新诗在形式上的另一次突破,丰富了新诗在表现诗人内心细腻情感方面的内涵,为现代性的抒写提供了别致的舞台。罗振亚先生曾专文指出小诗域外传统的主体乃是日本俳句,小诗“冥想的理趣”与“感伤的情调”“淡泊、平易、纤细的审美趣味”等古典风格受到了日本俳句的深刻浸染,日本俳句在对中国小诗形成“诗意纯粹性的构筑”“激发出‘冥想’的理趣”“精神情调上充满感伤的气息”等方面产生了潜在影响。众所周知,日本俳句受中国古典诗歌影响很大,例如人们耳熟能详的日本俳句大家松尾芭蕉就对唐诗借镜甚多,其诗“今夜三井寺,月亮来敲门”让人很自然就想到了唐代诗人贾岛的“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其“日月乃百代之过客,今岁又是羁旅也”同样让人想到李白之“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可见,日本俳句与中国古典诗歌之间存在紧密联系,也正因此,日本俳句与中国古典诗歌精神气质的相近性给中国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逐渐兴盛的小诗打上了浓郁的古典诗词烙印。再如,宗白华的诗集《流云》语言工巧,却自有出水芙蓉之美,其短诗在意境的营造上更是广为后人所称道,比如这首《红花》:
我立在光的泉上。
眼看那滟滟的波,
流到人间。
我随手掷下红花一朵,
人间添了几分春色。
整首诗虽仅仅五行,但诗歌意境之开阔令人惊叹,大有包罗宇宙万物的情思在里面。立在光之泉上,让人浮想联翩,画面感也极为生动。而那流到人间的滟滟的波,更是特别,仿佛可以看见站在天上俯瞰大地而思接千载的图景。可以说,这首诗人生哲理与诗歌意境合二为一、却不造作实在难得。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宗白华的小诗真正做到了以小见大,其诗不仅在形式上再次丰富了新诗的发展路向,尤其是在现代情感的表达上,其熔铸古典与现代的新质为新诗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再如这首《夜》:“一时间/觉得我的微躯/是一颗小星/莹然万星里/随着星流/一会儿/又觉得我的心/是一张明镜/宇宙的万星/在里面灿着”这首小诗,无论是诗人内心世界的感受,还是对外界的描写都显得气度非凡、哲思万千,作者以如此小的篇幅却营造出了如此美妙而阔达的意境实在不易。正如宗白华自己所言:“这微妙的心和那遥远的自然,和那茫茫的广大的人类,打通了一条地下的神秘暗道,在绝对的静寂里获得自然人生最亲密的接触”。正是宗白华在诗艺上的探索让此种静怡的心境与诗情完全接通了古典与现代的哲思。其实,宗白华早在《新诗略谈》中就曾谈及新诗的音乐美、绘画美的问题,他说:“我们要想在诗的形式有高等技艺,就不可不学习点音乐与图画”,这个提法实质已经触及到了新月派后来提出的诗歌三美的问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宗白华曾经描述《流云》小诗当时写作的情形:“往往在半夜的黑影里爬起来,扶着床栏寻找火柴,在烛光摇晃中写下那些现在人不感兴趣而我自己却借以慰藉寂寞的诗句”,可以想见,宗白华在幽暗的花火下写出的宇宙空幽诗情与其早年旧体诗的熏陶有着某种紧密的联系,因为,在他看来,诗是“用一种美的文字——音律的绘画的文字——表写人的情绪中的意境”,很显然,宗白华是以生命诗学来烛照古典诗歌的意境并且将之转化为现代诗意的诉求,这一努力毫无疑问有力地拓展了现代诗歌的写作路径。所以说,宗白华的这一努力也从侧面反映了其诗中语言的凝练与优美、意境的典雅与深远,事实上,早已在不知不觉中有了中国古典诗歌的强大投影。而众所周知,这一投影并非个案,投身小诗写作的诗人非常之多,俞平伯、康白情、汪静之、沈尹默、冯雪峰、应修人、潘漠华等新诗人都曾投身其间。可以说,小诗的闲适、淡然、典雅等诸种情趣其实正是对旧诗美学体验所形成的阅读焦虑而做出的圆融性回应。
结语
无论自由体新诗在多大程度上取得了文坛的认可,但新诗人内在的焦虑显然无法掩饰,刘半农在1920年写给胡适的一封信中提到:“旧体诗的衰落,是你知道的。但是,新体诗前途的暧昧,也要请你注意”,刘半农的此番话,一方面,证实了新文学群落对旧体诗衰落的遐想以及早期的新诗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文坛地位,但另一方面,不能回避的是,刘半农此信的重点却是为新诗的前途担忧——旧体诗对新诗如影随形的压力。总而言之,不论是诗体大解放还是《女神》式的抒情回归抑或小诗的流行,都说明早期新诗的种种变革其实始终都难以摆脱旧诗美学样式的强大影响。应该说,当胡适等新文学先驱们借助进化论的威力树立起“以新为美”的价值评判标准后,新旧文学在新时代文坛的地位也就逐渐形成了巨大的分野。凡是新的就是好的,在这样的时代浪潮冲刷之下,新旧诗的文坛位置发生逆转也就成为了必然。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旧诗作为强大的传统,时刻都潜隐地影响着现代中国新诗的发展,而正是新旧诗这种内在的相互映照与影响,又为现代中国诗歌的内涵注入了新的前行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