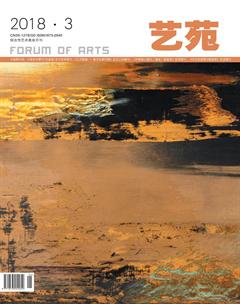《清水里的刀子》:超越“民族身份”的银幕探索
张歆
【摘要】 《清水里的刀子》融合了中国少数民族电影的传统风格与西方现代美学意识,从而产生一种为大众所认可的独特美学特质。电影中没有囿于“特殊性”的表现来诠释民族,而是试图通过关于生与死的人类哲学命题的探讨,超越“民族身份”的类型化话语表达,构建清洁的美学场域来实现少数民族电影自身的突围。
【关键词】 《清水里的刀子》;旁观者;美学场域
[中图分类号]J90 [文献标识码]A
少数民族电影呈现出各个民族不同的生存方式、文化景观、生存经验以及美学追求,它们共同构建了一个巨大的影像空间场域,拥有着自身的运行规则。对民族生活的原生态书写、个人的情感诉求、文化身份的认同建构等方面的影像表述,建构着一个“实在的影像空间”(1)。“艺术作为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无疑导向对世界的洞察和理解,它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上与时代的理性观念汇合或重合。”[1]13随着全球化程度的加深,“本土的世界主义”正在形成,少数民族电影不再处于一种“奇观化”的被表述状态之中,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关于日常生活的平静叙述,这一切愈加显示出少数民族电影具有一种更广泛的文化接受的可能性。找到这个空间场域的突破口,探索少数民族电影在世界电影格局中的定位,这关系到少数民族电影的未来发展趋势。
2018年4月4日上映的电影《清水里的刀子》改编自回族作家石舒清的同名作品,以发生在干旱的西海固中一个穆斯林在老伴去世之后的生活为主要内容,在西海固这个独特的地域文化空间中书写了看似平淡的人与人、人与牛的故事,从而引出了对生与死这个人类终极哲学命题的深沉思考。这部电影中超越“民族身份”的银幕探索,没有固守于表现民族的“特殊性”来诠释民族电影,而是从特殊性走向普遍性,通过美学场域的构建来实现少数民族电影自身的突围。
一、旁观者的凝视
作为一位青年汉族导演,王学博并没有妄言自己能够去完美诠释潜在的民族意识与宗教信仰,而是通过长达十个月的西海固生活的实践经验去获取旁观者的立场主动融入西海固这片独特的文化地域之中。这体现了作为一个拥有自己美学追求的青年导演的抱负。就像拍摄《尔玛的婚礼》《青槟榔之味》的汉族导演韩万峰说的那样,如果用自己的思维惯性去理解少数民族“是有误差的”,他在电影创作中尽量保持一种距离,“我采取的是记录,我不做表现”[2]。王学博也表示,在《清水里的刀子》的创作中,“我的重点是在刻画这样一个人,而不是一个民族话题、一个家庭话题,我想这些最后也都是人性的话题”[3]。
《清水里的刀子》从主题阐释到叙事策略,都显示了导演王学博试图改变以往少数民族电影在电影市场中边缘化地位的努力。他并没有为了迎合市场而放弃对民族身份的忠实叙述,而是具有更高的美学追求。他在电影中超越“民族身份”的特殊性演绎,聚焦于更具有普遍性的“人”的内心的追索中。电影着意于经过美学升华的情感作用实现民族文学的自身突围。整部电影本身实际上显现的是不停变幻意义与目光下的“他者”的注视,导演与主创们不同的民族身份(2)使得电影本身达成了一种对话,在艺术风格上呈现出了“多元一体”。大道至简,银幕探索中的种种冲突和裂变在电影本身的主题呈现中却又浑然一体。
在电影中,“高度写实的生活场景的断片所形成的一个非常优美的,关于信仰,也关于日常生活的图画”[4]。电影通篇采用大量的长镜头和冷色调去建构一个独特的属于电影本身的叙事空间,在电影中大量使用的黑、白的色彩元素,使這个地域空间以清洁的面貌呈现。
电影中不再是单一采用“农人”“荒漠”“马”这些略显苍白的意象,电影突破类型模式下的少数民族电影语言。作者通过大山在沉寂的薄雾中的隐现、颓败的屋舍、成片的黄土堆就的坟头等场景,强调某种同构性和时空的一致性。这些意象都坦然地存在于西海固这块不毛之地中。黄土、泥泞和阴霾并没有给生命带来阴霾和虚无。人们在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中坚守着自己对于清洁的追寻。死亡的冷寂与新生的纯净完成了某种形式上的转换,新生情节在电影中的出现实际上蕴含着导演对于西海固的深情凝视,对于拥有坚韧品格的民族的赞颂。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对于信仰的坚守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生存状态,一种充满洁净感的民族意识。老人在家中的沉思、坟地上的静穆和宗教仪式的庄严吟唱表现出一种具有连续性的生命感受,显示了在这里生活的人们对生命、生存的一种复杂的观念,死亡、再生、交替更新的关系带来了一种生命的未完成性。
虽然电影的叙事一直围绕着死亡主题,但是就像导演在接受访谈时所说的那样,他的关注点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对于死亡的重复,而是更加深入到人的灵魂和内心中去寻找一种日常生活中潜藏着的对待生与死的力量,而这种力量就存在于土地中。他不执著于在电影反复运用死亡的符号指称来突出和加深电影表面上的主题意义。他深知,符号如果被无限制地运用,其意义终将被耗尽。电影中通过对日常生活中吃饭、做饭、闲聊、喂牛、做农活、孩子的打闹、下雨天的忙乱等场景的连缀和刻画,试图找寻与电影主题的关联性而为这个沉重的主题自身存在获得一种意义。电影形式本身包括了故事的全部结构,为我们提供了一张西海固的精神地图,在我们跨进电影院的那一刹那就被牵连到作为旁观者的意指和重构的现实中。电影通过影像的呈现,不仅展现了一个现象世界,也表现出了一种主体经验,镜头成为了对某种人生状况进行反思的窗口。电影的导演虽然是王学博,但实际上早已是每一个观者。
二、清洁的美学场域
就像罗伯特·麦基说的那样,当今“漏洞百出和虚假的故事手法被迫用奇观来取代实质,用诡异来取代真实”[5]6。在这样一个娱乐至死的年代,脆弱的故事为了博取观众的欢心已经堕落为金钱的炫目噱头。相对于浮华、空洞和虚假的故事,我们需要“用明丽素洁的光来照亮人性和社会的阴暗角落”[5]6。当全球化成为别无选择的事实(3)时,它打破了西海固这个独特的地理空间的封闭性和独特性,电影中的西海固成了一个“话语言说和意识形态隐喻的存在场域”[6]。《清水里的刀子》在银幕上呈现的洁净暗含着对这片土地上每个人的尊敬,也包括对这个民族本身的尊敬。
电影中在决定把牛当作妻子过世四十天的祭品以后,老人和儿子对牛精心喂养、清洁。在祭日的前几天,这头牛在供它饮的水里看到了将要宰它的那把刀子,于是开始不吃不喝,为了以一个清洁的内里来结束自己的生命。这让刚刚失去老伴、自己也进入年迈的老人,陷入了对生命和死亡的思考之中。
当精神得以栖居的家园早已经面目全非的时候,王学博试图寻找和构建的,是一个清洁的美学场域空间。美国学者爱德华·苏贾说:“空间也具有它的精神属性,一如我们所熟知的社会空间、国家空间、日常生活空间、城市空间、经济空间、政治空间等概念,但这并不意味空间的观念形态和社会意义可以抹杀或替代它作为地域空间的客观存在。”[7]作为具有精神属性的地域空间是以象征和隐喻方式存在的,电影中的西海固无疑是实在的物质空间和弥散的精神空间交织共融中产生的具有多重意蕴的地域文化空间。它的存在,承载着那束“明丽素洁之光”,贾平凹在《文学是水墨的》一文中曾经说到:“大转型期的社会有太多的矛盾、冲突、荒唐、焦虑、文学里当然就有太多的揭露、批判、怀疑、追问。”[8]同样,作为影像叙事的电影也同样给我们呈现了纷繁复杂的主题,过多的主题和色调充溢着我们所感知到的电影空间,繁华落尽处现实中呈现的是一片苍白,叹息、笑骂、感叹后留下事物只是“21世纪商业消费和视觉奇观空间的彰显和张扬”[6]。而在《清水里的刀子》中,居住在西海固的人们那种特有的民族记忆通过银幕跨越时空的局限,透过镜头呈现出来的地域性和民族性的书写更像是一种隐喻,用一种隐蔽但充满力量的话语定义了电影所构建的这个清洁的世界。导演将西海固的人们心底最深处的对待生活的坦然与老人看待死亡的深邃目光相结合,显示出了导演对书写民族精神的执着。导演在十年的时光中不断回到这片文字和影像所建构的苍凉大地,叩问自己的内心。可以说,《清水里的刀子》是一部具有自审意识的作品,它通过老人的眼睛去审视一个拥有信仰的民族灵魂深处对待生与死的坦然。波澜不惊的影像中不再有那用以区分边缘与中心的难以抒解的痛苦,如影随形的焦虑、恐惧和绝望。
三、流动的叙事空间
在发现和建构双重意识关照下,我们的生活处于一种混杂,交融各种不同文化内容的客观社会结构当中,碎片化、身份撕裂与失忆,不可避免地成为人们主体意识的一部分。为了消解这种碎片化、失忆的影响,电影中构筑了一个在房屋、田地、清真寺中流动的叙事空间,使得貌似散乱的镜头通过老人的视角得以连缀。经由空间的变幻,老人正视着死亡与灵魂,不断和自己对话。在妻子无常后,在黄牛不吃不喝日渐消瘦后,在劝阻儿子出外打工无果后,巨大的孤寂感包裹着他。他在沉寂中一步步达成与世界、与自我的和解,走向坦然与平静。虚化镜头的使用使薄雾中、黎明中、夜色中、大雨中的电影构图都呈现出朦胧与陌生的效果。在这些镜头中,蕴含了一种超越民族性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类的悲哀。这种悲哀在老者一次次清洁自身的镜头语言中得以化解、冲淡、澄净,渐渐将电影的节奏转到一种平缓的状态中来。
这一点也在电影的结尾处有所呈现,故事的戛然而止带来的电影结构上的未完成性恰恰是其精到之处。在观者看来,电影中的叙述永远呈现出一种未完成的状态,正因其未封闭的话语结构,观者参与到电影的意义的阐释之中,因此电影的审美意义呈现出连续不断的生成性。电影本身所具有的开放性,使得其最终的意义能够循环着达成一种自我实现,去构筑西海固这个充满独特民族性的地域,叙事的未完成性和开放性都给观者留下了审美参与的位置。
在王学博也参与制作的万玛才旦导演的电影《塔洛》中探讨的是那些积淀在民族心理深处的古老文明和现代性冲突中产生的具有普遍性的身份焦虑和无所适从的心理状态。而《清水里的刀子》试图为我们呈现的是一种复归了神话力量的纯净的叙事状态,它崇尚简单和清洁,努力挣脱话语的束缚,它试图用关于生活的叙事,为过去提供意义,解释现在,并为未来提供指引。在这个人类无法把握自身的位置和未来方向的时代,人们将自己层层包裹进繁复的语言形式、庞杂的艺术形象、晦涩的神话象征之中,而电影借助自己独特的媒介形式将蕴藏在文本中的民族性和地域性借助银幕上的形象使其更加饱满充沛而又不失其神韵。电影通过镜头带来了某种共鸣,唤起了人们心底潜藏的那种震撼人心的情感激荡。
四、結语
当代人的精神生态的失衡表征为现代人的心灵丧失了对崇高和超越性存在的追求,精神变得日益平庸而低俗。在日常生活中表现为一种世俗化和消费化倾向,在艺术活动中表现为沉溺世俗、肉身自恋、逃避精神困境但又无力突围,电影中充斥着种种对于生命的否定,幻像与欲望充斥了电影的话语场域。我们在《清水里的刀子》中发现了自身,发现了一种蕴藏于普遍性之中关于灵魂的真挚表达,它将我们带入西海固这片清洁的美学场域之中,让精神远离堕落与颓废,从喧嚣和怪诞中逃脱,重新获得对于日常生活中最朴实洁净的美的欣赏能力。
在少数民族电影创作中,面对全球化带来的文化的交融,“最重要的不是导演的民族身份,而是导演的文化态度、审美态度,包括对少数民族生活、少数民族文化的把握与审视、所选择的审美表达方式以及包括少数民族电影观众在内的广大观众的认同”[9]。少数民族电影呼唤着坦诚,呼唤着向死而生的勇气;呼唤着坦然,呼唤着顺其自然的平静;呼唤着坦荡,呼唤着胸怀世界的壮志。电影从来不是用影像来给出某种定型了的想象,而是面对人类生活的共同困境,实现对现代性的拯救。
注释:
(1)居伊·德波认为影像天生是现代性的追求,因为在现代,很多东西都在消失,都被打碎,于是只有一样东西变得真实,就是影像。影像成为我们最后安放文化的地方。它不是一个手段,也不是一个工具,而是一个地方、一个处所、一个实实在在的空间。
(2)《清水里的刀子》改编自作家石舒清获得鲁迅文学奖的同名作品,由导演尔冬升、张猛、万玛才旦监制、青年导演王学博执导,作家石彦伟参与策划。
(3)戴锦华教授在《飘移、碎裂与亡灵出没——数码时代的性别、家庭与父权》的讲座中提到。
参考文献:
[1]陈晓明.审美的激变[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
[2]邹华芬.记录全球化背景下少数民族的生存状态——《尔玛的婚礼》导演访谈[J].电影新作,2009(2).
[3]这部平静如水的电影,问出了一个你想也不敢想的问题[EB/OL].http://www.sohu.com/a/227259716_556712.
[4]《清水里的刀子》北京首映,主演大赞主创,业内人士高度肯定[EB/OL].猫眼电影.https://m.maoyan.com/information/36399?_v_=yes&share;=android&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5](美)罗伯特·麦基.故事:材质、结构、风格和银幕剧作的原理[M].周铁东,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
[6]巩杰、梁英建.中国电影“西部空间”的影像呈现与文化嬗变[J].电影艺术.2017(4).
[7](美)爱德华·苏贾.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M].陆扬,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
[8]贾平凹.文学是水墨的[J].民族文学,2016(3).
[9]饶曙光.少数民族电影:多样化及其多元文化价值[J].当代文坛,2015(1).